19 反对裹足行动(一)
第一部: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
如果你现在对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海水时的感觉还记忆犹新,那么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脚时的心情,你就能深感同受。我对那里完全陌生,中国最古老、在人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就是裹脚。
我孤身一人去南方反对裹足,得到了天足会名誉会长的鼎力相助,她写信给中国招商局(一个很大的航运公司),说我代表天足会出行,这样我就可以乘招商局的汽船免费周游全中国。此行,我决心要全力工作,不辜负他们给我的优惠待遇。他们还答应把中国南部的欧洲人介绍给我。我在中国西部住的时间比较长,在南方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我们在汉口租了维多利亚剧院,以方便我登台演讲反对裹足,这次演讲我还特地请来中国政府官员旁听,并由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中国官员们鱼贯而入,有些人身后还跟着随从,有的官员把头昂得高高的,像是藐视天地万物间的一切事物,架子摆得如此大,我的心开始变得冰凉。领事先生开始向听众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当我站在这些听众面前时,才彻底意识到与中国官员讨论女人的脚这一敏感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多么不可思议,况且与他们讨论的还是一个外国妇女,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中国翻译临阵怯场了,对此我毫不奇怪。中国官员的威慑力把他镇住了,无法再履行他对我的义务。幸好一个传教士赶来救场,他的中文极好,说话掷地有声。眼前这一幕太滑稽了,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以免大声笑出来。对这些中国听众来说,我所说的一切不过是给他们茶余饭后提供了笑料。关于反对裹脚的小册子,在会上散发了2000份,临行前,几个主要官员还向我索取。
汉口是武汉三镇之一,与其他两镇间隔着汉江和长江。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的府邸就在长江对岸的武昌,据说他的文采天马行空,无人能比。我们用红纸写了张之洞关于反对裹脚的话,贴在会场里。张之洞把中国古文发挥得淋漓尽致,行文中他把反对裹脚的理由都说尽了,关于反对裹脚的理由,恐怕别人很难再用古文写出来。他是“文理”方面的专家,张之洞的文章太深奥了,那些“愚民”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到这里来听我演讲的一位军官,好像只为了研究张之洞的文采而来,他对我的演讲丝毫不感兴趣,不过听到最后,他还是签名加入了我们的天足会。汉阳是三镇中最小的,它与同在长江一岸的汉口间隔着汉江,在会议上,汉阳知县表示他家里的女眷都不裹脚。此举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裹脚,总督张之洞大人大加鞭挞,汉阳知县家里的女人又都没有裹脚,汉口这样的商业城市,怎能就此自甘落后呢?他们都争相上来索要我们的传单和小册子。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家眷裹脚的痛苦,有谁不想让她们摆脱呢?在会议开始前,我的翻译表现良好,没有失声,他承认曾经把小女儿的脚松开两次,可他妻子又给裹上了。让女儿裹脚,母亲们是为了让她们争得男人们的欢心,希望她们将来嫁个有地位的丈夫。上了年纪的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男人,都反对女性裹脚,他们认为那是野蛮的象征。欧洲妇女戴耳环、束腰以及穿高跟鞋,都曾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有地位的未婚男性喜欢小巧玲珑的脚,女人们都知道,一些女性认为裹脚会增加自己的女性魅力,这样一来就会征服男人的心。
汉口的集会后,我们又在汉阳举行了专门由妇女参加的集会。对废除裹脚这一观点,所有到会妇女都赞同。当我们请这些摆脱了裹脚布的妇女们站起来时,她们似乎有点不太习惯,经努力她们还是慢慢站了起来。在我们向她们耐心地解释了裹脚的坏处后,这些湖北妇女们脸上都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她们坐下去,又全站起来。在武昌举行类似集会前,我们还专门针对上层社会的年轻男子们举行了一次集会。我在会上提了一个较为无知的问题,就是女人是不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才裹脚,满屋子人听了这话都吃吃笑起来。第二天一早,在湖北省会的大街上,一些小孩子从豪华官宅中跑出来,上前询问我还有没有多余的小册子,他们要把这些小册子拿回家去。汉阳之行的成功标志是:扔了裹脚布的妇女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此行结束后,我回到上海,开始为去南方演讲废除裹脚做准备。
默默无闻的欧洲人为推动中国废除裹脚运动所花费的精力,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不过他们也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此次南行对英国读者而言,最有趣的莫过于中国人自己对裹脚所持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我在拜访李鸿章总督时听到的。首先,我请英国驻华总领事在这件事上对我提供帮助,或者由他直接把我介绍给李鸿章。他说,我这样一个女人,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像这样有失礼节的事情,不用说他帮不了忙,连提它都毫无必要。幸亏有住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他给李鸿章的一个养子——李大人(此人于1908年被派往伦敦做驻英公使)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把我引见给李鸿章。我也给李大人写了信,信上说如果李鸿章大人赞同废除裹脚,将会大大推进废除裹脚运动的进程。假如星期天李鸿章总督有空,请他代为安排此事。届时,与我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时间再推迟的话,我就得去外地了。李大人很快就做了答复,定出了日子和时间。当时我正好要去参加一次中国妇女的集会,约定的时间对我来说有点不太方便。此前,我还参加了一次在长老会教堂里举行的集会。会上,两位中国医科女学生接受了玛丽·富尔顿大夫向她们颁发的毕业证书。两位女士及他们的朋友和同伴们的穿着活泼、漂亮。按中国方式,教堂里装饰着无数绿色的树枝,每人手上都拿着红纸,上面印有赞美诗,当人们翻动红纸时,像有许多红色的鸟在教堂里飞翔,为节日平添了一抹喜庆的气氛。
在驻华传教士中,科尔大夫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在亲手建成的两家医院投入了毕生的精力。那天他也出席了颁奖典礼,并讲了一个故事,以此来阐述他对医疗技术的深刻理解。那是20多年前,一位中国妇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请求他医治她的双脚,因为裹脚,这位妇女的双脚已经坏死了,她请求外国医生替她恢复双脚的功能,因为奇迹总能在外国医生这里发生。
如果奇迹真能发生的话,将会有多少中国妇女脱离苦难啊,或许医疗技术真能够修复看得见的伤痛,可又有谁能修复她们内心的伤痛呢?有些国家的年轻人喜欢追求时尚,殊不知追求时尚同样也会给人带来痛苦。
一位中国舰长(曾在耶鲁大学学习)自告奋勇为我做翻译,他的翻译完整、准确,这一点,可从听众急切的表情以及不时发出的阵阵笑声得知。有那么一两次,这位英武的舰长在翻译时明显停顿了一下,他的眼睛扫向教堂屏风后的妇女,原来他的妻子坐在那里。他的妻子是广东最富有、脚裹得最紧的女人。不过,舰长还是鼓足勇气,把我下面说的话翻译完了。广东听众在我参加过的集会中,是最活跃的,这一点从他们爽朗的笑声中就可听出来。在中国,对你的最好评价就是听众的笑声。男人们在会后都涌上来交上一点钱,领一张证明他们是天足会成员的纸。妇女们被涌上来的男人挤了出来,只能站在一旁观看。舰长的妻子瞅准机会,也上前领了一张,还声明说她已不裹脚了。一位老妇人已经70多岁了,她说像她这样的年纪,谁也不敢劝她不裹脚,可裹脚布还是被她扔了。她说刚开始很痛苦,可她愿意成为别人的榜样,现在脚已经不痛了。尽管70多岁了,我们看到她的步履仍然很轻盈。

李鸿章的花园
次日,我们专门为裹脚的妇女举行了一次集会,那天,也正好是李大人安排我去见李鸿章总督的日子。只有9位中国妇女在瓢泼大雨中到会。英国人怕在雨天出门,看来中国人更怕。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因为赶着去见李鸿章总督,我再三道歉后走了出来。我请的这些妇女,她们本可以不来的。现在她们来了,我又丢下她们不管了。9个中国妇女在其他欧洲女士的劝导下,同意加入天足会,并且当场就把裹脚布仍掉了。这样的效果,是我演说几百次也无法达到的。作为宣传废除裹脚的工具,在这场运动中,我其实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坐在漏雨的轿子里,前往李鸿章大人的衙门,街道曲折泥泞,我们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达。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进官宅。衣服被淋湿了,裹在身上又冷又湿,想着马上要被李鸿章大人接见,还真紧张。富尔顿大夫在路上就猜测说衙门一定又脏又乱,破败不堪。现在看来她的话应验了。天气好的话,重重大门后的内宅一定宏伟华丽,气势盛大,我这样想道。
过了一会儿,我们被人领进厢房,同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可大夫会合。我们进厢房前路过一个房间,有一位官员躺在里面,全身盖着毛皮,瑟瑟发抖。不久,李鸿章大人就派人传话说让我们到他那里去。一条长长的走廊出现在眼前,两边是很宽敞的院子,右手是个马棚,里面拴满了马。穿过长廊,我们在接待室门口见到了李鸿章大人。他身材魁梧,将近6英尺高,穿一件镶着貂皮的长袍,一直拖到脚上,头带镶着钻石的黑貂皮帽子,手上套着钻戒。钻戒和貂皮是我的传教士朋友富尔顿大夫后来告诉我的,美国人对钻石和貂皮很敏感,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李鸿章大人犀利的目光和欧洲人一般高大的身材。他和蔼地和我们打招呼,并让我们在屋中央的一张圆桌旁坐下。这位老人自己有一个扶手椅,上面铺了一张垫子,在旁边,有一个随从负责扶他起坐。李大人坐在李鸿章对面,坐在左手的是我和富尔顿大夫。在李鸿章大人右手靠后的地方有一张椅子,马可大夫坐在那里。一排男仆立在墙边,中国街谈巷议的消息均来源于这些男仆们,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密,也是通过他们泄露出去的,这些消息,街上的闲人知道得比外交官还快。
我力图排除任何偏见(可能做不到),但我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大人之前可能从没接见过对他的过去持坏印象的人,我的戒备心在几分钟后开始瓦解,是他的谈笑风生感染了我。此行我要与他讨论的裹脚话题,他总是极力避开。我们还没讨论裹脚问题时,他就问起我丈夫,说见过我丈夫,还把他们见面时说过的话转述给我,并略带微笑地问我,那次会谈的结果我是否还有印象。他说长江水流很急,船在三峡肯定遇到很多麻烦。我鼓起勇气告诉他,汽船已经被我丈夫开到了重庆,当时船上唯一的欧洲人就是我。李鸿章大人说:“你真有勇气。”我答道:“见总督大人需要更大的勇气。”接着,我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并让他收回了话题。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嘀咕着:“不,我不喜欢因为裹脚而让小孩子哇哇地哭,”“可我从没听过她们哭。”他接着这样说道。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家人,以及他的亲戚中已经有许多人不裹脚了。他表示怀疑,不得已我又斗胆提起他母亲。“噢,她不裹脚了,年龄大了,”李鸿章大人说道,“李家的女人我想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我不想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与这位大人物纠缠。李大人这时候很有礼貌地插话道:“我告诉你,我的小女儿现在没有裹脚,将来也不会裹脚。”显然,李鸿章大人认为假装没听见这话更合适,他接着说:“你想让我发布命令,让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我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同一双鞋能穿在全中国女人的脚上吗?不能。你想让我给你写点东西,像张之洞那样?好,你知道,那我得写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又嘟哝着说:“我现在老了,不善写文章了,也写不动了。”我灵机一动,想到如让李鸿章大人在我的扇子题字,对废除裹脚运动也算是一种认可呀!他同意了,这位善良的老人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纪大了,行动有些不便,两个仆人扶着身材高大的他到书桌前为我题词。此后他的题词都被展示在每次集会上,确实极有号召力。我的企图被一旁的李大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很含蓄地对我说他父亲年事已高,很劳碌,如果能写的话,是很愿意为我多写几句的。我们听出了话外之音,知道该告辞了,但总督让我们等一下,他吩咐佣人拿100个大洋送给富尔顿大夫的医院,并对她说不能推辞,一定要收下。他在仔细询问了富尔顿大夫的医院后,趁仆人拿钱的工夫,他又详细地审阅了她的捐助名单。然后转向我说:“你知道,如果让妇女的双脚解放了,她们会因此变得强壮起来,男人已经很强壮了,这样的话,他们会联合起来推翻朝廷的。”他的这句预言,后来在我琢磨他为什么能消除我对他的戒备甚至厌恶时,经常想起。在这个年龄段上,李鸿章大人的思维还如此敏锐,这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佼佼者,何况是中国人呢。他不愿意触及一些敏感话题,可一旦触及,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拉·布赫叶说,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这种态度是非常高明和正确的。很明显,中国人对舌战的偏爱在李鸿章大人身上地地道道地体现出了,他还很幽默,不失时机地和我开玩笑。他说话极具感染力,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对这一点都印象深刻。我想,慈禧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一定很遗憾。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有了隔膜,慈禧心里一定深感惋惜。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有个性魅力的人在身边,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波洛克先生(后任香港执行副检察长)安排了香港的集会,因为有港督夫人布莱克女士的光临,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到会的人物都来自上流社会,市府大厅里挤满了他们的身影。尽管语言上的障碍使得许多人不能畅所欲言,但我们做的一些实际工作,还是感染很多人前来帮忙。一年前,香港也成立了华人俱乐部,其形式和欧洲人俱乐部一模一样。华人俱乐部是今天这场集会的举办方,会前,我们享受到了欧洲人的礼节性待遇,被俱乐部委员会的几位委员邀请去包厢。刚进包厢,里面的中国贵妇们就全体起立,表示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出席集会的还有被称为香港首富的何东先生,为防止出席集会的人因不懂英语而无法尽兴听演讲,俱乐部还专门请了一位著名华人律师充任翻译,翻译还没开始工作,听众的哄笑声和其他迹象就已表明,台下很多人都懂英语,我说的话,听众不会产生误解,这就是翻译要做的工作。我经常提到笑声,这也许有点奇怪,因为在集会上大家所讨论的话题非但不可笑,多少还有点令人伤感。我想,如果人们经常笑的话,可能就会加速他们放弃裹脚的念头。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认为做出悲伤表情是有失体面的。即使是件伤心事,他们的表达方式也不会很直接。他们通常会在宣布死讯时笑。在宁波时,我们路过修女们的驻地,看到5个年轻的姑娘,其中3个还是孩子,另外两个大概20岁。她们的脚因为裹脚烂掉了,只能用手和膝盖行走。这样的惨景如被英国人看到了,一定会长嘘短叹,以泪洗面的,可她们居然能发出咯咯的笑声。
香港华人俱乐部的集会结束后,我们被俱乐部委员邀请到楼上。楼上房间布置得绚丽多姿,既有中国制造的精制广东木雕和大理石盆景,也有欧式的窗帘和扶手椅。在屋中央的桌上放着为我们准备的各色糕点。我们在与一两位中国维新派人物谈话时,得到了前天足会会长的提醒,他说在要求人们放弃裹脚这一问题上不要想得太乐观,据他了解,在一两个鼓掌欢迎解放双脚的家庭中,女眷的脚依然包裹得很严实。在香港我最先遇到的困难是:在这里居住很长时间的居民居然谎称这里的女人大部分都不裹脚。若不是先前的一次经验,我差点放弃举行集会的念头了。那次是与几个朋友去一位中国广东人家做客。主人和一位白胡子客人(来自香港)一听到我的名字,连忙求我们不要到女人们的房间里去。我们由主人的儿子陪同着,在他家里四处走走,正要掉头,帘角一掀,一个女佣人出来请我们进房去。幽暗的房中,一位衣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年轻姑娘被一群女佣簇拥在中间。按照礼节我们向她行了礼,这位姑娘却没站起来迎接我们。女佣们按捺不住了,把她的裙子拉到一边,示意我们看她那双小得难以置信的脚。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的双脚现在一定非常痛苦。我们闯进她的闺房,她很不高兴。我往后退了退,只见她把脸转到一边,弯下腰,对我的同伴又踢又打,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一些对我们极端厌恶的话。我们脸上的惊讶表情一定被仆人们看到了,他们打圆场说这位姑娘第一次看见外国女人,她可能有点不习惯。正说着话,女孩的姐姐走进来了,显然她还没化完妆。她一看到我们,立即跑进房间最暗的角落,把眼睛用胳膊挡住,可能是她不想看到可怜妹妹的双脚,也可能是不想让我们看到她。我立即退出去,请主人的儿子转告我们对两位年轻女士的歉意,我们说冒然进她们的房间,给她们造成不愉快,我们深感内疚,早知道我们的来访如此不受欢迎,我们一定不会来的。主人的儿子丝毫没觉得有什么难堪,似乎认为这是件小事,他告诉我们这两位姑娘是姐妹俩,后进来的是他的妻子,那位白胡子老人是岳父,在香港,他的岳父是拥有最多中国房子的人。对于外国女人,这两位年轻的女士从出生到现在就没有见过。由此可见,中国姑娘在香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港的欧洲人如果不刻意留心,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中国姑娘的生活。汽船的船长也告诉我,中国姑娘坐他的船,都是由男仆们像扛麻袋一样扛上船的。由此可见,前面那些人说香港的女人不裹脚,是带有欺骗性的。刚才到会的满满两屋子人,都是较为富有的家庭,有人告诉我,在这些富有的中国家庭里,女眷们都裹脚。
“看来,我们有必要举行一次上层社会的女士集会。”布莱克女士说。她立刻着手安排这件事情。在香港,中国政府官员的女眷们都还裹脚着,针对这件事,布莱克女士特意向这些官员们发出了请柬,以便他们的女眷能够出席。在此之前,我针对男学生们也发表了一次反对裹脚的演讲,这次演讲由女王学院院长主持。英国政府在中国建立了女王学院,这是对中国最无私的奉献,在这里有无数中国男青年受到了良好教育,在中国各省都能看到这些青年才俊的身影。出席集会的还有维多利亚大主教从他的教区学院带来的一些男学生,在集会上充任翻译的是伦敦教会的佩尔斯先生。有500多个小伙子出席了这次集会,一想到这次集会,我就有点后怕。轿夫们在抬我去集会地点的途中走错了方向,我要去的地点,也没法向他们说明白。最后,一个路人帮助了我们,他懂英语,轿夫们总算弄清我要去哪儿了,可他们不认识路,我也爱莫能助。我被他们抬着在城里转来转去,想着主教、听众和翻译都在等我,心急如焚。到了会场我很羞愧,可没有勇气向大家道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向听众说明了本次集会的宗旨,小伙子们因为等得不耐烦而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笑声,他们的掌声长久地回荡在会场中,我的演讲几乎无法继续进行。像以往一样,我拿出了李鸿章题词的扇子来救场,还免费向听众散发了中国妇女脚部的x射线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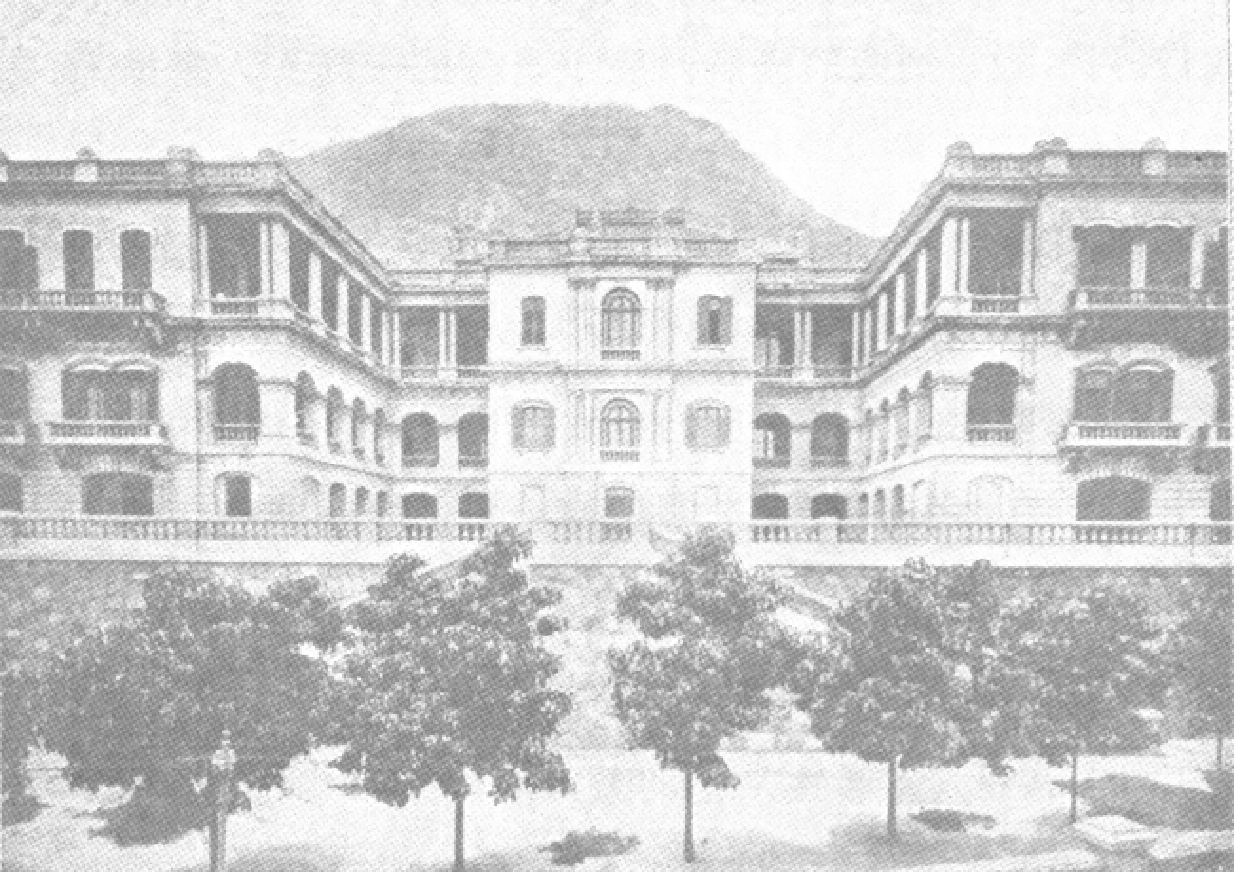
香港的女王学院
片(裹脚和不裹脚的)和宣传手册。年轻人被激活了,他们挤垮了栏杆,冲到前台把手册和照片一抢而光。我虽然没吃饭,但有这些精神食粮就足够了。那个下午,一定会永存在女王学院人的脑海中。
小伙子们的集会完成后,接下来就要安排女士们的集会了。女士们是否能到会,我们事前比较担心。会前一小时,一位女士(英国海军上将的妻子)把自己的脚放在凳子上拍着说:“不来也没关系。”港督夫人说:“噢,她们一定会来的,如果只来几个人,我们请她们去客厅,把舞厅关上。”这时,我同港督女儿布莱克小姐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邀请她担任香港天足会名誉主席一职,她同意就任。在通往舞厅的路旁,园丁已经放上了棕榈树和小树丛,着实漂亮。我们在会前半小时,就几乎已经确信中国女士们不敢来了,即使已经出发,当她们看到有戒备森严的警卫站在大门口时,也不敢进来。可往外一看,她们来了!把轿子停在外面的大门外,她们走了进来,步伐是歪歪扭扭的,场面煞是壮观。舞厅里挤满了人,椅子都被人坐满了。有两三个中国女士凑在一起在一旁嘀咕了半天,其中一位说,当主人在场时,佣人们不应该坐着。听到主人说这样的话,所有的女佣人都赶忙站起来,走到墙边,这样一来就留出了70~80个空位子。至于小女孩就只能坐在地板上,中国人对小女孩们只能坐在地板上感到惊讶,在英国,有孩子坐在地上,大家就不会感到奇怪。有人说这些孩子太小,送她们回去吧,后来还是留下来了。小女孩们在集会结束后都签名加入了天足会,还捐了钱,这令人感到由衷的快乐。有四五个小女孩已经缠足了,这些小女孩一定很清楚她们签名表示反对的是什么,我在心里这样想。有两个脚裹得很小的女人坐在会场前排末尾,这次我们请来的翻译是一位澳大利亚女士,我的开场白和布莱克夫人的欢迎辞在被她翻译完后,可能是无法再忍受眼前这两双小脚,她就走到小脚的主人前面,这样她心里就会舒服点,看不见这两双小脚。听众对翻译的举动较为不满,两位英国女士对听众的反映充满疑惑甚至有点愤怒,于是开始用地道的南方话表示抗议,许多观众被她们的举动吸引,都回头去看。那两位中国女士表现出了超人的冷静,都无动于衷。年龄较大的一位说她都这么大年纪了,拆掉裹脚布,脚也不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年轻的一位为什么不拆裹脚布,我有点不明白。散会后,女主人们在女佣们搀扶下颤巍巍地上了轿子,看到她们这个样子真让人心里难受。在这次集会上,有47位女士加入了天足会,有一位还为大家介绍了她是如何拆裹脚布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在当地一家主要的华文报馆里工作,他向我鞠了一躬说:“我的妻子和姐妹们现在都不缠足了。”一位中国医生曾断言,在香港废除裹脚根本行不通,脚裹得最紧的就是香港女人。事实证明医生的话是错误的。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年,一般都会躺在床上,实在没办法时父母们才把他们抱下床”。

穿着华丽的香港女士
在上海的一次妇女集会上,一位手臂粗壮有力的妇女平生第一次当着大家的面表演裹脚。她用劲实在太大了,裹脚布已经和脚紧紧连在一起,不得已她把脚连同裹脚布一起放进温水里泡,不然的话,解开裹脚布时就会把皮肉带下来。这样的事,有人确实见过。在福州的一次集会上,许多女士都说亲眼看见一个没有双脚的女孩,之所以失去双脚,是因为缠了足。一位中国海军军官的妻子说:“不止这一两个,这样的女孩我看见好几个。”一双脚从坏死到脱落,其间的痛苦真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
“这满屋子中国妇女,如此盛妆打扮,是不是比英国女士强?”有个女士这样问道。英国海军上将的夫人对服饰较有研究,在穿衣方面我们都向她咨询。她说:“我看未必,她们到这里都经过精心打扮,而我们穿的都是便服。我们穿上礼服,佩上珠宝首饰,不会比她们差。”随即,她又陶醉于中国刺绣的精美和丰富的色彩上了。香港的刺绣服装与杭州和苏州的刺绣相比,前者只能算低劣的半成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