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权衡
一、完全依赖法律真实的缺点
法律毕竟不是类似于科学研究那样的单纯认知活动,其实质不单单是对于事实的认知,而是强调合法性评价,它的目的不是追求事实之真,而是追求法律之善。所以,法律真实优先的思维让我们面对一些情况时,即使没有不查明客观真实,也需要作出结论;即使查明客观真实,有时也需要作出相反结论(比如,超过诉讼时效的败诉、非法取证的证据排除等);限制对事实真相的查明;甚至于强调虚构的事实优位于客观的事实等。
秘密收集视听资料的排除规定
视听资料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而诞生的。它以录音带、录像带、激光唱盘、密纹唱片、影像胶卷、电报传真、电话录音、电子或雷达扫描记录、电子计算机软盘贮存的数据和图文资料、电子网络等作为技术设备基础的。其收集的过程无非有公开和秘密两种。不过,何种方式收集的视听资料才具有法律效力,我国诉讼法和其他法律一直未作具体规定。但从立法精神上理解,视听资料的收集一般应公开进行。但是,以秘密方式收集的视听资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以秘密方式收集视听资料,就是制作的一方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针对特定的人制作的证据。比如,利用变焦电视摄像机、增敏传声器、微波装置等各式各样的窃听器,以及或通过电话搭线进行监听等获得的证据材料。对于此种方式取得的视听资料是否合法,各国看法不一,但总的看来,一般都采取了“原则否定”和“例外肯定”的作法。也就是说,原则上都不承认窃听等秘密方式收集视听资料证据的效力。换句话说,以偷录、窃听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视听资料,即使能够反映案件事实的真相,一般也应当认定无效。不过,中国民事诉讼同时吸纳了例外肯定的做法,规定以秘密方式取得的证据,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如侵害隐私)或违反禁止性规定(如窃听),也可作为证据使用。当然,如果是通过侵犯他人隐私或窃听获取的能够反映客观事实的证据,仍然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

法律真实的事实推定机制,是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假设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根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作出相应的法律效果判断。事实上,假设本身肯定隐含着错误判断的风险。当然,从理论上讲,如果指向实现法律真实的事实推定是合理的,那么根据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的拟制,就是合理及正当的;反之,就等于是在法律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让一方当事人承担了不利后果,比如,证明责任之所在往往就是败诉之所在。
进一步而言,法律真实与法律公正的特殊品质相一致,能够符合法律之善,但不代表肯定可以被个人伦理所接受。通常地说,个人伦理的是非判断取决于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实,一旦推定的事实与事实的真相差距甚远,个人伦理往往会发生禁令。可见,法律真实的事实推定,只是对事实状况的或然性所做的盖然性判断,或者是对事实状况的不可解释性的风险所做的分配。虽然它从整体上符合正义的目标,但仍然存在着类似于特殊正义存在的合理性那样的情形。
二、寻求客观真实的补充
有关客观真实的学说,源于前苏联早期,是指案件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的真实。它是把哲学认识论上的实事求是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司法过程中的一切决定和结论都应服从客观真实的指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客观真实的服从是法官的最重要义务。如果服从法律会得出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那么,法官就应当放弃对于法律的服从,以保证司法决定与事实真相的一致性,也就是以寻求客观真实为目的。
一般而言,当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要作出一个违反法律而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无非出现了两种情况:①作出决定的人认为,某一法律制度是不正义的,并且他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来讨论司法公正,因而就不存在法律应当被服从这样的前提。所以,他期待正义的裁判者应当放弃对不义之法的服从,转而去实现那些被错误地排斥在法律之外的正义。②作为决定的人虽然承认所待援引的法律制度的正义,可并不认为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就应当被服从。因此,他对法律的态度是机会主义的,尽管法律制度在总体上合他的意,但他是否会服从法律,仍需看一看待决案件的处理结论是否与客观真实相一致。如果发现一致,他会作为法律的支持者出现;可是一旦发现不一致,他不是试图在制度和程序内谋求一般规则的改进,而是作为法律的反对者出现,为保证结论符合事实的真相而牺牲合法性。[4]可以说,面对上述出现的两种情况,无论是认为法律不正义而放弃服从法律,还是从机会的利己主义角度废法行事,都不符合实现法律之内正义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客观真实虽然失去了王者之尊,但并不代表不该受到应有的关注。尤其是只要不与位阶较高的法律真实原则相抵触,它仍不失为事实认定的一项重要原则。这种情况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刑事诉讼中面对有罪判决时应当抱持客观真实的标准。因为有罪判决涉及人的生命和自由等重要价值,所以,过度推崇法律真实,可能导致冤假错案,产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换言之,诉讼性质对于客观真实的要求,往往会因案件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作出有罪判决。该规定具体表现于有关事实认定的证据上,就是需要构成严密的排他性证据体系。所谓排他性,就是犯罪实施者是谁必须确证无误,而绝不可能是其他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罪认定必须是绝对真实的,可以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能够成为“铁案”。
当前中国五起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
以下的几起发生在当代中国的刑事冤假错案,虽然只是一个中国刑事司法的片断,但都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无可争议的反面典型意义。毫无疑问,因为长期以来片面追求所谓的被告人口供作为最终认定有罪的主要标准,而不是努力让证据体系完全达到“排他性”标准,直接导致一桩桩沉冤的连续发生。目前,到底如何解决冤假错案问题,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
案例一:滕兴善,湖南人,捕前系农民。1987年某地相继发现被肢解的六块女性尸块,当地警方认定石小荣为被害人。而滕兴善则被列为疑犯,滕实在不堪逼供重压而被迫认罪,随后被提起公诉,同年被判处死刑,后被执行枪决。1993年,“被杀害”的石小荣突然回到了贵州老家,并托人告知滕妻。出于惧怕对抗政府,以及其时一双子女尚小,滕妻直到十年后子女成人,才相告这一消息。2005年,滕的女儿提起再审翻案。此时,距滕兴善被执行死刑已达16年之久。
案例二:佘祥林,湖北人,捕前系某派出所治安巡逻员。1994年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后,张的亲属怀疑张被佘杀害。同年,异地发现一具女尸,经张的亲属辨认死者与张在玉特征相符。随后,佘祥林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同样被施以逼供认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佘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检察院也数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一审法院改判15年有期徒刑,佘又再次上诉。此案前后历时5年,佘祥林仍被判决有罪。就在他在监狱服刑11年后,已被判决认定死亡的佘祥林妻子突然归来,佘祥林终获法院宣告无罪。
案例三:杜培武,云南人,捕前系某公安局干警。1998年停在路边的车内一男一女被发现枪杀,死者分别为公局机关领导和干警。此后,女性死者的丈夫杜培武被确定有嫌疑,仍然是被逼供而认罪,可是,对于枪杀凶器及死者身上物品去向始终“交待”不明。然而,杜虽有当庭翻供,一审仍判决其死刑。杜不服上诉后,二审法院因该案有疑点而改判死缓。两年后某劫车杀人团伙案告破,供认上述枪杀案系他们所为。历时2年多,杜培武被无罪释放。
案例四:李久明,河北人,捕前系某监狱干部。2002年一歹徒窜入某监狱家属楼,将宋某夫妇二人刺伤。后被怀疑系李久明所为,因为李此前与宋的妹妹有两性关系,其妹要求李离婚不成,多次到李家闹事。诉讼中李久明被逼认罪,并因此住进了他无比熟悉的监狱。两年多后,浙江温州一名抢劫杀人犯在临行前供认,上述入室杀人案系其所为。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直到中央有关领导直接干预,此案才得以平反。此时,李久明已蒙冤866个日夜。
案例五:赵作海,河南人,捕前系农民。1999年赵振晌与邻居赵作海打架后失踪,一年后淘井时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被疑就是失踪的赵振晌。随后,赵作海被传讯带走。审讯中,赵被逼供承认自己是在赵振晌持刀追打过程中,夺刀将其杀死。有鉴于此,一审法院判决赵作海死缓,赵未上诉。十余年后,一直在外做生意的“被害人”赵振晌突然回村,使得此案掀起狂澜,曾作为无头尸案主案的赵作海终被洗涮罪名。
上面五起案件,也许只是已发生的冤假错案的一个缩影。因为五起错案的被发现,都有概率极小的偶然性,要么是因为“被杀”的被害人重新出现,要么就是真凶的出现和认罪。分析其原因,刑讯逼供恐怕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主要因素,正是刑讯逼供逼出了假口供,才产生了错案。虽然这几起案件中参与逼供的警察大都受到了法律制裁,但关键还在于建立起预防刑讯逼供的机制。其中,针对有罪判决实施排他性的证据标准,而不是轻信被告人口供,就是极其重要的环节。简言之,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要求实现更高程度的客观真实,对于被告人前后翻供、前后供词不一致以及供词存在疑问等情况,同时通过其他证据不能达到排他性标准的,即应当推定无罪或罪轻,而不是用逼供证词作为达到法律真实标准以形成铁案的依据。
当然,刑事诉讼证明具有一定的限度。比如,由于部分案件的各种原因和条件限制,可能根本无法恢复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导致不能确证被追诉者为有罪或无罪;已经侦破的案件,即使查明了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有时也不可能把一切犯罪事实都查清,有些案件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情节根本难以查清。此时,刑事诉讼中适用两种事实推定:一是有罪证据不足的推定为无罪(无罪推定);二是罪轻、罪重查不清的推定为罪轻(罪轻推定)。显然,这两种推定都不是客观真实,而是法律真实。因此,刑事诉讼中把客观真实绝对化是片面的。刑事诉讼中面对有罪判决,只要不与位阶较高的法律真实原则严重背离,还是应当尽可能地趋向于客观真实。换言之,寻求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客观真实,应当被置于相对较高的地位。
(2)行政诉讼中对于行政机关举证应当寻求客观真实的标准。应当承认,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由于诉讼客体的不同,因此在证明标准、举证责任等诉讼规则上也有不同的特点。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涉及当事人财产权、名誉权等权利义务纠纷问题,如果一味追求客观真实,完全不考虑诉讼效率及其他的价值取向,就显得不符合诉讼的实际要求了。但是,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对公民或单位的合法权利是否造成侵犯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举证责任在被告政府一方,被告对公民或单位所作出的处分或处理决定,应当以被证据证明了的客观事实为根据,否则就应当加以纠正。也就是说,这里同样严格适用了客观真实的要求。因为在行政诉讼中强调法律真实,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没有完全查明事实真相就惩罚公民或单位,如此就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孙志刚被害案与废止行政收容遣送制度
2003年3月17日晚,被害人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执行清查任务的广州市某派出所民警收容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3月18日,因孙志刚自报有心脏病,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将其送至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治疗,3月19日晚,因孙志刚向到救治站认领被收容救治人员的家属大声喊叫求助,引起该救治站护工的不满。该名护工遂与其他护工商量,授意8名被收治人员殴打孙志刚,3月20日凌晨,被害人孙志刚遭受轮番殴打,于3月20日上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虽然此案不是行政诉讼案件,但涉及在中国实施了二十多年的行政收容遣送制度。此案经报道后,引起了举国民众的震惊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案发后两个月,五位法学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对本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建议书。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至此,中国施行了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了,这在新中国刑事法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仔细分析,假设没有孙志刚案件演变成为恶性的刑事案件这一契机,再如果案发后没有知名法学家的强烈呼吁,发生在收容遣送过程中的许多行政违法现象仍会反复持续地发生。事实上,以往的收容遣送早已暴露出来不少政府公权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事件,遗憾的是,即使政府在被提起行政诉讼时承担着举证责任倒置而来的举证义务,也由于达到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过低而屡屡轻易过关,绝大多数涉及收容遣送的行政诉讼都是这样不了了之。从法理上讲,当人们受到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实施的侵害时,如果此时的侵害者又是裁判者,则被侵害者将被置于丧失一切防卫手段的危险境地。此时,面对既是侵害者又是裁判者的国家机关,只以法律的真实标准来决定它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显然就会使危险的滑坡效应继续放大,乃至难以覆水。其实,这也是造成长期以来收容遣送制度被广为诟病,以及法学家始终强烈呼吁予以废除的根本原因。而孙志刚案件上升成为刑事案件,正是给了一个必须以客观真实的标准加以裁判的良机。藉此,推动违宪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让人们重拾宪法权威。不过,这种不得不借助偶然事件推动制度变革的现象,是颇为值得深思的。
三、走向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
法律真实抑或客观真实,作为不同类型案件的事实认定目标,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在两种真实之间最有争议的民事案件中,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说,法律真实相对更能得到认同而成为主流学说,这就是法律真实优先的法律思维。
但是,基于法社会学的角度,近年来又出现了“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的提法。所谓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是从当事人对裁判中事实认定的信赖程度来评估诉讼中的真实。也就是说,不仅应从国家的立场或者从维护民事法律秩序的立场,来看待事实认定的真实问题,而且还应当符合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利益,毕竟赢得当事人的满意才是最重要的。说到底,值得当事人信赖的事实归属于法律真实,它不是以追逐客观真实为目标,而是认为应当更多考虑从当事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不过,现代当事人对于真实产生信赖感,绝不仅是像过去那样单纯地依靠尊重程序选择权、防止诉讼突袭等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置于一个具体的语境中,作出更为实质性的权衡判断。
那么,这个具体的语境是什么?社会学理论认为,整体社会可分为互动、组织和社会系统。就社会系统而言,当今世界从能源危机到金融风暴,从气候变化到粮食短缺,从信息安全到恐怖袭击等,已经出现贝克(Ulrich Beck)意义上的“风险社会”。[5]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无论是宏观的物价上涨、食品安全、房价高企、医疗改革、失业率上升,还是微观的歧视待遇、谷贱伤农、拆迁纠纷等,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所蕴含的风险,也都让人们充满了不确定性,以及承受较大的压力,社会性不满情绪正在积累,一旦超出了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容忍与接受程度,比较严重的危机事件就可能发生。显然,风险社会离世界和中国不再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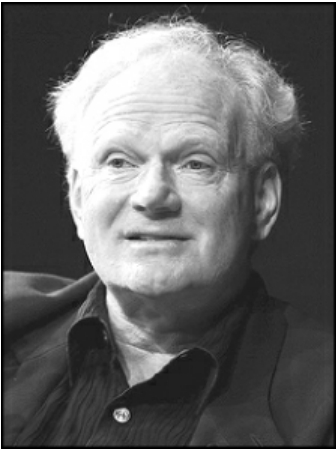
乌尔里希·贝克
处于风险社会这个具体的语境,法律思维是继续固守既有的核心价值,还是接纳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何去何从的抉择问题日益凸显。不过,无论采取的是什么立场,更加关注于实质判断都成为一个核心。从事实认定的角度,这个实质判断不是寻求客观真实或法律真实,而是如何取得当事人的信赖。其原因在于,试图取得当事人信赖的实质判断,仍然单是依靠那种简单地指向法律真实或客观真实的做法,已经无法像万能钥匙一样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矛盾与交错的利益诉求,有效解决风险社会中由于体制、政策和制度带来的许多问题,反而可能助长价值倾向的保守性,抑或诱发新型的全能主义。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现实的法律治理演绎成为一个“正”高于“善”的局面。其中,现代法律所塑造的只是分不清个体属性差异的拟制人格,无法承担公共的、道德的责任和促进社会团结,因而现实的制度运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少问题。
面对这一困境,理念的转向正在发生。价值同盟、交叠共识、民主商谈、实践理性、后果论辩主义、合理性证成、疑难案件讨论等“合唱般”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不言而喻,理念层面的地壳变动,重新突出了多元价值的实质判断。显然,法律的制度治理涉及对多元价值的实质判断,至少可以提醒既有的制度安排应该被不断审视,使得固执于某种实质性价值的态度能够适当相对化,以增强反思的理性。比如,中国这种多元价值的实质判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开始破除过去阶级意识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出了差别化对待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重新划分社会十大阶层以及赞同中国已出现利益集团,进而让整体社会的利益需要趋于割据化和碎片化。客观地说,这种趋向于实质判断的思维正在成为主流思想,乃至开始左右制度设计,前一章所提到的特殊正义的实现就是脚注。在这种背景下,固守事实认定目标的单一化,只会与防范社会风险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现代制度的重新设计,尤其需要以围绕多元的价值加以实质判断为前提。显然,事实认定只是依靠法律真实或客观真实的博弈,已无法彻底解决问题,而是应走向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
那么,当事人信赖的事实如何获得?处于风险社会压力之下的法律发展,如何获得当事人信赖的事实,将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一方面,那种单纯从社会利益出发的立场,可能会割裂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情境,片面把社会利益视为一个抽象概念,而风险情境下的社会利益在每个案件中的具体指向都可能有所不同。相反,风险社会下的整体利益本身所包容的多元道德观念,反而会成为随意放大或缩小当事人所处情境理由强度的借口,造成得出的结果表面公平,但实质不公正。另一方面,拘泥于从当事人利益出发的观点,同时也难以从宽阔的视野上结合风险社会的复杂性作出恰当的判断。尤其是当现实的立法或司法陷入对当事人双方具体利益的细微衡量后,极易导致利益的取舍陷入“保护谁的利益可以或不保护谁也可以”的尴尬境地。显然,有关事实认定那种“绝对化”地从所谓的整体社会利益出发的权衡,抑或围绕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的权衡,都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为了获取让当事人信赖的真实,需要结合证明责任、具体情境乃至环境证据等方面作出更为周全的综合思量。
龚如心争夺遗产案让当事人信赖的真实
香港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是1990年遭绑架而失踪的香港地产商王德辉之妻。1999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宣告王德辉在法律上死亡。王德辉曾于1960年、1968年各订有一份遗嘱。王德辉之父王廷歆要求法院确认王德辉在1968年所立的指明其为遗产唯一继承人及执行人的遗嘱。而龚如心则向法院提交了据称是王德辉1990年所立但从未公开的第三份遗嘱,声言将所有财产留给妻子龚如心,并有王家当时管家谢炳炎的见证签名,但谢炳炎在出具证言后不久即病逝。
2001年8月6日,争夺遗产案正式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法律,若死者生前先后订立遗嘱,则以后者为准。因此,这场争产案的关键,即为确定龚所持1990遗嘱是否真实。翁媳对王德辉遗产的争夺形成了两大“战场”:一场是以争论遗嘱有效性的民事“争产案”,另一场则是司法部门对龚如心是否伪造文件的刑事调查。2002年11月,高等法院原审法庭判定龚所持1990年遗嘱为伪造;2004年6月,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裁定龚上诉失败。然而,这场涉及绑架、隐私、遗产争夺的豪门恩怨最终峰回路转。2005年9月,终审法院法官对世纪争产案作出最终判决,出人意料地推翻此前判决,一致裁定王德辉1990年遗嘱为其生前最后遗嘱,宣告龚如心胜诉,为这位“亚洲最富有的女人”平添近400亿港元的遗产。
其实,龚如心只需证明1990年遗嘱乃王德辉订立即可。但是,一、二审法官却要求龚如心举证推翻其所持遗嘱的多项疑点,尤其是法官根据环境证据所做的不利推定。比如,法官认定龚如心所持1990年遗嘱为假的依据在于,王德辉在该份遗嘱第二、第三页表达了对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失望”,禁止龚将遗产分与他们;最后一页,则仅有王对龚的一句表白“one life one love”。一、二审法官认为:王德辉一向家庭观念很强,与家人关系很好,应该不会说出对家人“失望”的话;而且王德辉经商多年,生活情调并不浪漫,不会写出这样情感过于直露的话。
而对作为终审的三审法官来说,为了获取让当事人信赖的真实,他们转而对证明责任、具体情境乃至环境证据等方面进行了颇为周全的综合思量。①从证明责任而言,龚如心只需证明1990年遗嘱乃王德辉订立即可,而王廷歆既然对儿媳龚如心所持遗嘱为假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②应当综合考虑龚如心与丈夫婚后感情的情况,以及王德辉与王廷歆的关系变化情况,这对分析遗嘱发生逆变的原因,以及判断1990年遗嘱的真实性是有作用的;③证人谢炳炎尽管未能出庭作证及接受质证,但其生前提供的证词前后一致,称自己曾亲见王德辉在1990年遗嘱上签字并要求自己作为见证人,证词清晰无可置疑。
【注释】
[1]Eric Lode,Slippery Slope Arguments and Legal Reasoning,California Law Review Rev.Vol.87,1999.
[2][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3]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18页。
[4]郑成良:《法律之内的正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16页。
[5]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在他的代表作《风险社会》中,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1)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2)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所以,现在的风险与古代的风险不同,是现代化、现代性本身的结果。风险社会的风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和技术的,如核技术的、化学的、生物的风险。这些风险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为的风险,这种风险与以前的自然风险明显不同。从性质上讲,这种风险是网络型的、平面扩展的,不放过任何人;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包括法律制度的各种社会制度运行的共同结果;而从应对方法上,现有的风险计算和补偿方法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反思能力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可以说,风险社会为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为我们反思当代世界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贝克风险社会的两本经典是:Risk Society:Toward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World Risk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这两本书都同时被翻译成为中文:[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