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J·伯尔曼:【1】
《法律与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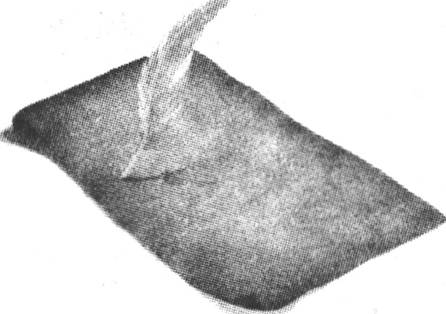
■ 本书精要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一书面世后,立即引起英美等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甚或激烈的争议。但总的说来,该书的重要价值及其巨大的包容量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肯定,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认为:“该书篇幅宏大,视野开阔,细节丰富,这可能是我们的时代最主要的法律著作。”由于美国律师协会的推荐,该书荣获1984年度法律学科最佳图书奖(Scribes Book Award)。【2】
■ 作者简介
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 Berman)1918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938年获达特茅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42年和1947年先后获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和法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基督教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和1997年先后被弗吉尼亚神学院和比利时根特大学授予希伯来文学博士学位。
1938年,伯尔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法律史专业,尤金·罗森斯托克·胡塞、R·H·托尼和T·F·T·普拉克内特这三位“伟大的欧洲人”对其影响甚大。据伯尔曼自己介绍,《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一书正是建立在他们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3】此后,伯尔曼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执教长达37年,后为哈佛大学詹姆斯·巴·阿米斯讲座名誉法学教授),曾在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做过访问学者,于1962年和1982年两度在莫斯科大学讲授美国法律。近年来,因贸易事务和教研工作曾多次往返于美俄两国之间。1985年迄今,任美国埃莫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罗伯特·W·伍德洛夫讲座法学教授、埃莫里大学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学术会议研究员、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作为比较法律史、法理学、苏俄法、国际贸易法以及法律与宗教方面的权威人士,伯尔曼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地广泛地进行了讲学活动。他是莫斯科美国法律中心的主要创立人(该中心是埃莫里大学法学院与俄罗斯司法部下属的法学会合作的产物,从1991年以来,已举办了三届为期两年的美国法律讲座)。同时,他还是创办于1997年的世界法律协会的主席之一,该协会旨在开展有关世界经济、世界组织以及人类共同关心的诸如环境保护、跨国冲突调停和人权问题等方面的法律教育活动。
伯尔曼堪称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5月,他已先后创作了约21部著作,300多篇专业学术论文(含合著)。其中,《法律与宗教》(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和谐》(Faith and Order: The R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等被认为是其代表作。【4】尤其是《法律与革命》这部据称是在长达45年之后(1938—1983)方得以最终问世的呕心沥血之作,在1983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奠定了伯尔曼在法理学、法律史学等领域的权威地位。
由于伯尔曼的两部代表作均有中译本,故而中国读者对于伯尔曼其人及其主要思想并不陌生。因此,相关中译者所做的出色工作亦可谓功不可没。
20世纪70和80年代,在美国先后有两部关于西方法律传统的著作问世:其一是泰格、利维二人合作的《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其二就是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
伯尔曼是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论述自己的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观的:其一是教皇革命与教会法,其二是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前者被刻意安排在第一部分,孰轻孰重,自然不言自明。
法律与宗教是伯尔曼一再予以论述的一个主题。如何摆正两者的关系,伯尔曼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在西方社会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械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宗教信仰……则会蜕变为宗教狂热。”【5】
伯尔曼在论述西方法律传统时最引人注目,同时又最引发激烈争议的,莫过于他的危机论。他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像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在20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我们整个的法律传统都受到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制的结构。”【6】据此,他列举了种种令人堪忧的现象,并指出西方法律传统的10个特征中后6个特征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美国全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他着重谈到了“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今天都受到了对法律玩世不恭态度的威胁,这种态度导致了各阶层人们对法律的蔑视”【7】。在他看来,西方法律传统的崩溃,部分地应归因于1917年10月始于俄国并逐渐传遍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多地则是来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危机。而这种传统基础的崩溃不可弥合,因为,对这些基础最大的挑战是人们对作为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共同体的西方本身的信念和对9个世纪以来维系西方文明的那种法律传统普遍丧失了信念。因此,他呼吁:“我们必须调动整个传统的应变能力来克服这种危机。”【8】所以,强调尊重传统,倡导信仰法律以克服西方法律传统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应当是伯尔曼殚精竭虑地写作《法律与革命》的一大动机。
■ 内容概述
《法律与革命》主要由导论、第一部——教皇革命与教会法(内含7章)、第二部——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内含7章)和尾论四个部分组成。
在这部洋洋70万言的巨著中(据中译本),伯尔曼讲述的是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的西欧在昔日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建法律的历史,由此展示了作者对于西方法律传统深入的探究、全面的把握和独到的见解。
在序言的开篇处,作者写道:这是一部关于起源、“根源”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路线”即我们借以到达今天的路径的历史。作者的动机则在于:从遥远历史的视角,从头考察西方的法律与法制、秩序与正义的传统,以便找到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也正是在《法律与革命》的序言中,伯尔曼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综合法学的观点(即综合“法律实证主义”和“历史法学派”与“法的社会理论”、“自然法理论”这三个传统学派,并对其有所超越),对法律概念的狭隘性(即把法律主要看做在某个特定的国家生效的一大堆立法的、行政的和司法的规则、程序和技术)进行了批判。
一、导论
导论部分(中译本约5万字)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伯尔曼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理解以及他的法理学观念。
关于“西方”(“the West”),伯尔曼的定义是: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诸民族(西方信奉伊斯兰教的部分不包括在内)。【9】
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10个方面:
①在法律制度与其他类型制度之间有较为鲜明的区分。虽然法律受到宗教、政治、道德和习惯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分析,可以将法律和它们区别开来。
②与上述这样鲜明区分相关联的是以下事实: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施行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
③法律职业者都在一种具有高级学问的独立的机构中接受专门的培训,这种学问被认为是法律学问,这种机构具有自己的职业文献作品、职业学校或其他培训场所。
④培训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有着复杂的辩证的关系。换言之,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做的阐述。法律本身包含一种科学,一种超然法(meta-law)——通过它能够对法律进行分析和评价。
⑤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
⑥法律实体或体系的概念,其活力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的特征即它世世代代发展能力的信念,它是一种在西方所独有的信念。法律体系只因其包含一种有机变化的内在机制才能生存下来。
⑦法律的发展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变化不仅是旧对新的适应,而且也是一种变化形式的一部分。法律不仅仅是在不断发展中,它有其历史,它叙述着一个经历。
⑧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即使处于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也一直被广泛讲述并经常得到承认。
⑨西方法律传统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是这种司法管辖权和法律体系的多元性使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
⑩西方法律传统在思想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以及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革命对法律体系周期性剧烈冲击。但是,这种法律传统毕竟存活了下来,甚至由这些革命所更新,这种法律传统比作为它组成部分之一的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要大。【10】
不过,根据伯尔曼的说法,西方法律传统的10个特征中只有4个,即前4个仍然构成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另外6个特征则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美国全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一)法律与历史
伯尔曼宣称:相信并接受关于西方法律传统的这种历史,必须面对不再被广泛接受(至少在各大学是如此)的关于法律和历史的固有理论。因为,“这种流行的理论成为理解这个历史严重的障碍”。
在伯尔曼看来,认为法律是来源于制定法和法院判决的规则体系的这种传统的概念(即把立法者“国家”意志作为法律最终渊源的理论)完全不适合于探讨跨国的法律文化。
在这里,伯尔曼对于所谓“盲目的历史循环论”展开了批判,并认为在20世纪后期,我们仍然受害于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法,这种编纂法起源于19世纪,它赞成对西方共同遗产予以肢解。【11】
(二)法律与革命
伯尔曼的一大贡献就是他将“革命”模式用于解释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
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在其历史过程中已经由六次伟大的革命加以改造(这六次革命依次为教皇革命、新教改革运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其中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是《法律与革命》一书研究的主题)。“革命”一词不仅用于指新体制借以产生的最初暴力事件,而且也指体制得以确立所需的整个时期(这里,“暴力”是指个人和集团对既定权力机构实施的非法暴力)。
六次重大革命是“全方位的”革命,因为它们不仅涉及创设新的政府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结构,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新的法律结构,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视野,新的历史前景,以及新的一套普遍价值和信仰。及时变革是所有面临不可抗拒变革压力的法律制度获得生命力的关键。
伯尔曼指出,未预见到根本性的变革并没有及时实现这些变革,可能是由于西方法律传统性质中一个固有的矛盾,即它的目的之一是要维持秩序,而另一个目的是旨在实现正义。【12】
(三)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
探究伯尔曼法律理论的思想根源,也许应当从他的最引人注目,同时又最易引起激烈争论和异议的观点即他关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论入手。
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部分地归咎于1917年10月始于俄国并逐渐传遍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更多地归咎于来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危机。且这种传统基础的崩溃不可弥合。因为人们对作为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共同体的西方本身的信念和对9个世纪以来一直维系着西方文明的那种法律传统普遍丧失了信心,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人们对法律的蔑视和对法律玩世不恭的态度。
(四)走向一种法的社会理论
伯尔曼认为,19世纪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致力于贬低、否认和无视近代西方的制度和价值在前新教时代、前人文主义时代、前民族主义时代、前个人主义时代和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深厚根基;它们全部试图掩盖发生于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西方历史的断裂。伯尔曼的观点是:至少不能只把西方历史中的法律完全归结为产生它的社会物质条件或观念和价值体系;还必须把它部分地看做社会、政治、知识、道德和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不仅仅是结果之一。【13】以此为出发点,伯尔曼指出:
今天法的社会理论的首要任务旨在摆脱关于法律及其因果关系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应该把三个传统的法学派(即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理论和历史法学派)综合成一个一体化的法学。
法的社会理论的第二个任务是旨在采用一种适合于法律史的历史编纂而不是主要采用来源于经济史、哲学史或其他史类的历史编纂法。
当代法的社会理论的第三个任务是研究法律在革命变革时期的命运。
最后,法的社会理论还必须研究非西方的法律体系和传统,研究西方法律与非西方法律的融合,研究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摆脱20世纪后期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之路。【14】
二、教皇革命与教会法
(一)西方法律传统的背景:民俗法
伯尔曼认为,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们今天统称为法律体系——被有意识地加以系统化的、独特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的东西,在西欧各民族中并不存在,只是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早期及此后,各种法律体系才首次在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各王国、城市和其他世俗政治体中被创立出来。这正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论题。
就存在依法设立的适用法律的官方机构而言,在11、12世纪以前西欧的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某种法律秩序。然而,在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以前这一阶段,西欧各种法律秩序中被使用的法律规则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习惯、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并无差别。
伯尔曼指出,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上述状况发生了梅特兰所谓的“不可思议的突发”。专职法院、立法机构、法律职业、法律著作和“法律科学”,在西欧各国纷纷产生。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主张教皇在整个西欧教会中的至上权威和主张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这是一场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革命,为此,教皇派和皇帝派之间进行了约50年的血战一决雌雄,而大约100年后的1170年——托马斯·贝克特殉难,才标志着在英格兰达成最终妥协。在随后的世纪里,欧洲各民族的民俗法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新的、复杂的法律体系——教会法、城市法、王室法、商法、封建法和庄园法——先后为教会、世俗政治体所创立。16—20世纪,一系列伟大的革命改变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把它的日耳曼“背景”远远地抛在后面。
伯尔曼强调,特别是在当今,在20世纪最后这个时期,当西方不再像从前那样确信自己的法律传统的时候,回顾这种传统最初所替换的东西尤为重要。而且,日耳曼法并没有整个被否定,被否定的部分也没有马上消除。因为,新的法学不是凭空的创造。日耳曼法为取代它的新法律传统(注:指形成于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的西方法律传统)提供了新的基础。【15】
(二)西方法律传统在教皇革命中的起源
在11世纪以前的西欧各民族中,法律不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调整体系或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而存在的。而在11世纪晚期、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的西欧,无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法律还是作为一种智识概念的法律,其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法律被发掘了出来。政治和知识两方面因素的结合,有助于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产生。其中首先有助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新教会法体系的产生。
各种宗教因素也起了作用。近代法律体系的创立首先反映了教会内部和教会与世俗当局关系上的革命性变化。这里,“革命”一词具有整个近代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暴力的含义。【16】
在11、12世纪中出现的新的社会意识的三个方面,即关于僧侣的社团共一性的观念,关于僧侣有责任改革世俗界的新观念,以及包含了近代性概念和进步概念的历史时代的新观念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发展都具有强烈的影响。
教皇革命导致了近代西方国家的诞生——第一个悖论性的例子就是教会自身。因为,近代国家与古代国家以及日耳曼或法兰克国家的区别是它的世俗特性。而教会在一段时间内,行使着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它坚持教会法这样一种理性的法律制度体系。一个人实际上可以因为开除教籍而被剥夺公民权。教会有时甚至还建立军队。【17】
教皇革命也导致了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产生。第一个近代西方法律体系就是近代的教会法体系。教皇革命还形成了教会法体系和世俗法体系的二元格局,导致了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的管辖权。教皇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它把革命经历自身引入西方历史。伯尔曼的结论是: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西方法律不仅与较早的西方民俗法形成对比,而且也与查士丁尼以前和以后的罗马法形成对比;它被想象为一种有机发展的体系,一种不断发展或生成的原则和程序体系;它的建造——像大教堂一样——跨越了几代人和数个世纪。【18】
(三)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
伯尔曼认为,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出现是与欧洲最早的一批大学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在那里,西欧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亦即一门科学来讲授。经历了新的法律科学训练的一代又一代大学毕业生进入正在形成中的宗教和世俗国家的法律事务部门和其他官署中担任顾问、法官、律师、行政官、立法起草人。他们通过运用其常识赋予历史积累下来的大量法律规范的结构和逻辑性,从而使各种新的法律体系得以从以前几乎完全与社会习俗和一般的政治和宗教制度混为一体的各种旧法律体系中脱胎出来。【19】
在这一章里,伯尔曼对于近代欧洲最早的大学波伦亚法学院、其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经院主义与希腊哲学和罗马法的关系、经院主义辩证法在法律科学中的应用、作为西方科学原型之一的法律等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评价。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科学在其形成时期的主要社会特征,尤其是作为受到大学影响时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如大学帮助西方法律科学成就了一种跨国家的特征等。
(四)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
伯尔曼宣称:假如不去探讨西方法律传统的宗教方面的话,要理解这一传统的革命性质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为法律类推和法律概念奠定基础的法律隐喻首先是宗教性质的。它们是最后审判和炼狱的隐喻、在补赎礼中罪过得到赦免的隐喻、教士的“捆绑”和“释放”即施加或减免永罚的权柄的隐喻。其他一些法律隐喻主要是封建性质的,虽然其不乏宗教性质——它们是荣誉、对损害荣誉的赔偿、信仰誓言、服务与保护的双方互利契约等隐喻。所有这些隐喻都是礼仪与神话的统一结构中的组成部分。【20】西方法律科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它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没有意义,是因为它的神学前提已不再被人们所接受。当这些历史根源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候,法律的许多内容便显得缺乏基本的有效性资源。【21】
(五)教会法: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
伯尔曼认为,断言教会法的体系是在1050—1200年间被创造出来(抑或教会法律走向系统化),并不否认有一种法律秩序从教会建立的早期起便存在于其中。早期的教会法,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受到了罗马法的深刻影响以及《圣经》尤其是《旧约全书》的深刻影响。此外,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教会法律的系统化在所有方面都与教皇革命密切相关。【22】
在这一章里,伯尔曼先后探讨了教会法与罗马法的关系、教会法体系的宪法性基础、作为教会宪法的社团法、对教会管辖权的限制等,并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例如,他认为罗马法与教会法之间最重要的差异或许是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极有限的例外,前者被视为已经完成、不可改变的,是只能重新解释而不能予以变化的东西。后者则不尽然;又如,关于教会法体系的宪法性基础,伯尔曼的结论是:教会是一个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与此同时,对于教会权威所进行的限制,培育出了某种超过法治国意义上依法而治的东西。这些东西更接近后来英国人所称的“法的统治”(“the rule of law”)。【23】
(六)教会法律体系的结构要素
伯尔曼认为,12和13世纪的教会法缺乏抽象,也很少“逻辑化”。它的范畴生成于教会法院的管辖权,生成于教会法院所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来自学究气法学家的纯理论推理。法律的次级体系也出现了,尽管其还不具备后来所发展出来的那般高度的自主性和学说上的一致性。【24】
本章主要讲述:教会婚姻法、教会继承法、教会财产法、教会契约法、诉讼程序、教会法的系统化特征。
(七)贝克特对亨利二世:并行管辖权之争
本章主要讲述:《克拉伦登宪章》(1164年由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僧侣权益和双重危境、英格兰的教会司法管辖权、禁止令状等。
伯尔曼认为,从12世纪到16世纪,教会法院与王室法院抗争之根由,在于限制各方的司法管辖权。【25】关于12世纪晚期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之间的冲突(贝克特在1170年被国王的4名役从谋杀,此事震动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以致亨利裸足步行到坎特伯雷表示赎罪),伯尔曼的看法是:其实质是一种关于教会司法管辖权范围的冲突;它因而成为教皇革命的一个范例,这一革命在整个西方建立了两种相匹敌的政治法律权威类型,即精神的与世俗的权威。这种二元主义的后果之一是增强了国王在俗界的政治法律权威;后果之二则是造成了国王与教皇之间在司法管辖界限上的某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不同的王国以不同的方式解决。在英格兰,它们的解决受到贝克特殉难氛围的强烈影响。【26】伯尔曼认为,教会法院与世俗法院之间的抗争对西方法律传统具有深远的影响。复合的司法管辖权和复合的法律体系成为西方法制的一个标志,贝克特的传统仍遗留至今。
三、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
(一)世俗法的概念
伯尔曼认为,教皇革命使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教会国家和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教会法体系首次形成。与此同时,它也使各种不具有教会职能的政治实体和各种非教会的法律秩序首次形成。教皇党把这些非教会的政治实体及其法律称作“现实的”(受时间束缚的)和“世俗的”(尘世的)。【27】
世俗法被期待去模仿教会法。因为教会法有更高程度的发展并可以加以模仿,所以各种世俗法——封建的、庄园的、商业的、城市的、王室的——才使教会法的许多基本概念和技术成为适合于它们自己使用的东西。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12和13世纪,绝大多数的法律家、法官以及世俗法律制度中的其他专职顾问和官员都是僧侣,他们或者受训于教会法,或者在总体上熟悉教会法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世俗当局也抵制教会当局侵犯世俗管辖权。因此,它们也寻求使世俗法取得像教会法那样的内聚性和精致性。每一种不同类型世俗法的发展,部分在于对教会法的模仿,部分在于同教会法的抗争。它最终都被人们看做是一种法律体系。所以,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法概念,每一种法律体系在范围上都限于特定种类的现世事务,它产生于习惯,虽不完美无缺,却为神所指定,并按照理性和良心获得纠正。【28】
(二)封建法
伯尔曼认为,“封建主义”这一术语在18世纪才被发明出来。自12世纪以来,人们所说所写的不是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而是“封建法”,主要指的是与领主——封臣关系和依附性土地占有权相联系的权利义务关系。【29】在1050年到1150年这一个世纪里,封建主义在西方得以合法化,因为封建法和庄园法在这时第一次被想象为与属于它们自己的一种生活相结合的法律体系,通过它们,封建关系和庄园关系的所有方面都获得了自觉的调控。【30】
伯尔曼断言,封建法与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新的教会法共有许多基本的法制特性,这些特性给处于形成阶段的西方法律传统打上了烙印。然而,较之于教会法,封建法在系统性、自觉意义上的完整性、专业性和精确性这四个方面都更逊色。【31】
(三)庄园法
伯尔曼认为,直到11世纪,庄园经济才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像规定封臣与领主关系和独立的土地占有权的封建法一样,调整领主与农民关系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庄园法也开始形成一种法律体系。这两种法律体系彼此紧密联系。它们也与同时代发展的商人法、城市法和王室(普通)法诸体系有着并不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世俗的法律体系与教会法体系密切联系,它们全部都是整个构造过程即西方法律传统的组成部分。【32】
(四)商法
正如封建庄园法的情况一样,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也是商法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那时,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那时,商法在西方才第一次逐渐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看做是一种法律体系。【33】
本章主要讲述:宗教和资本主义兴起、新商法体系(其中包括客观性、普遍性、权利的互惠性、参与裁判制、商事法院、商法的整体性、商法的发展性)。
(五)城市法
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在西欧涌现了约数千个新的城市和城镇。不论它们的特性如何多彩纷呈,它们都具有作为城市共同体的一种共同的自我意识,并且它们都拥有相似的法律制度:都由一套城市法律体系来治理。【34】
本章主要讲述:近代城市兴起的原因、西欧城市和城镇的起源、行会和行会法、城市法的主要特点、作为一种历史共同体的城市。
(六)王室法:西西里、英格兰、诺曼底和法兰西
教皇革命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一种新的王权概念。国王不再是教会的最高首脑了。“神圣王权”,的时代逐渐结束。【35】伯尔曼认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于11世纪晚期、12和13世纪涌现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共同体,即世俗领地王国,概括起来,它有9个重要特点。这些新型王权的一般特征,在西方各国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36】
本章主要讲述:西西里的诺曼王国、英格兰、法兰西。
(七)王室法:德意志、西班牙、佛兰德、匈牙利和丹麦
伯尔曼认为,在每个王国或王侯领地里,王室法和教会法以这样一种方式互补,即它们被说成构成了一个单一法律秩序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具体而言:①教会法和王室法皆行使有限的权能和有限的管辖。②上述两者皆植根于一种它们从中寻求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外在的法律渊源的权威。③两者都是成体系的。教会法的系统化程度要高一些,它甚至比复兴的罗马法更为系统。④王室法和教会法还受一代又一代自觉成长原则的支配。⑤两者都证明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一切法律本身都含有某种与正义相一致的目的;这些内在的目的要指导法律规则和技术的解释和运用。【37】
本章主要讲述:德意志、西班牙、佛兰德、匈牙利和丹麦、王室法与教会法。
四、尾论
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是反对皇帝、国王和领主控制神职人员的革命,是旨在使罗马教会成为一个在教皇领导下的独立的、共同的、政治和法律实体的革命。……一言以蔽之,教皇革命具有全面变革的特性。它不仅构想了一个新天堂,而且也展示了一个新的尘世。授职权之争只是它的一部分,格列高利改革也只是它的一部分。【38】
显然,伯尔曼对于所谓民族主义的偏史方法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于法系的划分,伯尔曼也无意赞同。伯尔曼指出,除了民族主义的谬误之外,包括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在内的宗教也难逃其咎。同时,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亦在其否定之列。出现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另一种历史编纂即所谓“社会经济史”或称“社会理论”由于同样“掩盖了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历史”,也在伯尔曼的批判之列。伯尔曼断言,法律实质上既是物质的又是意识形态的。只有将实证法学、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这三种观点结合起来,方可对马克思和韦伯提出的问题,给予比他们更好的回答。
■ 简要评价
《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伯尔曼将“革命”模式用于解释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他关于基督教会及神学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理论。伯尔曼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西方法律的形成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这200年间,并且将教会与世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作为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本因素。
伯尔曼在法学领域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1.其在苏俄法领域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苏俄宪政、军事法律、经贸法、民商法、刑事法律、外交与领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国际法乃至行政法等。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俄罗斯的司法制度:苏维埃法释义》、《苏联的军事法律及其实施》(合著)等。
2.综合法学思想。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呼吁应将历史法学、实证法和自然法学这三个传统的学派统一起来,综合成一种一体化的法学,并强调此乃法的社会理论的首要任务。
3.对于西方法律传统长期的探讨和独到的见解,这方面的代表作当首推《法律与革命》。【39】
4.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论述。在当代西方法学家中,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与宗教(基督教)的关系论述较多,这也因此构成了他的学说体系的一大特色。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伯尔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人类学研究表明,在所有的文明中,法律与宗教共享四个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40】。至于如何摆正两者的位置,伯尔曼认为,答案就是在西方社会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
5.关于世界法律的构想。实际上,关于世界法律的构想在伯尔曼的著述中早已有之。但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一篇题为《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World Law in the New Millenium)的访谈录中。【41】伯尔曼认为,世界法传统正在形成,它是融合全世界东南西北各色各样文化的不同传统而成的。一场赋予正在出现的世界法传统具体形貌的革命已经在进行。伯尔曼断言,建立跨国界、跨文化的法律体系不仅可能,而且已经在进行,只差尚未名之为“世界法”而已。伯尔曼构想的世界法不仅包括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国际公法,而且也主要包括跨国社会团体的习惯法。其中,最明显的是国际经济法。
《法律与革命》一书面世后,在美英等国学术界引发了极大的关注甚或激烈的争议。褒奖者认为,伯尔曼对于“革命”模式的运用本身便具有革命性意义;批评者则认为,“革命”模式限制了他的视野,使他对11世纪之前西方的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的发展估价不足,并且作出了某些值得商榷的历史概括。但是,总的说来,该书的重要学术价值、独到的见解及其巨大的包容量还是得到了学术界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例如,美国学者、旧金山大学法学教授威廉·W·巴赛特的结论是:“恰当地说,伯尔曼已出人意料地修正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他的这本书代表了一种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知识上的成就。”【42】
伯尔曼的法律思想尤其是他关于西方法律传统的整体性观念、多元政治的并存、竞争与演变、宗教与法律的互动关系、“革命”模式的运用以及颇具争议的“危机论”等等,所有这一切,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于西方法律制度和文化的进一步探究和思考,在分析、批判和借鉴的层面上,相信亦不无裨益。例如,伯尔曼有关“革命”的学说已为我国某些学者认同和借鉴。
(郭义贵)
参考文献
1.〔美〕威廉·巴赛特著,阮齐林译:《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探究》,《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4期。
2.〔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林立伟译:《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香港《二十一世纪评论》,1999年第4期第52号(总)。
3.徐爱国、李桂林、郭义贵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5.〔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阿宾顿出版社1974年版。
注 释
【1】 《法律与革命》已有中译本,译者: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以下相关评价将以上述中译本为主要参考文本。
【2】 《法律与革命》(1983年)英文版封底。另,该书英文版截止到1995年已第8次印刷。
【3】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9页。
【4】 《法律与宗教》已有中译本。最新中译本请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梁治平译)。
【5】 〔美〕哈多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英文版),第47页。
【6】【7】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46页。
【8】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9】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0】【11】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18—20页。
【12】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7页。
【13】【14】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1、51—53页。
【15】
【16】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0、101—103页。
【17】【18】【19】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37、139—142、143页。
【20】【21】【22】【23】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201、242—245、259页。
【24】【25】【26】【27】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326、316—317、331页。
【28】【29】【30】【31】【32】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333、360、362—363、384—385、386页。
【33】【34】【35】【36】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434、489、493—495页。
【37】【38】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3—626、627页。
【39】 徐爱国、李桂林、郭义贵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40】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阿宾顿出版社1974年版,第25页。
【41】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林立伟译:《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载于香港《二十一世纪评论》,1999年4月第52号(总)。另,该访谈录在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亦被收录。
【42】 〔美〕威廉·巴赛特著,阮齐林译:《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探究》,《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4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