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开放与创新——江明教授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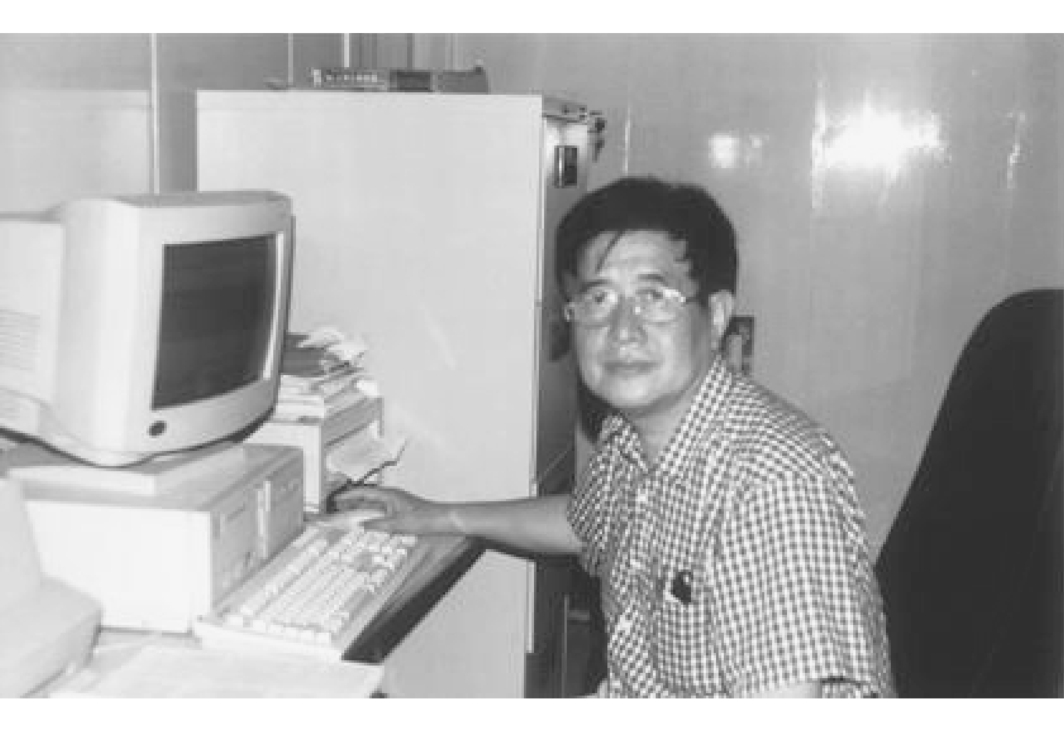
本人照片
江明,男,193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此后历任化学系助教、讲师,材料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高分子科学系教授,1979~1981年英国Liverpool大学访问学者。
现任复旦大学教育部聚合物分子工程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委员会副主任,还担任Polymer Journal和Macromolecular Research的顾问编委,《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高分子学报》、《功能高分子学报》、《应用化学》编委。
今年正好是我来到复旦的第五十个年头,半个世纪过去了,第一天走进复旦校园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起便决定了我此后一生的道路。
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比现在容易。我是从扬州中学毕业的,那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考上了大学,无非就是学校好些、差些的区别。我一直喜欢理科,读理科的话,从华东地区来讲,复旦是很好的选择。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学生有很多交流机会,我从出生一直到考大学,都没离开过家乡。我想找个机会到外面去,所以上海对我很有吸引力。还有,当时我的升学志愿完全是自己决定的,现在的孩子很奇怪,升学的志愿常常自己没有主意,家长倒为此操心得不得了,我真的不太理解这种变化。
我如愿以偿地进了复旦化学系,当时复旦的学习环境相当好,当然有些物质条件和现在没法比,但是学风确实不错。进校以后,大家的目标很单纯,就是读好书。当时都提些很理想化的口号:“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建设祖国。”但同学们的心里也确实是这么想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大家非常抓紧,不用功的学生很少见。那时图书馆的阅览室就在现在的校医院旁,是一排简陋的“草棚”,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不过那时玩的地方少也是一个客观原因,外面的诱惑很少。每星期在相辉堂(当时叫登辉堂)放一次电影,我们常去看;学校一些社团活动比较活跃,有特长的同学会参加。主要时间还是花在学习上。那时星期六也上课,星期天上午大都到教室去自习,下午就洗洗衣服啊、逛逛五角场,多数同学都是这样过的。
当时复旦刚经过院系调整,会集了很多其他学校的精英力量。我进大学第一年,学无机化学,实验指导老师是杨艳先生。开学两周第一次小测验,题目是“概述波尔原子理论”。过了两天,杨先生跟我讲:“江明,你这个题目答得非常好,条理性、逻辑性非常好。我把你的答题给吴(征铠)先生(当时的系主任,结构化学专家,杨先生的爱人)看了,他也很欣赏。”还拍拍我肩膀说:“你要好好学习啊!”一位大教授对于一个进大学才两个星期的一年级学生的答卷就这样重视和欣赏!吴先生和杨先生可能早就忘了这件小事,可对我来说,这种激励却受益终生。这件小事也可算是复旦精神的一个体现吧。
当时国家普遍提倡的是:建设需要人才,更需要科技人才。我也偏好理性思维,对于理科有兴趣,所以选择了化学专业,但不等于我对文科不感兴趣,中学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文学、历史。当时复旦的阅览室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杂志、期刊,有关于社会的、人文的,一般隔一两个星期我会去呆个半天。通过这些我了解了很多,知道复旦的中文、哲学、历史系也有很多名家,对他们我都很敬佩,虽然学科不同,但他们治学的精神也一样激励着我。
因为国家事业发展得很快,人才缺乏,原来的教师不够用了,就想办法在学生中选一些。为此,我得以提前毕业留在复旦搞研究,那时叫做“边干边学”。但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搞得一团糟。
“文革”中大约有3年,我完全无法学习,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前途非常渺茫,所企求的只不过是能够做个“人”,不要再整天被批啊、斗啊,谈不上学习或理想。后来虽然被“解放”了,但“文革”还没结束,教学也没恢复。有了空余时间,我就读一点英语,看一点专业知识。这些东西将来能否派上用场我完全不知道,只坚信那种“革命”是黑暗、是倒退,完全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总会过去的。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我讲不出;我还能不能看到这一天,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即使这样,人在世界上总要学点东西,而且对于当时的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在认真学英语、学物理、学化学的时候,我会暂时忘掉痛苦和烦恼,搞懂了难题,也会感到一些愉悦。
虽然那个年代“左”的路线干扰很严重,但复旦的学术精神是扼制不了的。复旦的老师,不论大学者、名教授,还是青年教师,大家都渴望着正常的学习研究,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中,仍希望把知识学好,把学术事业发展起来。许多党政领导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校刊上前几次发文纪念的陈传纲书记就是这样的代表。依照复旦的传统精神,如果没遇上搞历次运动,而是按照大家的愿望发展,本来是完全可以把学术搞得更好。
大约在1963年,学校里还组织过一个关于复旦学风的大讨论,讨论会在大礼堂举行,全校教师都参加了。那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宏论已经统治了政治思想文化界,但在复旦的校园里竟然还有关于学风的讨论,而且是大规模的。那个会由陈望道校长亲自主持,苏步青先生发表了长篇讲话。生物系遗传学的盛祖嘉教授,他讲理科的老师、同学应该怎样以实验室为“家”,鼓励大家树立学习上的奋斗精神。还有外文系一个叫葛传槼的老师,他是非常知名的英文专家,编过一本很知名的《英语惯用法字典》,这本字典我用了几十年。在复旦他是很特殊的教授,正式学历是初中,没念过大学,居然把英文学得那么好,成为名家,他讲的主题是:“中国人的英文能学得比英国人好!”主旨也是宣传扎实的学风以及非凡的努力。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喧闹中,我们还可以听到这些声音,还可以感受到师长们的言传身教,现在回忆起这件事我还是十分感动。复旦的精神,求真、开放、学术创新的精神都是有历史渊源,有根有底的,20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学风讨论就极具代表性。那个时候,学校的领导、校长、书记,还想着要抓学风问题,很不容易。
后来迎来了改革开放。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旦机会来了,复旦的学术精神很快就又复兴了。记得1986年,我到德国访问之前,谢(希德)校长给了我一份材料,是有关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China Program”,它专门提供经费,支持中国比较好的研究工作,最高可以提供10万马克。谢校长找到我,关照我好好去争取一下这个基金。后来我在德国找到一位很知名的教授合作,通过他的支持申请到了这个项目。我想这也是复旦才有的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校长就有这样的一种眼光,敢于放手让像我这样的年轻老师去做。如果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学校,情况会大有不同,即使拿到了这个项目,党委还要审查,还要报上级部门去批,时间花了不少,还不一定有人敢出来讲“OK”。所以,复旦的开放精神是领先的。
在此之前,我还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这对我来说真是来之不易,过去错过了太多,需要补回来。我在英国的学习中也确实收获颇多,两年后回到了国内。我对于人生没什么太高的奢望,只想有一个“正常”些的环境。像我在大学里书还是读得比较好的,很喜欢研究,能有机会考硕士、读博士、作研究,一步步发展下去,这就是我心目中“正常”的环境。但在“文革”的时代,这些都不可能。后来改革开放了,学校派我去留学,国家在变化,看到这些好的趋势,我觉得我的期望有可能实现了,所以我就决定回来。虽然国家尚在发展中,条件总不如外国优越,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去改变。20多年过去了,我见证了国内翻天覆地的变化,觉得自己无怨无悔,非常值。不少同事早年出国,在国外工作至今,我也并不觉得我的价值比他们小。
我在英国留学时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国外的一些专业课程,讲课的老师一般都在这个领域里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点在现在的复旦可能比较常见了,但几十年前我当大学生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复旦有好老师,但就理科来讲,在“文革”以前,极少有老师在基础研究工作中做出过很好成绩的,作为老师的角色,他可以把书教得很不错,把教材理解得很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很透彻,但并没有自己的科研成就作为依托。这两种情形存在很大的区别,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时我到英国去,听了高分子的课,从内容上讲我还是知道的,并不太高深。但那讲课的老师,如Bamford教授,讲高分子的聚合反应,他自己就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权威,讲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成果。这样,我听着就对他有一种崇敬感、一种信服感。
目前在复旦,我们也能逐步做到这一点了。像我们系开高分子的课,无论是高分子物理还是高分子化学,任课老师都已经在科研上有一定的水准,有些可能还是很拔尖的。我做学生时,这样的老师真是求之不得、非常向往的。复旦文科领域有很多老师本身就是在国内做学问最出类拔萃的人;理科方面数学系比较突出,因为数学不需要太多的研究条件。说到化学、物理和生物,当然也有一些知名教授,他们在国外时研究做得很好,可回来以后很多人没条件继续做,荒废了多年。现在情况改变了,这也是学校水准提高的标志之一。
我读书那会儿,大学的教材上还没有高分子的概念,我没有在课本上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但在化学期刊上看到过。那时学生的外语水平比现在差很多,很少有同学能看懂外文期刊。我在《化学通报》上看到钱人元先生写的关于高分子分子量测定的一篇综述,这是我看到的有关高分子的第一篇专业文章,产生了一些兴趣。后来当学校要搞高分子的时候,我对此已有些朦胧的概念,所以很乐意地参与了进去。
现在的高分子系从组织上建立起来是在1993年,只有10来年历史,但实际上,复旦高分子的教育和研究从1958年就开始了。当时于同隐先生带领一些年轻的教师,包括我们提前毕业的一些学生,开始创办这个专业。首先就是把本科的一些课程建立起来,像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也做一些研究。当然研究的水准是谈不上的,因为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在“文革”以前的阶段,主要打了一些基础,通过先建立的课程培养了一批人,每一届大概招30个同学。一直到1965年毕业了五六届的同学,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骨干。“文革”期间还招了几届工农兵学员。70年代后期一切重新恢复,建立了硕士点、博士点,我们专业的发展就这样渐渐走上正轨。1983年高分子专业并到了材料系,但发展受到了限制,于是在1993年分了出来,成立了高分子系。第二年又建立了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后来通过“211工程”、“985工程”,获得了比较大的资助。我们系虽然不算学校里接受投资最多的,但也得到了一些实惠,物质条件的改进明显加快了。现在复旦高分子是全国的重点学科,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在国内是比较受肯定的,有些还产生了国际影响。
(采访整理:朱玮、徐纯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