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康德与近代德国哲学之“转向美学”
在此,基于德国学界唯理念论美学问题史研究的一般结论,笔者要明确地将谢林的艺术哲学建树直接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论后继,纳入由康德肇始的近代哲学之“转向美学”的总体背景内。[17]由于在我们汉语世界的研究者和读者中,这一基础事实应该说尚未进入讨论的视野,这就首先要求纠正我们至今对谢林艺术哲学的那种不准确和不正确的美学史定位。汉语世界内的相关研究,由于最早的理论探讨主要由译介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工作所带动,在渊源阐发上,基本是接过黑格尔《美学讲演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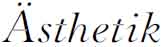 )中的一个现成观点,将谢林归为康德主义者席勒的思想后继者。尽管谢林如其他唯理念主义者一样,肯定受到了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精神的深刻影响,然而就此把他的哲学美学简单化地理解为席勒理论的直接后继,可以说这里已发生了由学派间观点商榷而造成的理解偏差。[18]尽管在此之间德语世界的唯理念论研究业已澄清,正是谢林必须被视为康德的“第三批判”最严格意义上的发展者,他的哲学美学动向正是直接衔接于康德的批判哲学[19];但广泛接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研究者和读者,尤其是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内的研究者和读者,一直很少了解也并未认真对待这个重要的事实辨析,如正统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奎(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的美学史表述,可说是这类误导的典型的例子之一。[20]为清除这种误解,我们必须回到对康德肇始的哲学之“转向美学”这个事实及其重大意义的辨析上来。
)中的一个现成观点,将谢林归为康德主义者席勒的思想后继者。尽管谢林如其他唯理念主义者一样,肯定受到了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精神的深刻影响,然而就此把他的哲学美学简单化地理解为席勒理论的直接后继,可以说这里已发生了由学派间观点商榷而造成的理解偏差。[18]尽管在此之间德语世界的唯理念论研究业已澄清,正是谢林必须被视为康德的“第三批判”最严格意义上的发展者,他的哲学美学动向正是直接衔接于康德的批判哲学[19];但广泛接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研究者和读者,尤其是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内的研究者和读者,一直很少了解也并未认真对待这个重要的事实辨析,如正统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奎(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的美学史表述,可说是这类误导的典型的例子之一。[20]为清除这种误解,我们必须回到对康德肇始的哲学之“转向美学”这个事实及其重大意义的辨析上来。
必须看到,尽管康德的批判哲学甚至没有以德国唯理念论本身的面目出现,尽管德国唯理念论已经远远地越出了康德,但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从1780年到1830年间这半个世纪内,唯理念主义的诸种精神运动包括其哲学美学之能够发生,只是以康德对人类理性本质的原则性思考为基础,只是以这一思考为导引。这一思考的奠基完成于1781年的KrV中,而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又在1788年的《实践理性的批判》[21](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中得到扩充,最后完成于1790年的《判断力的批判》(Kritk der Urteilskraft)。两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哲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批判和密集讨论,已对此基本达于共识:正是KdU标志着德国唯理念论哲学决定性地“转向美学”(Wende z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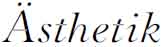 )。这指的是,KdU不仅与近代的一些先行者如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夏夫兹博里(The Earl of Shattesbury,1671—1713)、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l Baumgarten,1714—1762)的思想相呼应,强有力地推进了关于美、艺术家和艺术的学说之发展,毋宁说,当时是它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牢固地树立起一种确信:理性现在不再是在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神观照那里而是在艺术创造的“天才”那里去洞察人的本质。哲学现在既无法在科学理论和伦理学那里,也无法在作为历史理性的人那里寻找和发现人的本质,哲学只能审美地去洞察“人是什么”。美学因在普遍意义上处理美和艺术而能够提供一种彻底的“普遍观点”。正是康德思想的“转向美学”所造就并引进的这种确信,最终促成美学成为按其诉求看最具功能性的基础哲学,自18世纪末直至今天,由于哲学理性承认艺术的原理所具有的世界观意义,致使西方哲学的整个精神都被打上了深刻的概念印记。[22]
)。这指的是,KdU不仅与近代的一些先行者如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夏夫兹博里(The Earl of Shattesbury,1671—1713)、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l Baumgarten,1714—1762)的思想相呼应,强有力地推进了关于美、艺术家和艺术的学说之发展,毋宁说,当时是它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牢固地树立起一种确信:理性现在不再是在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神观照那里而是在艺术创造的“天才”那里去洞察人的本质。哲学现在既无法在科学理论和伦理学那里,也无法在作为历史理性的人那里寻找和发现人的本质,哲学只能审美地去洞察“人是什么”。美学因在普遍意义上处理美和艺术而能够提供一种彻底的“普遍观点”。正是康德思想的“转向美学”所造就并引进的这种确信,最终促成美学成为按其诉求看最具功能性的基础哲学,自18世纪末直至今天,由于哲学理性承认艺术的原理所具有的世界观意义,致使西方哲学的整个精神都被打上了深刻的概念印记。[22]
对本书的研究题目来说,强调这一点相当重要:要认清谢林哲学美学的建设性意义,首先要把握康德所肇启的近代德国哲学之“转向美学”在思想上的颠覆性,这也是我们的美学研究和讨论一直未能清楚认识也未曾思考的。如果说,严谨的新康德主义者如W.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在其1892年的哲学史回顾中毫无保留地将德国精神在这个时代所迸发的那种征服世界的伟大思想力量和成就根本上归因于“哲学与诗的一种光辉而幸运的结合”[23],从而始终仅把目光专注于哲学美学的全新的思想途径和领域;那么近一个世纪之后,德语世界的唯理念论研究者重新审查德国哲学的这一大事件时,却已在集中反思康德所肇启的这一“转向美学”的重大颠覆意义。[24]基森(Giessen)大学教授,著名的怀疑论者和唯理念论研究者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1928— )敏锐揭示出,哲学之“转向美学”不仅意味其在思想发展方向上发生某种特定变化,更不是仅指哲学于此时获得了新的对象领域,不如说,哲学“转向美学”这个现象根本上表明:此时哲学作为精神运动在其方向上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反转”,因为审美指向也好,“亲艺术”的立场也好,无不违反哲学自身的一贯传统。
我们对康德“转向美学”这一举措的研究必须把握住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和意义。而如果说此一“转向”的重大意义展示在一系列丰富的结果,尤其是在德国唯理念论的思想成果那里,研究可从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对其做出一系列问题史诠释,那么对本书的研究题目来说,努力去把握康德这个转向的意旨和康德本人的准确立场也至关重要,如果继续忽视它们,我们不但会继续低估和误解这个“转向”观念上的意义,也将无法在德国唯理念论美学的语境中对谢林的哲学美学贡献作出公正的判断。
如前所说,我们的回顾也必须首先集中到对这个事实的反思上来:“转向美学”的这个举措根本背离哲学的传统。与汉语世界的研究甚少质疑西方经典美学的习惯相反,德语世界的学术研究早已批判地解读了康德肇启的这个“转向”的完全背离哲学自身传统的那种精神实质:哲学这种反思精神,自其与宗教及艺术从它们的共同来源中分流出来,一贯努力与诗及艺术划清界限。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哲学史事实。我们的研究对此一直完全视而不见,应说是缺少问题意识所致。那么,站在近代启蒙主义立场上的哲学理性居然为艺术加冕并推崇诗的尊严,努力澄清后者所谓的“非理性因素”并将其与传统的联系阐述为与理性的联系,这种情况当然不是自然而然,而是前所未有。也就是说,近代德语世界的哲学开始致力于美学和艺术问题,完全不能仅以哲学当时获得了新的对象领域并扩展了自己的研究兴趣这类经验性的理由去解释。因为哲学的这一举措首先发生于一种称得上是巨大“反转”的态度和立场改变之上:哲学理性一反自“哲学之王”柏拉图以来对艺术的那种不信任传统,公开向自己的对手寻求帮助并与之联盟;而按照传统的观点,艺术不但具有与哲学竞争的资质和潜能,甚至能对哲学反思构成明显的威胁。我们还记得柏拉图《国家篇》(Politeia)中苏格拉底拒绝接纳“诗艺”进入他理想中“净化的”城邦时那种焦虑态度和激烈的观点:诗人及其摹仿性创造“诗的艺术”培育的是灵魂的低劣即非理性的部分,艺术让情感完全驾驭我们,致使灵魂中高贵即理性的部分走向毁灭;而诗艺的强大魅力足以使人们对正义及一切美德漠不关心。[25]而近代哲学史甚至整个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康德,却在严格的理性批判之后,驳回了以数学及精确科学手段运作的启蒙形而上学的科学整体性要求,在救援整体性的整个时代语境中决定性地“转向”艺术及美学。而把艺术这种对象以及“审美地规定的事物”这样的范畴引进到哲学之内,牵涉到哲学的内在本质,这意味着改变哲学的基本概念并修正哲学的自我理解。这是后果重大的改变,因为随着康德的这个举措开始了那种作为美学的近代哲学。
然而,我们在考察康德“转向美学”这个举措时必须对这个研究术语的表达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正确的把握:“转向”在此恰恰仅指“转向”。也就是说,康德在他这个影响深远的举措那里依然坚持着其理性批判工程的重要结论和划界。所以,我们决不能将康德哲学的“转向美学”误解为康德本人直接创立并建立了一种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美学;相反我们要再次强调,德国唯理念论研究所讨论的康德的“转向美学”,指的是KdU中的审美理性批判这个举措,这个批判的重要功绩是为时代精神牢固地树立起这样一种确信:理性是在艺术创造的“天才”那里寻找和发现人的本质,脱离宗教的哲学并不能依赖科学和伦理学,甚至不能依赖历史实践去洞察人的本质。因为依据康德的科学批判,科学理性的统治已根本上把世界关闭为一种“手段”的世界,而不将其看作“目的”的世界。康德的批判针对的正是这种减缩的理性所体现的那种危险的割裂思考方式,后者认为在精确科学之外不存在以理性去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抗议和批判这种割裂,他借助审美理性批判在KdU中建立的这种确信,标志着近代哲学脱离其传统宗教维系之后的一个重要突破,努力凭借审美理性去克服无整体的危险存在处境。由于审美理性继科学理性和历史理性之后被康德突出为最重要的救援形式,它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大幅度上升。康德已经把在其亲缘关系中的哲学与诗看作对实践的两种反思方式,认为二者虽有媒介上的区别,形态却是同一的。但他这个将哲学的和审美的反思方式扭结在一起的解决本身没有能成功,因为他无法从其美学的现象学基础出发去证明那种和谐统一的原理。
因此从德国唯理念主义运动内部来看,在扭转近代哲学,使之“转向美学”的康德那里,美学这门学科甚至连外部形态都未曾清晰。康德对人类的审美理性作出了严格的批判,之后他却认定:在美学这里不可能有学说存在,只可能有批判存在。在哲学体系这里,他甚至不允许有鲍姆嘉通那样的直接的感性认识扩展。所以他本人也只是为哲学美学贡献了一种判断力批判以及植入在这一批判关联中的鉴赏理论。
对同样是经典先验哲学家的费希特——其已将思辨推进到作为有限理性之原理的“绝对自我”——那里,我们能够有把握地确认,他对哲学美学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美学专著和直接的美学陈述,而是通过其基本哲学形式。这方面他最典型的贡献应该是他的“绝对自我”对天才思想的“先验哲学普遍化”,也就是费希特把天才的立场和天才的创造活动提高为一种普遍的先验立场。他认为从康德在“先验统觉”亦即“我思”那里的切入,已能导出把自我提高为论证一切的原理的可能性。历史地看来,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前,费希特的这种相应于先验的切入,独立于经验自我的“纯粹自我”,已经是近代哲学随笛卡尔开始的那种主体化和内在化的高潮点。至于此过程随着天才的意识形态同时开始,这也决非偶然。
在谢林先前的理论盟友和后来的理论敌手黑格尔的思想系统和哲学建构那里,笔者要提请读者注意:美学事实上被置于其理论建设的边缘地带。[26]这个情况也决非偶然,不如说,其与黑格尔在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实际上作为“先验唯理念论”批判者的独特身份有着微妙且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尽管黑格尔以其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学说——在其绝对性中的“精神”的一种生存形式的学说——在自己宏大而复杂的唯理念论体系中亦赋予艺术一个确定的形而上学地位,他那种系于柏拉图的艺术怀疑基本立场的严峻美学反思最终结出的一项能够直接切入到我们现代生活处境中的思想成果,乃是对“艺术的过去性”之深刻洞察。[27]
正是德国唯理念主义这个丰富的精神运动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去重视谢林艺术哲学中的那些要素,它们从内容上即决定了谢林艺术哲学在全部唯理念论美学思想内独有的重要地位。正如德语世界的专业研究者们对此的肯定性确认,正如研究事实早已为我们打破德国唯理念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某种“统一的哲学”之表象,作为哲学美学的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也不能理解为均质单一的哲学运动或思想学派,不能仅限于唯理念论学派的研究立场去研究处理;相反,这同一个事实显示,谢林的哲学美学工作与康德肇启的这个转向多重地衔接在一起,并且在他这里,美感的或艺术的反省形式与哲学反思形式的关系得到了另样的理解和阐发,其不同于康德所做:处于积极的互补关系中的哲学与艺术已达成为理论同盟,它们古老的争执则转化为哲学美学的知识形式中的一种与哲学的固有本性相矛盾的情况。就哲学美学本身指向艺术直观而言,它在反思着对实践的一种反思方式,其与它自己的反思方式对立。于是随着这种在自身内整合了哲学思考的反思和艺术直观的反省的艺术哲学,哲学在自身内设定了新的张力,尤其在哲学的思考不得不涉及审美经验和艺术直观的情况下。然而正是谢林的包含有内部张力的哲学美学规划构成为德国唯理念论美学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并且超出学派意义,体现为近代整体论追求的重要代表之一。本书将通过批判地审查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建树,也即他的System提出的艺术工具命题和他的PdK中的存在论神话学,对此提供事实方面的肯定性证据,展开谢林哲学美学思考的问题深度,以促进基础研究和讨论。
【注释】
[1]以下缩略语System;本书的讨论和行文采取德国学界通行的缩略语以指称相关的谢林原著,缩略语对应的原著全名,请参看本书附录中“缩略语及引用说明”。本书讨论中所援引的德文原著的汉译均由作者个人提供;能力所限,错讹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2]依德语世界谢林研究和谢林诠释的讨论习惯,本书以专业术语“艺术—哲学”(Kunst‐Philosophie)指称谢林在其System中的哲学美学纲要,其文本涵盖System的第六章;而以“艺术哲学”指称谢林同一性哲学体系中的哲学美学,其文本为谢林1802—1805年的耶拿维尔茨堡艺术哲学系列讲座手稿Philosphie der Kunst(生前部分出版)。
[3]以下缩略语PdK。
[4]这部分课题涉及大量的谢林手稿翻译和释义研究工作,作者的解读受益于德国学界多位唯理念论研究专家。
[5]P.松迪(P.Szondi)对此问题有专题研究,见该作者:Poe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Bd.II,Von der normativen zur spekulativen Gattungspoetik.Schellings Gattungspoetik,1974。
[6]国内学界对“Deutscher Idealimus”的通行译名是“德国唯心论”或“德国唯心主义”。
[7]Cf.Joachim Ritter(hg.),Historis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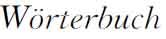 der Philosophie,Basel 1971—2007,Bd.4,S.30—33;R.Kroner,Von Kant bis Hege l,Bd.I:Von der Vernunftkirtik zur Naturphilosophie,Tbingen 1921,S.12.
der Philosophie,Basel 1971—2007,Bd.4,S.30—33;R.Kroner,Von Kant bis Hege l,Bd.I:Von der Vernunftkirtik zur Naturphilosophie,Tbingen 1921,S.12.
[8]Cf.R.Kroner,Von Kant bis Hege l,Bd.I:Von der Vernunftkirtik zur Naturphilosoph‐ie,T bingen 1921,S.12.
[9]Cf.N.Hartmann,Die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Berlin 1960,前言。
[10]“德国唯理念论/主义”还经常在广义上用于标识与德国古典同时并与之有精神联系的那些哲学精神,标志诗与哲学中的那个时代:在这个历史语境中不仅大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l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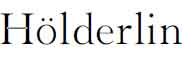 ,1770—1843)同被认为是古典主义和唯理念主义的代表,代表者还进一步包括浪漫派的施莱格尔兄弟(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等人,甚至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耶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也都属于这个面对启蒙时代的新纪元,他们都以生命的上升、生命内容和一种新的创造性为指向,在一个经受怀疑主义折磨的时代里致力于新世界和新理想的创造。以此,广义的唯理念主义首先是在德语世界中成为一种实践—道德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标志。
,1770—1843)同被认为是古典主义和唯理念主义的代表,代表者还进一步包括浪漫派的施莱格尔兄弟(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等人,甚至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耶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也都属于这个面对启蒙时代的新纪元,他们都以生命的上升、生命内容和一种新的创造性为指向,在一个经受怀疑主义折磨的时代里致力于新世界和新理想的创造。以此,广义的唯理念主义首先是在德语世界中成为一种实践—道德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标志。
[11]Cf.W.Schulz,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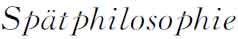 Schell‐ings第6页以下的阐述;有关这一术语的问题史讨论,还可参看H.J.Sandkühler(hg.):Handbuch Deutscher Idealismus,导论部分第1—23页。
Schell‐ings第6页以下的阐述;有关这一术语的问题史讨论,还可参看H.J.Sandkühler(hg.):Handbuch Deutscher Idealismus,导论部分第1—23页。
[12]以下缩略语KrV。
[13]以下缩略语Prolegomena。
[14]Cf.Historis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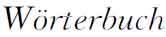 der Philosophie,Basel,1971—2007,Bd.4,S.38—40.
der Philosophie,Basel,1971—2007,Bd.4,S.38—40.
[15]以下缩略语Wissenschaftslehre。
[16]以下缩略语Vom Ich。
[17]早年深受J.里特(Joachim Ritter)影响的O.马夸德(Odo Marquard,1928— )在其专著Aesthtica und Anaesthetica.Philosophische legungen中对此问题集合做了探讨。
legungen中对此问题集合做了探讨。
[18]笔者认为,指谢林为“席勒派”理论后继的笼统观点,除了忽视谢林哲学美学的直接康德来源之外,还在另一个基本事实那里发生了判断错误。这就是不了解谢林哲学美学本质上的“非历史—非实践”的特点;而席勒美学众所周知,以对艺术乃至美育的历史功能的强调著称,后者对黑格尔影响甚大。就理论的切入点和展开方向说,席勒的古典美学的历史哲学指向,可说与浪漫派的审美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十分合拍。
[19]参见P.海因特(P.Heinter)在Die Bedeutung der  Urteilskraft für die Transzendentale Systematik当中的表述,第170页以下。
Urteilskraft für die Transzendentale Systematik当中的表述,第170页以下。
[20]参看汉译本〔英〕鲍桑奎:《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09页,此书观点为国内美学研究者引用甚多,但大多是作为一种定论使用,缺少理论辨析和论证探讨;另可比较黑格尔文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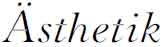 ,HW Bd.13,S.91,汉译本参看朱光潜译〔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页。
,HW Bd.13,S.91,汉译本参看朱光潜译〔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页。
[21]以下缩略语KpV。
[22]美学不仅在从古典主义到浪漫派的大思想家如席勒、叔本华、早期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乃至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那里被理解为基础哲学,即使在如黑格尔、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晚期尼采这些对浪漫派及美学的伟大批判者那里,也是他们要在形而上基础上与之抗争不已的哲学精神。
[23]Cf.W.Windelband,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Tübingen 1935,S.444—446.
[24]德语“Wende”一词的基本义是“转折”或“折返点”。马夸德已正确地看到,“对哲学来说,转向美学至少意味着与其最强大的那些传统的中断”。Aesthticaund Anaesthetica,1989,S.22.
[25]Der Staat,Zehntes Buch,1,6;aus Platon  Dialoge,Bd.V,S.388,404.
Dialoge,Bd.V,S.388,404.
[26]流传的史料证明,尽管黑格尔生前至少先后四次举办过美学—艺术哲学讲座,却仅仅留下一些篇幅不大的讲义提纲和简短的手记,他生前一直没有将演讲提纲成稿的打算。
[27]Cf.Hans‐Gerog Gadamer(1900—2002),”Ende der Kunst?Von Hegels Lehre vom Ver‐gangenheitscharakter der Kunst bis zur Anti‐Kunst von heute“及”Die Stellung der Poesie im System der Hegelsche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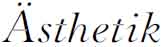 und die Frage des Vergangenheitscharaker der Kunst“,in H.‐G.Gadamer,Gesammelte Werke 8,
und die Frage des Vergangenheitscharaker der Kunst“,in H.‐G.Gadamer,Gesammelte Werke 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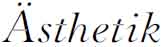 und Poetik I S.206—220,221—231;国内学者对黑格尔美学这一问题集合及其影响史的专题研究,有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薛华教授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可参看其中《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论点》一文,同书第1—49页。
und Poetik I S.206—220,221—231;国内学者对黑格尔美学这一问题集合及其影响史的专题研究,有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薛华教授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可参看其中《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论点》一文,同书第1—4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