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语言学者统计,全世界讲粤语的人约有7000多万。任何方言都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外壳和内核。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最流行的粤语语汇都是“打的”、“点心”、“埋单”,这是否就是粤文化最通俗的表征?
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到郑州讲课,一天,在友谊宾馆的餐厅里吃完饭,我请服务员“结账”,没想到她竟然反问道:“埋单是吗?”真令我这个老广有点吃惊。以前北方人到了广州,语言不通,诸多不便。而粤人说普通话又多是“狗养!狗养!”(久仰,久仰!粤语狗、久读音相同)的水平,人们谓之“鸡同鸭讲”。如今却有一位郑州姑娘以“埋单”纠正我的“结账”,看来鸡语与鸭语也是可以互相渗透的。

广州人和外国人(约1870年的广州街景)
前任广州市长黎子流可能是一位最勇敢的鸡说鸭语的公仆。前些年社会上流传着很多黎子流讲普通话的笑话,比如有这么一则:他到某海军基地慰问视察,在致词中有这样一句话:“看了你们的烂艇烂炮(舰艇舰炮),很令我开心。”(粤语的烂、舰读音相近)闻者大笑。他被评为广州市推广普通话的优秀分子,亦是当之无愧。他明知讲得不好、惹人笑话,却是若无其事,坚持到处讲普通话,这不正是最理想的推广员么?
其实,从历史上看,粤方言的形成曾大量受到楚方言和中原汉语的影响,鸡语鸭语之间往往有“本是同根生”的血脉相连。但今日的楚人只有在粤人的嘴里才能听到自己的古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今日已惘然。
除了古楚语,粤方言还与古代广东、广西等地使用的壮语、侗语、傣语——属壮侗语族,又称为古台语——有密切关系。比如大家都知道粤人喜在人称前加一“阿”字,如“阿明”、“阿强”等,此一“阿”字词头便是各种古台语共有的用法,先是被粤方言吸收,至魏晋时才传入北方话系统。
秦汉时期大批中原汉人(当时的南下大军、南下干部以及流放的犯人)进入广东,由“言语各异,重译乃通”至“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均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正是粤方言接受中原汉语影响的过程。唐代的粤方言在接受中原汉语语音和书面语方面更为广泛和成熟,是同化期的高潮。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自宋代则开始了另一个方向的进程。当时的北方宋人已感到粤方言的难懂,而至明代的粤方言,已经与现代粤方言大体相同了。
然而,今日粤语中又有另一股时髦的潮流使粤人之间也产生另一种鸡同鸭讲的障碍。这就是受香港口语的影响,在口语中夹杂大量的英文单词。而且增生速度很快,一两年间便有落伍的危险。会讲“冧把”(号码,英文number的音译)、“士多”(小商店,英文store的音译)等等只是昔日的语汇,今日讲的是“烟栽”(欣赏,英文enjoy的音译)、“枯”(冷酷,英文cool的音译)等等。一位在广州环市中路(有香港中环之喻)的高层写字楼任职的白领很可能在一分钟的言说中夹杂进20个英文单词,而其字音则都是已经粤语化的,颇有点“拿来主义”的气魄。然而如果听者不是同类中人,则很可能也是鸡同鸭讲。在这方面,广东的传媒还算控制挺严的,据说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做节目时不得夹杂英文字音,即使普遍如“拜拜”二字。
不少北方人以为粤方言只是难听懂,书面文字则不会看不懂。实际上,粤方言在书面上也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写法,香港很多报刊都充斥着大量的这种书面语,只是内地对之控制甚严而难以泛滥而已。请看下面几句话:
“我都 饮番杯先。”
饮番杯先。”
“重话我有用添,究竟边个缩沙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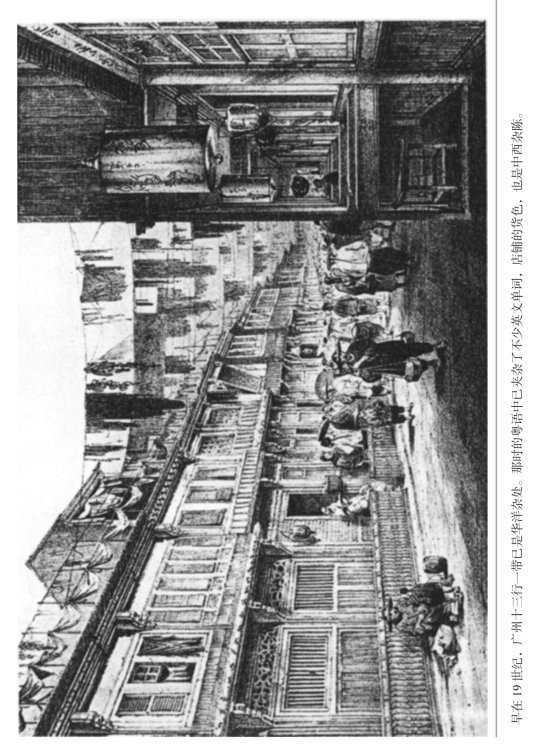

清末广州帮办洋务的翻译
“你伊只鬼古我地听过晒喇。”
“佢而家多数唔响屋企,你直程去厂 拒系啦。”
拒系啦。”
——什么意思?北方人准会看得一愣一愣的。译为普通话的书面语则是:
“我也来喝上一杯再说。”
“还说我没用呢,究竟是谁先退缩了?”
“你那个关于鬼的故事我们全都听过了。”
“他现在多半不在家,你直接到厂里找他就是了。”
这不是鸡写给鸭子看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