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坐火车去伊尔库茨克。因为火车站就在酒店对面,所以我直到开车前半个小时才拉着箱子慢吞吞地进站。火车站里人很少,安检也很宽松,与印象中向来人山人海的火车站很不一样。我几乎是凭着一种直觉进站,走下楼梯,到达站台,黑咕咚咚的站台已经有几个人在排队了,列车员把大家的证件和票凑近眼睛核对,我是最后一个,他帮我把箱子拎上车,带我到铺位,给我一套床单。然后用很不清晰的英语告诉我:他们说你想睡觉,这里可以睡觉。一边用手比出睡觉的动作。与列车平行的下铺中间一块是掀起来的,当做一张小桌子,设计得很巧妙,但我却不知道怎么把它放下去,隔壁的人见我在那里抓瞎,便过来帮我放了下去,又到车厢头给我拿来一个枕头和一个垫子。我扯开床单,仔仔细细的铺好,脱掉靴子,爬了上去。
夜已经深了,车厢里面没有灯光,但与列车并行的,却有一轮大大明月,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月亮,感觉距它如此近。皎洁的月光照进车窗,我睡不着,坐起来,抱着膝盖,看着远处那些不断向后隐去的森林,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梦的世界。列车似乎拐了个弯,月亮不见了,我躺了下去,被车厢内此起彼伏的鼾声拉回了现实。失眠了,很晚才睡着。
中途停靠站拍的火车的样子。

似乎没睡多久,便被人们洗漱和吃早餐的声音吵醒了,我迷迷糊糊地撑起来,列车恰好在经过一座大桥,天已经大亮了,太阳从斜后方射进来。灌了半瓶水,清醒了些,便坐起来,一边啃饼干,一边打量着车厢里面的人。成年人大都很胖,他们穿着睡衣或者宽松T恤,几乎每个人都带了拖鞋和毛巾。他们洗漱完毕便坐下来开始吃早餐,用自带的刀切面包和火腿,用自带的茶壶泡茶,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的铺位与列车平行,整面靠窗。

列车驰过森林、原野、河流,村庄很少,偶尔在蓝天下出现几个彩色的小木屋,若非褪了色,真感觉像童话里一样。这段视频拍的并不是最美的,而且车窗还反光。天亮没多久这个手机就没电了,只拍到短短两段很平常的。
列车员火红色的头发是真的,制服很漂亮吧?中途停靠站乘客可以下车自由活动,我每每下去出气,因为视觉上的盛宴也让嗅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想象一下满车厢巨大的俄式大脚丫。还有很多人吃一种小方盒的泡面,我很想尝尝的,但是没有列车员推着卖。

下午我都在睡觉,实在是太困了。中途醒来,发现不知谁把遮光的窗帘给我拉上了,翻个身又继续睡。晚上便发生了一件奇遇。我正在记事本上画画,一个人突然坐过来开始对我说话。这个人我是认识的,就在我前面垂直铺位的上铺,头天晚上我躺着失眠的时候他的脚从铺位悬出来,我从未见过那样长的脚,简直触目惊心,当时还想这样的脚在中国肯定买不到鞋。第二天早上,这双巨脚的主人——一个红脸膛的西伯利亚汉子从上铺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他简直有两米高,好在他不胖。现在,这个巨人坐在我旁边,但我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打开手机的谷歌翻译,一句一句地猜:
“你叫什么名字?”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伊戈”,他用大拇指指着自己说。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伊戈尔远征记》。
“你想对我说什么?我听不懂俄国话,我是外国人。”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一部老式的诺基亚,开始给我看照片。
“这是你的卡车?”他点点头。这种巨大的黄色卡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是一个卡车司机?”他点点头。
“这是你的女儿?”他点点头,照片上是一个10岁左右的大眼睛小姑娘,长长的黑发。
“这是你的马?”照片上是一只棕色的马。他点点头,又指着我,比出骑马的动作。
“你说我可以骑它?”他点点头。
“不行啊,我得去贝加尔湖。”听到这个名字他打着手势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
“你说你住在贝加尔湖旁边?”他点点头。
“住在森林里?”他点点头。
往后翻是几张他很傻的自拍照,最后是一张我趴着呼呼大睡的照片。
“你为什么要拍我的照片?”他很羞涩地笑了,然后拿过我的笔,在笔记本上画了一颗心。
“你说你喜欢我?”他点点头。
“你多少岁了?”他伸出两只手,一只比成四,另一只比成OK。
“43?”他摇摇头,又扬了扬手。
“40?”这次我才对了。
“可是我要回家,我住在中国。”恰好这时候手机没有了信号,他接下来说些什么我就猜不着了,我告诉他我要休息了。他凑过脸颊恳求我亲他一下,我亲了一下,他又把脸转到右边,我又亲了一下,他又转到左边,我以为他没个完,便不干了。后来看《西伯利亚理发师》才想起俄罗斯告别礼,亲三下是再见,而亲两下,则是不再相见。
列车员熄了灯,德米特里在车厢里晃了几圈,又在我对面坐下,我只是埋着头装睡。夜渐渐深了,他还坐在那里,空气渐渐的变得很冷很冷。突然,他开始打起喷嚏来,巨大的喷嚏一个接一个,引得周围的人开始辗转反侧,抱怨起来,他终于爬上自己的铺位睡觉去了,我差点忍不住爆笑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便下了车,德米特里还在睡觉。一个新上车的人帮我把箱子拎了下去,交给出租车司机,自己再回到车上。整个火车之旅我几乎没自己拎过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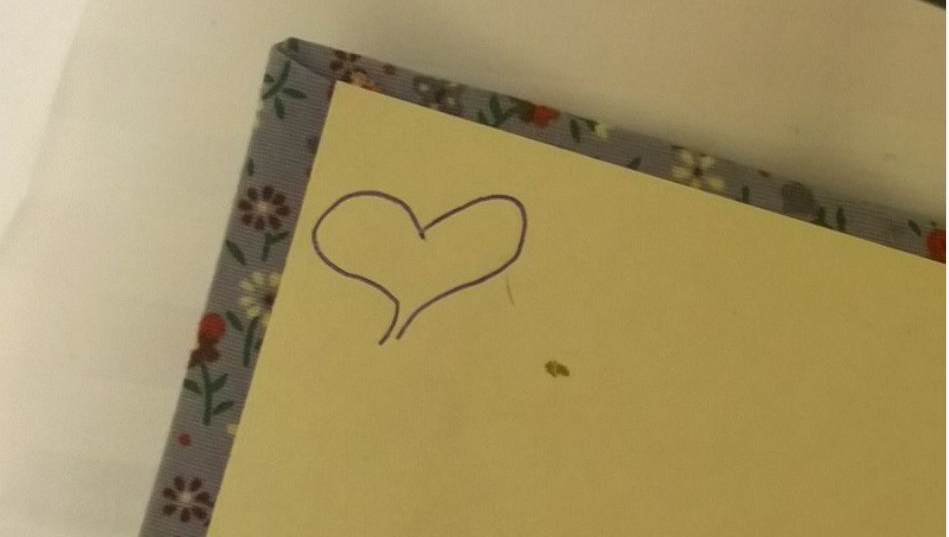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