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阿廖沙渐渐跟染坊工人小茨冈熟络起来,这个人很健硕,也很健谈,外公很器重他,两个舅舅只敢偷偷说他坏话。听外婆说,小茨冈的本名叫伊凡,因为是茨冈族人,所以大家都叫他“小茨冈”。虽然是个捡来的孩子,但他却比外婆亲生的那两个好多了。他纯朴、勤快,玩儿起来像孩子一样执拗,还会玩儿许多花样,真是有趣极了。不仅如此,每逢节日,小茨冈就会伴着雅科夫的琴声跳起舞来,他的舞蹈还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渐渐地,我的身体好了起来,也意识到小茨冈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外公骂他不如骂那两个舅舅多,而且还常常私下夸奖他:“小伊凡是个好手,这小子会有出息!”
两个舅舅对他算是和善,从来不像对格里戈里那样搞什么恶作剧。这帮人用各种花招折腾那个半盲的老师傅,都没有重样的。不过,格里戈里似乎一点儿也不当回事,无论是凳子上放钉子还是弄乱布的颜色,每次他都保持沉默。但是外婆每次都会挥起拳头骂他们:“不要脸的魔鬼们!”
然而,舅舅们常常偷偷咒骂小茨冈,说他是个小偷,是个懒汉。我不懂,就去问外婆。她耐心地向我解释:“他们将来是得分家自己开染坊的,都想要凡纽什卡到自己的店里帮忙,所以嘛,他们俩就都在对方面前辱骂他!他们怕他跟你外公一起开另一家染坊,他们就竞争不过老头子了。”说到这儿,外婆就轻声地笑起来了,“哼,他们那点儿小算盘早让你外公看穿了。他故意对他俩说:‘啊,我要给伊凡买一个免役证,我太需要他了,他可不能去当兵!’看把你舅舅们气的!”
现在,我像坐轮船来的时候那样同外婆坐在一起。每天临睡前,她都过来给我讲故事,都是她自己的故事,可是听着像童话一样神奇。提到分家之类的事情时,外婆完全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语气在评论,似乎这一切与她无关。

也是在这样的故事会里,我才听说小茨冈是被捡来的孩子。一个春天的夜里,阴雨连绵,人们在门口的长凳上看到了幼小的小茨冈。据说他被冻僵了,只有一块破围裙包着。
“是谁扔的?怎么会扔了他?”
“他妈妈没有奶水,养不活他,听说有一家刚生下的孩子夭折了,于是就把自己的孩子送来了。”一阵沉默,外婆叹气说,“唉,亲爱的阿廖沙,都是因为太穷哇!你外公想把凡纽什卡送到警察局去,我拦住了他,想自己养,这可是上帝的恩赐。我14岁结婚,15岁开始生孩子,生过18个,可是上帝偏偏看中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召唤到天上当天使去了!我又心疼又高兴!”
她低声笑着,眼中闪着泪光。她坐在床沿上,蓬松的黑发披在硕大的身板上,好像一只大熊。
“好孩子都叫上帝带走了,剩下的都是坏的!”外婆接着说,“伊凡就这样留下了,洗礼之后,他越长越水灵!刚开始,我叫他‘甲壳虫’,那和他满屋子爬的样子很像呢!他很纯朴,你可以放心地去爱他!”
伊凡不仅纯朴,还很有趣,他经常会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每到周六,外公收拾过本周内犯过错误的孩子后,就要去教堂做晚祷。这时候,我们就在厨房里称王称霸了。小茨冈会用纸做一架马车,再剪一个雪橇,然后赶来几只黑色的蟑螂。啊,真是太有趣了!四匹“黑马”拉着雪橇在黄色的桌子上驰骋起来,伊凡用一根小松枝赶着它们,大叫:“哈,赶着车接大主教去喽!”
他又剪了一片纸贴在另一只蟑螂身上,赶着它去追雪橇:“他们忘了带褡裢,这个修道士追上来了!”再用一根线捆住一只蟑螂的腿,这只蟑螂一边爬,一边不断地点头,伊凡大笑:“助祭从酒馆里出来,醉醺醺地要去做晚祷喽!”
他还将一只小老鼠藏在怀里,吻着它还喂它糖,他十分自信地说:“老鼠聪明着呢,家神特别喜欢它!谁养了小老鼠,家神爷爷就会保佑谁!”
伊凡还会用纸牌或者铜钱变戏法,玩儿的时候嚷得跟孩子一样大声;还有玩儿牌的时候,他如果输了,也会像孩子一样气鼓鼓的。
每到节日的夜晚,小茨冈更是活跃得起劲。通常情况下,这时外公和米哈伊尔舅舅都会出门去做客。雅科夫舅舅拿着六弦琴走进厨房,同时,外婆会摆好一桌子丰盛的饭菜和一瓶伏特加酒。小茨冈穿着节日的盛装帮着忙活;格里戈里轻轻地走进来,眼镜片泛着光;保姆叶夫根尼娅的麻子脸也更红了,她胖得像个缸,嗓音则像喇叭。有时候,乌斯平尼耶教堂的长发助祭,还有些贼眉鼠眼的人也会来。他们敞开肚皮大吃一通,还给孩子们发糖果和甜酒!接下来,畅快的狂欢节目就要登场了!
雅科夫舅舅小心地调好了他的六弦琴,照惯例先要问一句:“各位,怎么样,我就要开始了!”
然后,甩一下他的卷发,好像猫似的伸长脖子,眯起眼睛,流转着捉摸不定的眼神,轻轻地拨起琴弦来,一支极富感染力的曲子就这样倾泻而出。它像一条奔流的小河,从远方的高山破竹而下,渗过墙缝挤进来,冲击着在座的每个人,让人顿感忧伤然而又无比激越!对世界的悲悯、对自己的悔悟都随着旋律溢出躯壳,大人和孩子在灵魂上彼此转换着,每个人都端坐静思,凝滞的空气包围着一个个跳动的心。
米哈伊尔家的萨沙把身子探向他的叔叔,张着嘴巴、流着口水!他听得出了神,从椅子上滑到地板上,仅用不太听使唤的手撑着地,静静地倾听着,好像永远都不会再起来了。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茶炊偶然响起的低鸣,仿佛划破宁静后留下的伤口,使哀伤的情绪更加浓重了。那哀伤围拢着透着秋风中漆黑夜空的小窗户,摇曳的灯影里,是它们影影绰绰的眼神。
节奏越来越快了,雅科夫舅舅的两只手像机械一般弹动,手指如十只快乐的小鸟在飞速地抖动翅膀,快得让人难以置信。
喝过几杯酒,他就边弹边唱起来,那声音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雅科夫假如是条狗,
就从早到晚叫不休。
哎哟哟,我孤苦!
哎哟哟,我忧愁!
一个尼姑顺着大街走,
一只老鸦飞落在墙头。
哎哟哟,我孤苦!
蛐蛐钻墙缝叫破喉,
蟑螂嫌它闹腾没够。
哎哟哟,我孤苦!
一个乞丐晒裹脚布,
另一个乞丐跑来偷!
嗷嗷,我孤苦!
嗷嗷,我忧愁!
听这支歌我从来没听完过,因为一听他唱到“乞丐”,一种莫名的悲痛就会让我失声大哭。
小茨冈听歌的时候会将手插进黑色的头发里,低着头喘粗气。忽然,他叹息道:“唉,我要能有副好嗓子就好了,我一定会唱个痛快!”
外婆说道:“好啦,雅沙,别再折磨人了!来吧,叫凡纽什卡给我们跳个舞吧!”
大家并不是每次都立即同意,不过雅科夫舅舅常常用手按着琴,攥紧拳头一挥手,好像从身上甩掉了什么一样猛喊一声:“好,让忧愁烦恼都走吧!瓦尼加,该你上场了!”
小茨冈整理整理衣服和头发,恭敬地走到中间,红红的脸膛微微一笑:“要弹得快一点儿,雅科夫·瓦西里奇!”
就这样,暴风骤雨般的节奏疯狂响起,小茨冈的靴子跳着细碎的步子,整个厨房似乎被他火一样的舞蹈点亮了!他突然尖叫一声,仿佛一只金色的燕子在大雨来临之前盘旋,衬衫颤动着,好像在燃烧,闪动着灿烂的光芒。他放纵地跳哇跳哇,要是一开门,他准能跳出去跳遍全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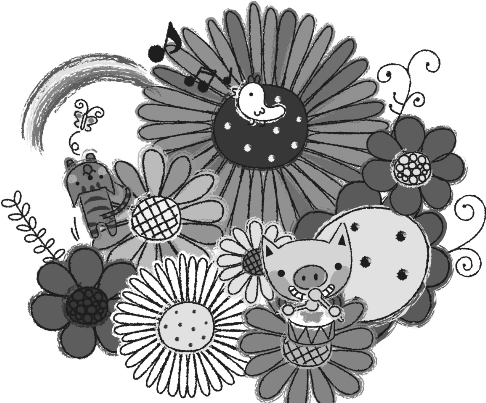
接着,小茨冈又来了一段俏皮的串场词,人们不由得也跟着他抖动,脚下似乎有团火,不时地还跟着他吼上几声。格里戈里拍着自己的光头,一边高兴地念叨着什么,一边弯下腰来,那柔软的大胡子盖住了我的肩头:“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假如你父亲还活着,他会跳得比火还热烈!他可是个快乐的人啊,很讨人喜欢呢!你还能记起他吗?”
“我不记得了。”
“噢,你不记得了!以前,他同你外婆跳起舞来……嘿,你等一下!”他说着站了起来,朝另一边的外婆一鞠躬说道:“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请赏个脸和我跳上一圈吧!就像以前和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怎么样?”
“让我跳舞,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外婆朝后退了一下。但是大家的盛情难却,于是,她顿了顿,整理一下衣裙,挺胸昂头地走到中间,兴高采烈地舞了起来,她叫着:“你们只管笑吧,尽情地笑吧!雅沙,换支曲子!”
一支舒缓的曲子响起,小茨冈又跑到外婆身前,围着她跳开了。外婆两手伸展,眉毛上挑,双目遥视,在地板上滑行的样子好像飘在空中一般。真有趣,我扑哧笑出了声,格里戈里伸出指头点了点我的额头,所有的人都责备地瞪了我一下。
格里戈里示意小茨冈停下,接着,保姆叶夫根尼娅提起了嗓音,唱道:
周一到周六,
姑娘忙着把花边绣。
累得筋疲力尽哟,
顾不上把气喘一口。
外婆根本不是在跳舞,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她若有所思,遥望着前方,巨大的身躯靠两只显得很小的脚撑着摸索前进。她忽然停止了脚步,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过立刻,她又容光焕发,露出慈祥的笑容。她闪向一边,低头指点,好像在给什么人指路。忽然,她转了起来,裙摆飞舞着使她变大了许多,力量和青春似乎一下子重新回到了她身上。每个人的目光都被吸住了,她奇迹般地展现出一种鲜花般的美丽。
保姆叶夫根尼娅又唱起来了:
周日的午祷结束,
夜半时分才停下舞步。
她走上回家的路,
叹息周一又要劳碌。
跳完了,大家使劲夸奖外婆,她整理着头发,说:“好啦!你们或许还没有见过真正的舞蹈吧。以前,我们巴拉罕纳[1]有个女孩,她叫什么来着……她的舞姿令我毕生难忘!那简直快活得让你想流泪,只要看一眼就能幸福得昏过去,我太羡慕她了!”
“歌手和舞蹈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叶夫根尼娅认真地说,她又唱起了大卫王[2]的歌。
雅科夫舅舅说小茨冈要是去酒馆跳舞,那里的人都会疯狂的,可是小茨冈还是执着地希望自己有副好嗓子。

说笑间,大家开始喝伏特加,互相敬酒。外婆看见格里戈里喝多了,就劝他不要喝瞎了眼睛,格里戈里却十分镇静地说:“瞎吧,要眼睛也没什么用,我啥都见过了!”他似乎还没醉,但话越说越多,见了我总要说起我的父亲:“他可有一颗伟大的仁慈的心哪,我的小老弟,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
“是啊,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外婆叹了一口气说。
我似乎是每场狂欢的旁观者,各式各样的信息填满我的耳朵,人们的每一句话、每个表情、每个动作都吸引着我,变成一种甜蜜的惆怅冲上心头。欢乐和忧愁就是这样相伴盘旋,它们纠缠着、融合着,变幻莫测。
有一次,雅科夫舅舅喝得微醉,他撕扯着上衣,胡乱揪着头发和胡须说:“这算哪门子生活,为啥要这样活呢?”他张牙舞爪地泪流满面,“我是流氓、浑蛋、白眼儿狼!”
格里戈里突然叫道:“非常正确,你就是!”
“得了,雅沙,上帝最清楚你是什么人!”外婆也喝醉了,她显得十分温润,一对含笑的黑眼睛向每个人撒播着温暖的爱意。她用头巾扇着红红的脸,如泣如诉地说:“主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么美好!真是太美好了!”这是她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
雅科夫舅舅一向无忧无虑,我对于他此刻的表现非常吃惊。我问外婆,他为什么要哭,还打自己骂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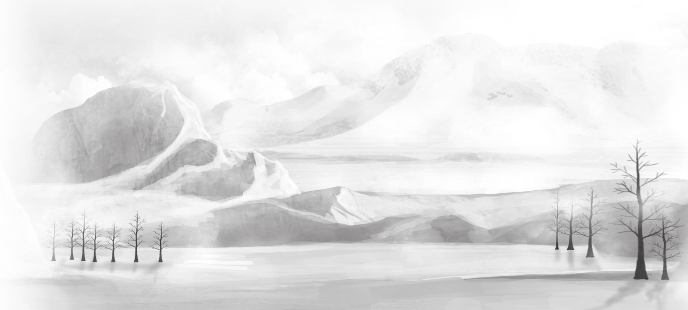
“你并不是立刻就要知道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迟早你会理解的。”以往,外婆都是直接向我解释问题的。这下可触动了我的好奇心,我跑到染坊去问伊凡,他却威胁我说不要再缠着他问这个问题。幸好,站在一旁的格里戈里肯用真相解开我的好奇。他支开小茨冈,把我放到膝头说:“当年,你舅舅把自己的老婆[3]打死了!现在,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谁叫他那么混账!这下你明白了吧。你可得当心,什么都想知道是很危险的!”
格里戈里像外婆一样温柔,不同的是,他镜片后的目光仿佛能看透一切,这一点我有些害怕。
我追问舅舅是怎么打死舅妈的,为什么打死她。格里戈里支支吾吾说不清,好像是因为嫉妒舅妈比他好,不过有一句话我却听他说得真切:“这一家子人,容不下好人!你去问一下你外婆,就会知道,他们是怎样想弄死你的父亲的!你外婆是个纯洁的圣徒,她什么都会告诉你的。”
说完,他推开了我,我心情十分沉重地向院子里走去。这时,凡纽什卡赶上来,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怕他,他是个好人哪!你往后直盯着他的眼睛看就好,他喜欢那种感觉!”
在外公家住了些日子,让我感到越来越别扭,因为我记得,我的父母不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总是一起做事情,肩并肩地依偎着;夜里,他们经常有说有笑,坐在窗子旁边大声唱歌,街上的行人都抬头看他们——那许多往上看的面孔,让我想起了饭后的脏碟子。
可是在这里,人们很少笑,偶尔有人笑,你却不知道为什么。争吵、恐吓、耳语是这里说话的常用方式。没人陪伴、照顾孩子,他们也如同尘土一般微不足道,也不敢大声玩闹。在这儿,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每天都忐忑不安、心事重重地看着周遭。
这段日子,外婆整天忙得团团转,也顾不上照看我,于是我就跟着小茨冈的屁股转,我们的友谊越来越深。每次外公打我,他就用胳膊帮我挡着,还指着红肿的地方说,帮我挡也没用,以后才不要管我。不过,下一次挨打,他还会伸出胳膊。
后来,我又知道了他一个秘密,对他的兴趣更浓了。
每逢星期五,小茨冈都会套上枣红马沙拉普去集市买东西。沙拉普是外婆的宝贝,它脾气可坏呢,只吃好东西。小茨冈穿上长到膝盖的皮大衣,戴上大帽子,系上一条绿色的腰带就出发了。有时候,天色很晚了还不见他回家。家里人就都十分焦急,跑到窗户前,用哈气融掉窗户玻璃上的冰花儿朝外张望。
“还没回来吗?”
“没呢!”
外婆比谁都急,一边巴望着,一边数落外公和舅舅,谁叫他们总没命地使唤小茨冈。
终于,小茨冈回家了!外公和舅舅们赶紧跑到院子里,外婆却抽着鼻烟落在后面,笨拙得像个冒烟的大熊。孩子们也跑出去了,兴高采烈地从雪橇上往下搬东西:鸡鸭鱼肉,应有尽有。
“让你买的都已经买了?”外公敏锐的眼光扫过雪橇上的东西。
“全买了。”小茨冈在院子里跳着取暖,啪啪地拍打着手套。外公严厉地训斥说:“别将手套拍坏了,那可是用钱买的!找回零钱了没有?”
“没有。”

外公绕着雪橇转了一圈儿:“我看,这些东西比计划要买的多哇,用钱能买回来这么多吗?我可不喜欢偷偷摸摸的事情。”他皱了皱眉,转身走了。
两个舅舅兴致勃勃地拿下鱼、鹅肝、小牛腿、大肉块,他们吹着口哨,掂着重量:“好小伙子,买的可都是好东西!”
米哈伊尔舅舅身上好像装了弹簧一样蹦来蹦去,闻闻这儿、嗅嗅那儿,眯缝着眼睛,咋着舌头。他耸着干瘦的肩膀,抄着手问小茨冈:“我得给你多少钱?”
“得10个卢布。”
“我看这些东西值15个卢布!你到底花了多少?”
“花了9卢布零10戈比。”
“好啊,90戈比又进了你自己荷包了!雅科夫,你瞧瞧这小子多会挣钱。”雅科夫打着哆嗦笑了笑:“瓦尼加,请我们喝点儿伏特加总行吧!”
外婆一边卸马套一边跟马儿说:“哎呀,我的小乖乖,小猫咪,又调皮啦?”高大健壮的沙拉普抖了抖鬃毛,用雪白的牙齿磨蹭着外婆的肩头,快乐地看着外婆低声叫着。
“吃点儿面包吧?”外婆将一大块面包塞进它嘴里,又兜起围裙在马头下面接着掉下来的面包渣儿。看着它吃东西,外婆似乎陷入了沉思。
小茨冈走过来:“老奶奶,这马可真聪明啊!”
“靠边站!别在这里耍滑头!”外婆跺了跺脚。
后来,我听外婆解释说,其实每次采买,小茨冈偷的东西比买的东西多。
“你外公给他五个卢布,他只花了三个卢布买东西,其余那些东西全是他偷来的!最开始他偷回东西的时候,大家都夸他能干,他心里可美了,谁知道就此养成了习惯,偷东西跟闹着玩儿似的!加上你外公自小就爱财,现在更贪财,一看见东西白白送上门,当然乐得合不上嘴。还有米哈伊尔跟雅科夫……”她说到这里,挥了一下手,闻了闻鼻烟,又接着说起来了:“廖尼亚,人世间的事就像花边,可织花边的却是个瞎老婆子,织出来的能是什么啊!小偷要是被抓住,就会被往死里打啊!”沉默一阵后,她又说道:“唉,上哪儿说理去呀!”
第二天我找到小茨冈问:“你会不会被抓住给打死呀?”
“抓住我?那可没那么简单!我眼疾手快,马也跑得飞快!”他得意地一笑,可立刻又皱起了眉头,“我知道偷东西不好,还很危险,可我只是玩儿呢!我也不想攒什么钱,因为根本攒不下,你的舅舅们盯着我要呢。抓走拉倒,反正我吃饱了,要钱也没啥用。”
他突然攥住我的手说:“啊,看你精瘦,骨头还硬,长大了力气一定特别大!听我的话,你跟雅科夫舅舅学吉他吧,小孩子学起来很容易的!看你这小不点儿,脾气倒挺大。你不喜欢你外公,对吗?”
“我也不清楚。”
“除了老太太,他们一家子我哪个也不喜欢——魔鬼才喜欢他们呢!”
“那么,你喜欢我吗?”
“你不姓卡希林,你姓彼什科夫,你是另外一个家族的人!”他忽然抱住我,低低地说:“唉,要是我有一副好嗓子,我就能把人们的心都照亮了,那该多好啊!……好啦,小弟弟你走吧,我要去干活儿了!”
他将我放到地板上,朝嘴里塞一把小钉子,先把一块湿湿的红布绷得紧紧的,再往一块大大的四方形木板上钉。
没想到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交谈。因为没过多久,他就死去了。
外公家的院子本来就拥挤而肮脏,再加上中间那个散发着苦味的橡木十字架,就更杂乱了。我刚来的时候它就放在那儿,不过还是崭新的。听说,这个十字架是雅科夫舅舅买回来的,他发愿要在妻子死去一周年的忌日时,亲自把它背到坟上。
那是刚入冬的一天,天气出奇的冷。外婆和外公一大早就带着三个孙子到坟地去了,我因为犯了错误而被关在家里。两个舅舅穿着黑色的皮大衣,将十字架从墙上拔了出来。格里戈里跟另外一个人把十字架放到了小茨冈的肩膀上。小茨冈一个踉跄又叉开腿,还好站稳了。
“怎么,挺得住吗?”格里戈里问道。
“说不清,很沉呢!”
米哈伊尔舅舅大喊道:“快点儿开门,瞎鬼!”
雅科夫舅舅说道:“瓦尼卡,你装蒜,咱俩加起来也不如你有力气!”
格里戈里打开门,叮嘱伊凡:“小心着点儿,千万别累着了!”
“秃驴快闪开!”米哈伊尔舅舅在街上喊,人们全笑了,大家似乎都期盼着把那个十字架快点儿弄走。格里戈里背着我到了染房,将我抱到一堆准备染色的羊毛上面,他说:“你外公今天兴许不会打你了,我看他眼神挺和气的!”他闻了闻锅中冒出来的蒸汽,“唉,小家伙,我跟你外公在一起待了37年,他的事我最了解。起初,我们是朋友,合伙做买卖。后来他当上了老板,我承认,他比我聪明。但是,上帝是最聪明的。尽管你还看不透别人,但是慢慢地都会了解的……孤儿,真苦哇!你的爸爸,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就啥都懂,他可是个宝贝疙瘩!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你外公才不喜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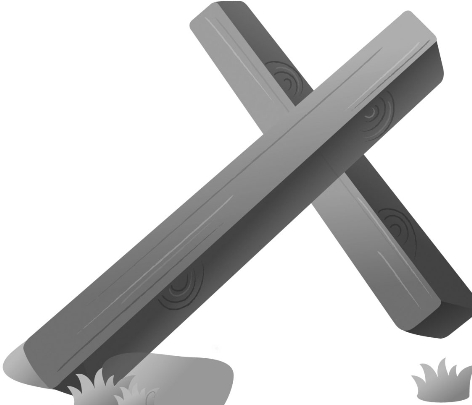
听着听着,我心里高兴极了。炉子里金红的火焰映红了我的脸,雾一样的蒸汽弥漫开来,它们升到房顶的木板上,变成了灰色的霜,有的顺着木板的缝隙继续上升,融到一线蓝蓝的天空里。屋外,风小了,雨也停了,阳光灿烂地照耀在雪地上,雪橇走在大街上时发出刺耳的尖叫。炊烟袅袅升起,轻淡的影子一拥一拥地滑过雪面,好像也在讲述着什么。
大胡子格里戈里高大瘦削,因为没戴帽子,一对大耳朵特别显眼,他极像善良的巫师。他搅着颜料,继续他的话题:“得用正直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即使是一条狗,你也要一样看待……”我正抬头打量他——这尊和外婆的鼻子有着同样红血丝的圣像——突然,他叫了起来:“啊,等一等,好像出什么事了!”他用脚关上了炉门,先竖着耳朵听了一下,然后一个箭步冲进了院子里。
我跟着跑了出去,看见小茨冈被人抬进了厨房。他躺在地板上,眉毛上挑,额头放射着一种奇怪的光,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只有暗紫的嘴唇轻轻地张合,吐出殷虹的血沫来。鲜红的血打嘴里流到脸上又流到脖子上,最后流向地板,很快他就被泡在了血泊里。他的两腿痛苦地扭曲着,一部分血把它们黏在了地板上,大部分血像一条红色的小溪流向门口。
小茨冈挺挺地躺着,只有手指头还在微微抓动。保姆叶夫根尼娅把一支细蜡烛往伊凡手里塞,可他根本抓不住,蜡烛倒了,栽进了血泊之中,叶夫根尼娅又塞回去。人们议论纷纷,我有点儿腿软,赶忙扶住了门环。
雅科夫舅舅战战兢兢地来回走着,低声道:“他摔倒了!被压住了!砸在背上!我们一看不行,就赶忙扔掉了十字架,要不我们也会被砸死的。”他面如死灰、两眼无神,而且疲惫不堪。
格里戈里怒喊道:“就是你们砸死了他!”
“是的,那又怎么样?”
“你,你们!”
门槛边上的血凝聚起来,渐渐发黑。小茨冈仍旧不停地吐着血沫,低吟声越来越小,人仿佛也憋了下去、平了下去,贴在地板上,似乎要陷进去。
“米哈伊尔去找爸爸了!是我雇了一辆马车把他拉了回来!唉,幸亏不是我亲自背着,否则……”雅科夫舅舅低声说。
叶夫根尼娅还在将蜡烛往小茨冈手里塞,烛泪滴进了他的手掌心。格里戈里怒吼道:“行啦,你让蜡烛立在地板上就行了,笨蛋!”
“哎!”
“把他的帽子摘下来。”
保姆笨拙地把伊凡的帽子拿下来,于是,他的后脑勺儿沉沉地落在地板上。他的头歪向一边,更多的血沿着嘴角往外淌。
我等了很久,希望小茨冈休息好了后坐在地板上,吐一口唾沫说:“呸,真热啊……”
但是,没有。
第三天,他还是那样躺着,一直憋下去。他的脸黑了,指头也不动了,嘴角上的血沫也没了。三支蜡烛围着他的头惨白地立着,黄色的火焰摇曳着照亮他蓬乱的头发。
叶夫根尼娅跪在地上哭道:“我的小鸽子,我那小宝贝儿……”
我觉得特别冷,十分害怕,就爬到了桌子下面躲了起来。这时,外公穿着貉绒大衣,步伐沉重地走进来。穿带毛尾巴领子皮大衣的外婆、米哈伊尔舅舅、孩子们,还有很多生人,也都挤了进来。外公将皮大衣往地上一扔,吼道:“你们这些浑蛋!一个多么能干的小伙子就让你们害死了!再过几年,他就是无价之宝啊!”
地板的衣服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向外爬,刚好碰到了外公的脚。他踢了我一脚,举起拳头朝舅舅们挥舞着:“你们这些狼崽子!”他一屁股坐到了凳子上,呜咽了几下,但却没有流泪,“我知道,他是你们的眼中钉!……唉,凡纽什卡,你这个傻瓜!……现在怎么办?哎,怎么办?上帝怎么就不帮助我们呢!嗯?老婆子?”
外婆一直趴在地板上,不停地抚摸着伊凡的脸和身子,搓他的手像取暖一样,把蜡烛都给碰倒了。听到外公叫她,她慢慢地站了起来,脸色和身上的黑衣服一样,两眼瞪得溜圆,可怕地低吼着:“滚!都给我滚出去!可恶的畜生!”
小茨冈就这么死了,悄声无息地被埋掉了。过了不久,人们也渐渐地就把他淡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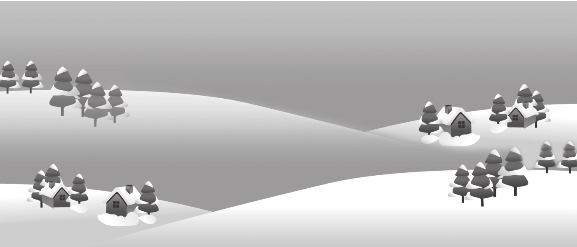
【注释】
[1]地名,在今天的俄罗斯高尔基州,是一座古老的码头城市,毗邻伏尔加河。
[2]大卫王是公元前11世纪末至公元前960年左右,犹太以色列的国王,他多才多艺,写了许多诗篇。
[3]雅科夫的第一任妻子卡希林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