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外公和外婆都是虔诚的教徒,晨祷、晚祷的功课从不怠慢。然而,上帝好像故意戏弄他们似的,在一天夜里降下一场火灾。阿廖沙既害怕又觉得有趣,就躲起来观察着一切。当时,外公和舅舅要么哭哭啼啼不知所措,要么拿着工具手忙脚乱,只有外婆英勇而镇定地指挥大家灭火,不仅发动邻居们一起帮忙,还奋不顾身地闯进火海抢救出快要爆炸的硫酸盐。
在大家的努力下,大火终于被扑灭了,染坊的损失惨重,外公吹胡子瞪眼睛地要找嫌疑人格里戈里算账。然而,还没等他缉拿“凶犯”,纳塔利娅舅妈就出事了……
这天晚上,外婆正虔敬地向上帝祷告,外公冲了进来焦急地吼道:“老婆子,上帝来了!外面着火了!”
“什么?啊!”
外婆腾地从地板上一跃而起,夺门而出。
“叶夫根尼娅,快把圣像拿下来!纳塔利娅,你倒是给孩子们穿上衣服哇!”外婆大声地指挥一切,外公却只是痛哭。我跑出去,看见厨房的地板上飘动着一簇簇闪闪烁烁的红光。
雅科夫舅舅好像被地上的红光烫了脚,一跳一跳地穿靴子。他大喊:“是米什卡放的火!他逃啦!”
“浑蛋,你胡说!”外婆大声训斥着他,差点儿把他推到。
火舌乱卷着房顶,舔着门窗,在寂静的黑夜里有如红色的莲花,蹿动着怒放!霎时,白雪成了红雪,耀眼的红光流泻而出,金色的带子好像要给染房系上一个复杂的领结,升腾着的黑云,将天上的银河若隐若现地藏起来。墙壁战栗起来,“突突”“嘎吧”“沙沙”“哗啦”,各式各样的奇怪声音杂乱地演奏着,染房被大火装饰上教堂那样的金顶,引得人不由自主地靠近它,想拥抱它。

院子里混乱一片,我害怕极了,披着笨重的短皮大衣,胡乱穿着不知道谁的鞋邋邋遢遢地躲在台阶上。外婆头顶空口袋、身披棉被,飞冲进火海去抢硫酸盐——那东西可是会爆炸的。外公大叫着要格里戈里拉住她,可是外婆已经进去又钻出来了,她浑身冒着烟,手里端着一大桶硫酸盐。“老头子,快将马都牵走!”外婆哑着嗓子喊着,“还不快帮我脱下来,我都快烧着了!”
格里戈里铲起大雪块儿扔向染坊,舅舅们拿着斧头乱蹦乱跳,不知道在干什么。外公忙着朝外婆身上扔雪,外婆将那个桶塞进雪堆里之后,就打开大门,向跑进来的人们哀号:“各位街坊邻居,快来救火吧!马上就要烧到仓库了,我们家烧没了,你们也要遭殃的!快把仓库的顶盖掀开,先把干草都扔出去!格里戈里,快点儿!……雅科夫,别乱跑了,把斧头和铁锹都拿来!……各位各位,大家行动起来吧,愿上帝保佑你们!”
外婆的表现正像这场大火一样有趣。她一身黑衣,可是跑到哪里都亮闪闪的,似乎被那火焰抓住了。她东奔西跑,指挥着所有人。沙拉普受惊了,跑到院子里撞倒了外公,火光好像钻进了它的大眼睛里,它躁动着,不安地嘶吼起来。
“老婆子,拉住它!”
外婆张开双臂跑过去,马儿一看外婆来了,就长鸣了一声顺从地让她靠近。
“别怕,别怕!亲爱的小老鼠,你不会有事的……”她轻拍着它的脖子说。这个比她大三倍的“小老鼠”乖乖地跟着她走向门口,还打着响鼻。叶夫根尼娅将哇哇直哭的孩子们一个一个抱了出来,她大声叫:“瓦西里·瓦西里奇,我找不到阿列克谢……”
其实,我就藏在台阶底下,正怕她将我弄走呢。
“好啦,走吧走吧!”外公一挥手,染坊的顶就塌了,几根梁柱上窜着烟,直冲夜空。红的、绿的、蓝的旋风,伴着噼啪的响声,将一团团火焰扔到院子里,就像跟正用铁锹铲扔雪的人们抗议似的。几口大染锅咆哮着、沸腾着,散出难闻的气味,熏得人直流眼泪。我呛着喉咙从台阶底下爬了出来,正好碰着外婆的脚。
“快走开,会砸死你的!”外婆大叫一声。
突然,有个人骑着马冲进院子。他头戴铜盔,高高地扬着鞭子:“快点儿让开!”枣红马吐着白沫,马铃的急促脆响戛然而止。
我被外婆撵到厨房里,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朝外看。大火终于熄灭了,警察赶走人群,外婆也走进了厨房。她坐在我身边安慰我,身子一晃,一切又似乎回到了平静的夜晚。
“是老婆子吗?”还没看见外公进门,就先听到了他关切的声音。
“嗯。”
“烧着没?”
“没事!”
他划了根火柴,一点黄光照亮了他的脸——都是烟灰,像黄鼠狼一样。点上蜡烛,他靠着外婆坐了下来。
“你去洗洗脸吧!”其实外婆自己脸上也黑乎乎的。忽然,外公叹了一口气:“感谢上帝的慈悲,赐给你智慧和力量,否则……”他摸了她的肩膀,“上帝保佑!”
外婆也笑了一笑,刚要说些什么,外公的脸却突然一沉:“哼,都是格里戈里这个浑蛋,粗心大意的。我看他是干够了,也活到头儿了!……雅什卡有正在门口哭呢,这个懦夫,你去看看他吧!”
外婆收起笑容,吹着手指头走了出去。
屋子里就剩下我跟外公了,他开始自言自语,又好像在跟我说话,话里话外都在夸奖外婆很能干,还不自然地安慰了我几句,一边说着,一边脱掉衬衫,洗了个脸,扭过头凶巴巴地问我:“你坐在这儿干吗?怎么还不去睡觉?”
我赶紧去睡觉,但刚躺上床,一阵鬼叫似的喊声又把我拽起来。我跑到厨房里,看见外公手已经站在那里了,他拿着烛台问:“老婆子、雅科夫,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爬到炕炉上,安静地看着他们一片忙乱。号叫声一起一伏地很有节奏,外婆有条理地指挥大家做事情,格里戈里在添柴烧水,可舅舅他们却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我被格里戈里逮住了,于是就问:“这是要干吗?”
“你的纳塔利娅舅妈要生孩子!”他面无表情地回答。回忆起来,我母亲生孩子也没有这么叫啊。格里戈里忙活完,就抽起烟锅来,听着舅妈的号叫,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你外婆还去接生!她也不看看自己都烧成什么样子了……你听你舅妈叫的,谁听了都忘不了哇!生孩子困难着呢,可人们却不尊敬妇女!你可得尊敬女人,尊敬女人也就是尊敬母亲!”
听着听着,我坚持不住了,终于打起瞌睡来。正当我睡得香的时候,吵闹的人声——应该是喝醉了的米哈伊尔舅舅,还有咚咚的关门声把我吵醒了,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几句很奇怪的话:
“上帝之门已经开启……”
“来来来,半杯油、半杯甜酒,还有一勺烟渣子……”
“让我看看……”那是米哈伊尔舅舅无力的叫声。我循声看去,他瘫在地板上,两只手没骨头似的拍打着地面。我忽然意识到炕上非常热,已经烫到我了,于是就腾地跳下来。这时,米哈伊尔舅舅突然使劲抓住了我的脚脖子,我向后躺去,头重重地砸到了地板上。
“浑蛋!”我大骂道。
他突然跳了起来,把我拉起来又扔到了地上:“摔死你这个小浑蛋……”我只觉得身子一阵刺痛,就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外公的膝盖上。他摇晃着我说:“上帝啊,我们是你的不肖子孙,谁都不能被宽恕,谁都不能……”
蜡烛有气无力地发着光,窗外的晨曦已经很耀眼了。
外公看我醒了,就关切地问这问那,我很难受,不想回答,只是默默看着四周的一切——这也太奇怪了:一群陌生人塞满了大厅,神甫、几个穿军装的老头儿,还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吗的;他们一动不动,似乎在谛听上帝的声音。
雅科夫舅舅站在门边上,外公跟他说:“你,带他睡觉去吧!”我跟着舅舅去了外婆的房间,刚爬上床,他低声对我说:“你的纳塔利娅舅妈[1]死了!”
我顿了一下,但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好长时间都没见过她了,这就是我身为一个孩子的逻辑。
我很想见外婆,雅科夫舅舅说她在大厅里,我只好躺在床上东张西望。墙角上挂着外婆的衣服,那后头好像藏着个人;窗户上好像有一张人的脸,他的头发特别长,还是个瞎子。我吓得藏到了枕头下,露出一只眼窥视着门口。太热了,我喘不上气来。突然,我想起了小茨冈死时的样子,地板上的血迹在慢慢地流淌到门口……似乎一个重载卡车压过我身上,把一切都碾碎了……
不知什么时候,门缓慢地打开了。外婆虚弱地用肩膀顶开门,几乎是爬着进来的。她朝着长明灯伸出两只手,孩子般地哭叫:“我这手……真疼啊!”——那是替舅妈接生的双手。
冬去春来,这个家终于分了。毫无悬念,雅科夫舅舅在城里,米哈伊尔被分到了河对岸。外公在波列沃伊大街[2]上买到了一所很有趣的大宅子:上面是阁楼,楼下是酒馆,后花园外有个山谷,四周都种满了柳树。
“哎呀,这可都是好鞭子啊!”外公一边踩着融化的雪,一边指着树条说,他又狡猾地眨了眨眼睛,“你快要学认字了,嘿,到时候鞭子是最有用的。”
没过多久,房客们陆陆续续把这个宅子住满了,外公只给自己在楼上留了一间,外婆和我则住在顶楼上。每天一大早,外公就到两个儿子的染坊去搭把手,可晚上回来总是又累又气的。外婆在家做饭、缝衣服、在花园里种地,忙得团团转。
从早到晚,房客们闹哄哄地走来走去,邻居的女人们经常跑过来嘁嘁喳喳说个不停,还总喊外婆的名字:“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
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对谁都是那么和蔼可亲,无微不至地关照每个人,常常给她们介绍家务方面的常识,什么蔬菜储藏、酸奶的做法、护理皮肤……她还替人家接生、调解家庭纠纷、给孩子们看病。

有一次,我问外婆:“你会巫术吗?”
她笑了,想了一下说:“巫术可是一门很难的学问啊,我不行,不认字啊!你外公就认得,圣母可没给我智慧!”
接着,她说起了她自己的事:
“我自小就是个孤儿,我母亲很穷还是个残废——那是让地主吓的,跳窗户的时候摔残了一半身子,右手也萎缩了。对于一个以做花边为生的女佣来说,这相当于要了她的命的!可恶的地主赶走了她,她就到处流浪,乞讨过活。
“好在,那时候的人比现在富有,巴拉罕纳城的木匠和织花边的人都十分善良。每年秋天,我跟母亲就留在城里要饭。等到大天使加百利[3]带来了春天,我们就赶着走赶着住。我们去过穆罗姆和尤列维茨,还有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春夏之后,在大地上四处流浪,真是一个美事啊!茸茸的青草里点缀着盛开的鲜花,温暖香甜的空气真舒服哇!有时,母亲会唱起歌,花草树木都在听呢!
“流浪的生活很有趣,可我逐渐长大了,总不能一直跟着母亲要饭。所以,我们就在巴拉罕纳城住了下来。每天她都上街去乞讨,要是赶上教堂布施那我们就有福了;我呢,就坐在家里拼命地学习织花边,因为学好了就能帮母亲了。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我就学会了所有技法,人们都慕名来找我做手工呢。‘喂,阿库利娅,替我织一件吧!’听到他们这么说,我特别高兴,跟过年似的!这当然都是妈妈教得好,尽管她只有一只手,可她很耐心、很会指教。可是,我有些怕她呢。每次我说:‘妈妈,你别再去要饭了,我能养活你的!’她就会严厉地说:‘闭嘴傻丫头,这是在替你攒嫁妆钱哪!’
“后来,你外公就出现了。他可是个不错的小伙子,22岁就当上一艘大船的工长了!第一次见到他母亲的时候,她仔细地审视了我一番,觉着我手挺巧,又是讨饭人的女儿会很老实。她是卖面包的,凶着呢……唉,别想她了,上帝心里什么都明白。”
说到这儿,她笑了,鼻子有趣地颤抖着,眼睛闪闪发光,十分亲切。
忽然有一天,外公拿了一本巴掌大的书,说要教我识字。他用消瘦而滚烫的胳膊揽着我的脖子,越过我的肩头,用指头点着我面前的字母。他身上那股味熏得我喘不上气来——酸味、汗味和烤葱味。可是他却跟没事人一样吼着字母和单词。我念着它们,脑海里不断联想着画面,有的画面里有蚯蚓、外婆、格里戈里,不过好像每个都有外公涨红的、吼叫的脸。
他以各种各样的顺序提问我,那些字母就像他的玩物。我也跟他较起劲来,也扯着嗓子大声喊。没想到,外公居然很高兴。
我的功课还算有进步,外公对我的关心多了,打骂少了。没多久我就能把诗拼读出来了。吃过晚茶以后,就由我来读圣歌。我用字棒指着书,移动地念着,很无趣。
“‘布拉任-穆日’[4],就是雅科夫舅舅吗?”有一次,我这样问道。
“我打你的后脑勺儿,还没弄清哪个是有福之人!”外公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他这假模假样的生气表情,我已经习惯了。
果然,过了一小会儿,他就不气了,只是嘟囔着说:“你雅科夫舅舅唱歌时简直是大卫王,可他干的那些事,却像个恶毒的押沙龙在撒泼[5]!唱啊跳啊的都是花拳绣腿,能弄出什么名堂?”
我读不下去了,认真地听外公说。他面孔很阴郁,眯着眼,目光越过我的头顶延伸到窗外,流露出一丝丝抖动。
外公教我读书的时候很卖力,可是求他讲个故事却很费力。有一次,我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他终于同意了。虽然外公更爱听笑话,不过我知道他熟悉所有诗篇和里面的故事,看他每天的祷告就知道了。他靠在那把古老的安乐椅上,望了一眼天花板,就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听说,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乡来了一伙土匪。我爷爷的爸爸想去报警,没想到被土匪用马刀砍死了,给塞到大钟底下。那个时候我太小,不记事。要说记事,那是从1812年,我12岁的时候。那年,巴拉罕纳城来了30多个法国俘虏[6],他们长得十分矮小,破衣烂衫的还不如要饭的,哆哆嗦嗦地傻愣在那里。老百姓想围上去打死他们,押送的士兵把人群撵散了。那些法国人被安置在城里,跟大家混熟了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们也都是普通人,有时候还唱歌呢。
“过了不久,打尼日尼来了一大群有钱的老爷,可是坐着三套大马车来的。他们中有的人见了那些法国俘虏就打骂,有的人却用法语跟他们交谈,还给他们送衣服和钱。有个年纪大的法国人哭着说:‘我们都是被拿破仑害的!你瞧瞧,还是俄国人心眼儿好,连老爷们都可怜我们……”
沉默了一会儿,外公用手抓了抓头,好像在努力地追忆着曾经的岁月:
“冬天里,暴风雪肆虐,那刺骨的严寒真能冻死人!那些法国俘虏常跑到我们家窗户下唱啊跳啊,还敲玻璃,讨口热面包吃。哦,对了,我母亲是卖面包的。她就从窗口把面包递出去,那法国人一把抓过来就往怀里揣。嘿,那可是刚出炉的呀!他们竟不管不顾地贴在心口上!那年月,很多法国人都冻死了,没办法,他们哪里见过这么冷的天!
“我家菜园里有间浴室,两个法国人就住在里头,一个是军官和一个是勤务兵。勤务兵叫米朗,军官瘦得只剩皮包骨,穿了一件女外套,才到膝盖。那军官很有礼貌,可嗜酒如命。那时候,我母亲偷着酿啤酒卖,他总要买去大喝一通,喝完就唱歌。他学了点儿俄国话,老说:‘啊,你们这儿天不是白的,是阴郁的、凶残的!’他的俄语不标准,不过我们还是能听懂的。是啊,我们这儿跟伏尔加河下游没法比,那里暖和多了。过了里海,就一年四季没有雪。《福音》《使徒传》都没有提过雪和冬天,耶稣就住在那里……好了,你读完《圣诗集》,咱们就来读《福音》!”
说完,他就睡着了似的不作声了,只斜着眼瞪着窗外,我觉得他更瘦小了。
“接着讲好不好?”我小心翼翼地说。

“啊……好!”他一抖像是醒过来,咳嗽了一声接着说:“法国人也是人啊,跟我们一样啊。他们还叫我母亲‘玛达姆’呢,是‘太太’的意思啊!啊,太太、贵妇人,但我们这位太太能一口气扛5普特①重的面粉,我20岁的时候,她还能毫不费力地揪住我的头发教训我呢,那力气可真大得吓人。
“话说回来,勤务兵米朗特别喜欢马,他常常挨家挨户地比画着要给人家洗马!开始大家还怕他使坏,可后来都主动接近他:‘米朗,洗马!’嘿,他可高兴了。他是个红头发的大鼻子家伙,嘴唇厚厚的。除了洗马,他还擅长给马治病。后来,他在尼日尼当了个马医,不过好景不长,他疯了,最后被人活活打死了。
“有一年春天,那个军官生病了,就在春神尼古拉纪念日那天,他坐在窗前,把头伸了出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可没想到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我很难过,偷偷地哭了一场,他对我还是很好的,老贴着我的耳朵亲切地说些法国话,尽管我不懂,但是能感受到他的善意。人与人的交情,不是钱能买到的。我打算跟他学法语,可母亲不让,还把我领到神父那儿,不仅我被打了一顿,那个军官还被控诉了。唉,亲爱的孩子,那段日子实在太难了,你没经历过,就当别人替你受了那份罪吧……”
天完全黑了,外公的身影似乎变大了,眼睛像猫一样放着光亮,语速快了不少,表情和激动。一讲到自己的事,外公就一反常态,不再小心谨慎。说实话,我不喜欢他这样,可他此时的样子,却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他自顾自地回忆着往事,也不让人插嘴提问,可我偏问:“法国人和俄国人哪个好哇?”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是什么样子的!”
“嗯……那俄国人坏吗?”
“有好的,也有坏的。我看奴隶时代的奴隶主就不好,那时候老百姓都被他们绑着。现在大家自由了,但却穷得连面包和盐都没有。老爷们当然不太和善,但他们都很精明,当然也有傻蛋。”
“俄国人力气很大吗?”
“当然,有好多大力士呢,可只有力气有啥用,要有智慧才行,力气再大还能比马大?”
“拿破仑是做什么的?”
“他呀,是个野心家,想征服全世界后,让所有的人过一样的生活,没有老爷也没有下人,大家都平等;当然信仰也只能有一个,那简直是胡闹!就说这海里的东西吧,只有龙虾长得一模一样,可鱼有各种各样的呢:鳟鱼和鲶鱼见面就打架,鲟鱼和青鱼也不友好。咱们国家也曾出过拿破仑派,什么拉辛·斯杰潘·季莫菲耶夫[7]、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8]……”
他又停下来了,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我,怪不舒服的。
说了那么多故事,他从没和我说起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和外公说话的时候,外婆也常常走过来。她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听,只是偶然柔和地插上几句。这天,外婆突然问道:“老头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去穆罗姆[9]朝圣,那是什么时候来着?”
外公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是,是在霍乱大流行之前,就是在树林里捉拿奥洛涅茨人那一年吧?……对了,对了!没错!”
外婆又问了些别的,她和外婆你来我往地说着,我好像不存在一样。
“你看看,你看看,”外公念叨着,“啥也忘不了!你还记得生瓦里娅之后的那年夏天吧?”
“哦,那是1848年,远征匈牙利的那一年,那个教父吉洪不是在圣诞节的第二天被拉了壮丁送到战场上去了吗……打那以后就没消息了……”外婆叹了一口气。
“是啊!不过,从那年起,上帝的恩泽就流连在咱们家了。唉,我的瓦尔瓦拉……”
“得啦,老头子!”
外公的脸阴沉下来:“才不!心血都白费了,这些熊孩子没一个有出息!”他激动地地乱喊乱叫起来,向外婆挥舞着瘦小的拳头,“都是你惯坏了,臭老婆子!”
他还跑到圣像跟前,捶胸吼起来:“上帝啊,我如此罪孽深重吗?为什么这么惩罚我?”他凶恶地、不甘地流着眼泪。外婆画了个十字,低声地安慰他:“你别这样!上帝是最公平的!比咱们儿女强的人家也没有几个呀!老爷子,谁家不是吵哇闹哇的,这是所有父母承受的痛苦,不光你一个人哪……”
外婆的话奏效了,外公渐渐平静了下来,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可是接下来,闹剧发生了!外公居然对想再安慰他几句的外婆大打出手,外婆的嘴唇被打出了血,不过外公也没个好,差点儿撞上门板。外婆不管发疯的外公,自己走回房间去。
“臭老婆子你别走!”外公扶住门框,奋力拉着。
眼前的一切令我难以置信,这是外公第一次在我面前打外婆,我愤怒极了,感到莫大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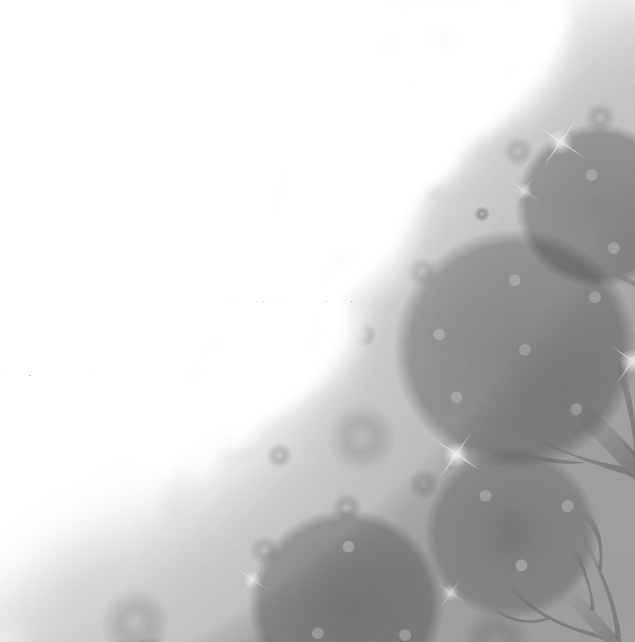
当我缓过神来,看见外公正跪在地上苦恼地喊着“上帝”,我才不理他,一个箭步冲出去追外婆。等我冲上顶楼,外婆正在小心地漱口。
“你疼吗?他怎么这样哪?”
她吐了口血水,看了看窗外说:“没事……他老是觉得憋闷、不如意,总爱发脾气……你快睡吧,别想太多啦……”
我又问了她一句,她严肃起来:“快点儿去睡觉!怎么不听话呢?”
我不情愿地上了床,一边脱衣服,一边望着外婆。她在窗边坐下,时不时往手绢里吐着什么。那青色的窗户外,闪烁着点点星光,夜很安详。不一会儿,她在寂静中走了过来,摸着我的头说:“睡吧孩子,我得去看看他……你别太向着我,也许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快睡吧!”她亲了亲我,就走了。
我打心底里难过,就下床来走到窗前,望着漆黑而清冷的街道,鼻子里的酸楚遮盖了我对孤独的恐惧。

【注释】
[1]米哈伊尔的第一任妻子玛利娅,1869年死于难产。雅科夫的第一任妻子也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亚历山大和卡捷林娜。
[2]现在的高尔基大街。
[3]宗教神话中的天使长,具有破坏人间一切污秽事物的职责,曾向未婚的圣母玛利亚预言耶稣降生。3月26日是加百利大天使日,也是冬天结束的日子。
[4]源自《旧约》,意思是“有福之人”。
[5]押沙龙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容貌俊美,不受约束,刚愎自用。为了王位的继承而发动叛乱,最后死在大卫的侄子手中。
[6]1812年6月,拿破仑率领50万大军入侵俄国。起初,俄国军队处于与劣势,并与法军进行了惨烈厮杀,为了保存实力,俄军坚壁清野,撤出莫斯科后放火烧城。法军入城后无法补给,在俄军的游击战下终于溃败。
[7]斯杰潘·季莫菲耶维奇·拉辛(约1630—1671)俄国农民起义领袖,顿河哥萨克人。17世纪60年代末组织领导了俄国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拉辛农民起义。
[8]叶米里扬·伊凡诺维奇·普加乔夫(约1742—1775),俄国农民起义领袖。1773年,普加乔夫聚集了80名哥萨克人起义,揭开了俄国历史上一场反对农奴制压迫的农民战争的序幕。
[9]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著名的科西玛和达米安大教堂,还有圣三一修道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