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阅历的逐渐丰富与思想的日渐成熟,托尔斯泰将精力转移到了写作上,同时他也发现,他的思想可以沿着这些作品传达到人们的心中,这无疑是一个思想家最想看到的景象。那么他的思想都在写作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童年》于1851年秋开始创作,1852年7月2日完成。这是很奇怪的——在使他陶醉的自然界中,在簇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在一意要发现为他所未认识的热情的世界时,托尔斯泰居然会在这第一部作品中追忆他的往事。不过他写《童年》时,正因病处于休养的闲暇中,既孤独又痛苦,正有感伤的倾向,过去的回忆便在他眼前温柔地展现了。最近几年的颓废生活,使他感到在筋疲力尽般的紧张之后,去重温“无邪的、诗意的、快乐的、美妙的时期”的幼年生活,追寻“温良的、善感的,富于情爱的童心”,于他自另有一番甜蜜的滋味。
后来他说自己的这本书糟透了,毫无可取之处。
但只有他一个人抱有这种见解。他获得普遍的成功,虽然其中含有魅人的诗意、细腻的笔致、精微的情感,让以后的他讨厌。但这正是别人爱好的理由:书中笼罩着一种温柔的感伤情调(这是他以后反感、摒除的)。这感伤情调,我们是熟识的,我们熟识这些幽默和热泪,它们是从狄更斯那里来的。他自己所说的还有两种影响:斯特恩与特普费尔。
紧接着,《童年》中热情而狡猾的纯朴,移植在一个更为贵族的环境中。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托尔斯泰的性格,观察的大胆、真诚,对于爱的信心,都显然明确地形成了。在这部短篇小说中,他描绘的若干农人的出色的肖像已是他后来写的《民间故事》中最美的描写的发端:如他的《养蜂老人》和《两个老头儿》。
名师指导
反衬出了托尔斯泰细致的观察和对停止战争的呼吁。
但这时期的代表作却是直接灌注着他当时情感的作品,如《高加索纪事》的第一篇《侵略》,其中壮丽的景色,尤其动人。《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个典型人物在此已在尝试着生活了:如赫洛波夫大尉那个真正的英雄,他去打仗,绝非为了他个人的高兴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是“那些朴实的、镇静的、令人欢喜用眼睛直望着他的俄罗斯人物”中的一员。笨拙的、有些可笑的,从不理会他周围的一切,在战事中,当大家都改变时,他一个人却不改变;“他,完全如大家一直所见的那样:同样镇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调,在天真而阴郁的脸上亦是同样质朴的表情”。在他旁边,一个中尉,扮演着莱蒙托夫式的英雄,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却装作粗野蛮横。还有那可怜的少尉,在第一仗时高兴得了不得,可爱又可笑地,准备抱着每个人的颈项亲吻的小家伙,愚蠢地死于非命。在这些景色中,显露出托尔斯泰的面目,他冷静地观察着而不参与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他已发出停止战争的呼声:
“在这如此美丽的世界上,在这广大无垠、星辰密布的天空之下,人们难道不能安适地生活吗?在此他们怎能保留着恶毒、仇恨和毁灭同类的情操?人类心中一切恶的成分,一经和自然接触便应消灭,因为自然是美与善的最直接的表现。”
在这时期观察所得的别的高加索纪事,到了1854—1855年间才写成,例如《伐林》,一种准确的写实手法,稍嫌冷峻,但充满了关于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的记载;1856年他又写成了《在别动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熟人的相遇》,描写一个失意的上流人物,变成一个放浪的下级军官,懦怯、酗酒、说谎,他甚至不如他所轻视的士兵,他们中最渺小的也要胜过他百倍。
名师指导
名师指导
表现出托尔斯泰内心的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情。
名师指导
写出了托尔斯泰作品里的主人公临死时欢悦的心态。
在这一切作品之上,矗立着这第一座山脉的最高峰,托尔斯泰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青春的歌曲,亦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白雪连绵的群山,光亮的天空映射着它们巍峨的线条,它们的诗意充满了全书。在天才的笔墨下,这部小说是独一无二之作,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青春的强有力的神威,永远不能复得的天才的飞跃。”简直是春泉的狂流!爱情的洋溢!
“我爱,我那么爱!……勇士们!善人们!他反复地说,他要哭泣。为什么?谁是勇士?他爱谁?他不大知道。”
这种心灵的陶醉,无限制地流溢着。书中的主人公奥列宁和托尔斯泰一样,到高加索来寻求奇险的生活;他迷恋上了一个高加索少女,沉浸在种种矛盾的希望中。有时他想:“幸福,是为别人生活,牺牲自己。”有时他想:“牺牲自己只是一种愚蠢。”于是他简直和高加索的一个叫叶罗什卡的老人同样地想:“一切都是值得的。神造出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欢乐,没有一件是犯罪。和一个美丽的女子玩不是一桩罪恶而是灵魂得救。”可是又何必用思想呢?只要生存便是。生存是整个的善,整个的幸福,至强的、万有的生命——“生”即是神。一种狂热的自然主义煽惑而且吞噬他的灵魂。临死前,他“突然感到无名的幸福,依了他童年的习惯,他画着十字,感谢着什么人”,他在此不再是一个俄国绅士,只是一个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麋鹿,如在他周围生存着、徘徊着的一切生物一样。但他的心是欢悦的。
在青春的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生活在对于力、对于人生之爱恋的狂热中。他抓住自然并和自然融化,对着自然发泄他的悲愁、他的欢乐和他的爱情。但这种罗曼蒂克的陶醉,从不能混淆他清晰的目光。自然与人间的对峙,是本书的中心思想,亦是托尔斯泰一生最爱用的主题之一,这也是他的信条之一。而这种对峙已使他找到《克勒策奏鸣曲》的若干严酷的语调,以指责人间的喜剧。但对于一切他所爱的人,他亦同样的真实——自然界的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和他的朋友们都受着他明辨的目光烛照,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恶习,他都一一描画无遗。
高加索,尤其使托尔斯泰唤起他自己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
他说:“儿时我不加思想,只因热情与感伤而信仰。十四岁时,我开始思虑着人生问题,而因为宗教不能和我的理论调和,我把毁灭宗教当作一件值得赞美的事——于我一切是明白的、合理的,一部一部分析得很好的,而宗教,却并没安插它的地位……以后,到了一个时期,人生于我已毫无秘密,但从那时起,人生亦开始丧失了它的意义。那时候……这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的、苦恼的。我竭尽我所有的精神力量,如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地做一次那样……这是殉道与幸福的时期……我发现一条简单的、古老的,但为我现在才知道而一般人尚未知道的真理——我发现人类有一点不朽性,有一种爱情,为要永久幸福起见,人应当为了别人而生活。这些发现使我非常惊讶,因为它和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复向前探寻转而到《圣经》中去求索了。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我竭尽我灵魂的力量寻找,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这样,只有我和我的宗教了。”
他又说:“……我认为,没有宗教,人是既不能善,亦不能幸福;我愿占有它较占有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牢固;我觉得没有它,我的心会枯萎……但我不信仰。是人生使我心中产生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生……我此时感到心中那么枯索,需要一种宗教。神将助我,这将会实现……自然对于我是一个引路人,它能导引我们皈依宗教,每人有他不同且未知的道路,这条路,只有在每人心灵的深处才能找到……”
1853年11月,俄罗斯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应召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务,以后又转入克里米亚军队。1854年11月7日,他到达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热情与爱国心。他勇于尽责,常常处于危险之境,尤其在1855年4月和5月间,他三天中便有一天在第四号棱堡的炮台中服务。
名师指导
写出了托尔斯泰的思想轨迹,表现了他内心的伟大、孤独和迷茫。
名师指导
突出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也强调了不得不中断写作的原因。
成年累月地生活在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和死亡较量着,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和神交谈着。他感谢神在危险中保护他,并请求神继续予以默佑。
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他重新开始写作。在枪林弹雨之下,怎么能有精神上的自由来让他写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呢?那部书的紊乱及其抽象分析的枯燥,大抵是它诞生时的环境造成的。但对这些模糊的幻梦与思想,他竟有镇静深刻的探索。作品显得非常坦率。在描写春日的城市风光、忏悔的故事、以及为了已经遗忘的罪恶而奔往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又有多少清新的诗意!一种热烈的泛神论调,使他书中若干部分含有一种抒情的美,其语调令人回想起《高加索纪事》。
但当前的现实在他心中较之过去的梦境更有力量,它迫使他注意,《青年时代》因此没有完成。他在棱堡的障蔽下,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同伴间,观察着生者与垂死者,并将他们和自己的苦恼记录在令人难忘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之中。
这三部纪事——《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往常是被人笼统地加以统一批判的,但它们实在是不同的,尤其是第二部,在情操上,在艺术上,与其他两部不同。第一、第三两部被爱国主义统治着,第二部则含有确切不移的真理。
名师指导
突出表现了托尔斯泰文笔的动人之处。
据说沙俄皇后读了第一部纪事之后,不禁为之流泪,以致沙皇下令把托尔斯泰调离危险区。这是我们很能了解的。在第一部中只有鼓吹爱国与战争的成分。托尔斯泰入伍不久,他的热情没有动摇,他沉溺在英雄主义中。他在护卫塞瓦斯托波尔的人中还未看出野心与自负,还未窥见任何卑鄙的情操。对于他,这是崇高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媲美”。此外,作者在此不靠想象,只是以清明的目光观看,但他讲述的方式,却太拘谨:“你看……你进入……你注意……”这是在巨帙的新闻记录中加入对于自然的美丽的印象作为穿插。
第二幕情景是全然不同的。篇首,我们即读道:
“千万的人类自尊心在这里互相冲撞,或在死亡中灭寂……”
后面又说:
“……因为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亦是那么多……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即使在墓门前面!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代的文学之辈谈着爱、光荣与痛苦,而我们这世纪的文学只谈虚荣者和趋崇时尚之徒那无穷尽的故事呢?”
纪事不再是简单的叙述,而是直接使人类与情欲角逐,暴露英雄主义的背面。托尔斯泰犀利的目光在他同伴们的心底探索,在他们心中如在他自己心中一样,他看到骄傲、恐惧,死到临头尚在不断地演变的世间的喜剧。尤其是恐惧已被他确切认明了,被他揭除了面目,赤裸裸地揭露了。这无穷的危惧,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无顾忌、毫无怜惜地剖解了,他的真诚竟至如此可怕的地步。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一切的感伤情调全部丧失了,那是浮夸的、只知流泪的同情。他的分析天才,从没有比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达到更尖锐、更富幻想的强烈程度。在炸弹落下而尚未爆裂的一秒钟内,不幸者的灵魂所经过的情景,有整整两页的描写……另外一页是描写炸弹爆裂之后,“胸部受到轰击马上死了”,这一刹那的内心的思念。
名师指导
表达了托尔斯泰追寻真理、摒弃虚伪的高尚情操。
名师指导
直接抒发托尔斯泰的爱国情感和对违反神道战争的诅咒。
此时他忘记了他第一部叙述中的爱国情调,诅咒那违背神道的战争:
“而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在世上宣扬伟大的爱与牺牲律令的人,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事,在赐予每个人的心魂以畏死的本能与爱善爱美的情操的神前,竟不跪下忏悔!他们竟不流着欢乐与幸福的眼泪而互相拥抱,如同胞一般!”
在结束这一短篇时,其中的惨痛的语调,令他怀疑起来。“也许他不应该说话的?”“一种可怕的怀疑把我压抑着,也许不应当说这一切。我所说的,或即是恶毒的真理之一,无意识地潜伏在每个人的心魂中,而不应当明言以致它成为有害,如不当搅动酒糟以免弄坏了酒一样。哪里是应当避免去表白的罪恶?哪里是应当模仿的、美的表白?谁是恶人,谁是英雄?一切都是善的,一切亦都是恶的……”
但他高傲地镇定了:“我这短篇小说中的英雄,为我整个心魂所爱的,为我努力表现他全部的美的,他不论在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永远是美的,这即是真理本身。”
有人写信给托尔斯泰说:“你在我们的艺术中所提出的真理对于我们完全是新的东西。我只怕一件事—我怕时间,人生的懦怯,围绕我们的一切昏聩痴聋会把你收拾了,如收拾我们中大半的人一样……换言之,我怕它们会消灭你的精力。”
名师指导
对比显示出托尔斯泰的不同寻常,因此时间带给他的是更多作品的问世。
可是不用怕这些。时间会消磨常人的精力,对于托尔斯泰,却更增加他的精力。但即在那时,严重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的失陷,使他在痛苦的虔敬的情操中悔恨他的过于严正的坦白。他在第三部中写道:
“这场戏赶紧落幕吧。明日,也许今天,这些人将快乐地去就义。在每个人的灵魂中,潜伏着高贵的火焰,有一天会使他成为一个英雄。”
这种顾虑固然没有丝毫减弱故事的写实色彩,但人物的选择已可相当地表现作者的同情了。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和它的悲壮的失陷,象征了两个动人的高傲的人物——他们心中充满了爱,高兴地笑着去打仗,突然莫名其妙地在死神前折丧了。弟兄俩同日——守城的最后一天——受创死了。小说以怒吼着爱国主义的呼声的句子结束了:
“军队离开了城市。每个士兵,望着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心中怀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悲苦,叹着气把拳头向敌人遥指着。”
从这地狱中出来——在这一年中他触到了情欲、虚荣与人类痛苦的底蕴——1855年11月,托尔斯泰周旋于圣彼得堡的文人中间,他对他们感到一种憎恶与轻蔑。他们的一切于他都显得是卑劣的、虚假的。从远处看,这些人似乎是在艺术光环中的人物——即便如屠格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林》题赠给他——近看却使他悲苦地失望了。有一幅肖像是他在这个团体中的留影——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在一任自然的人群中,他的禁欲的、严峻的神情,骨骼嶙峋的头,深凹的面颊,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显得非常触目。他穿着军服,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他不似参与这集团,更像是看守这些人物。甚至可以说他准备着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
名师指导
对比突出了托尔斯泰忧心于国家,正直且严肃的性格。
可是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的同道,他拥有双重的光荣——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屠格涅夫亲密地向他伸着手,他们固然具有同样清晰的目光,却不能和解。这是两个敌对的灵魂:一个是幽默的、颤动的、多情的、幻灭的、迷恋美的;另一个是暴躁的、骄傲的、为着道德思想而苦闷的、孕育着一个尚在隐蔽之中的神明的。
托尔斯泰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是他们自信为一种优秀阶级,自命为人类的首领。在对他们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个贵族、一个军官对于放浪的中产阶级与文人那般骄傲。他“本能地反对大家所承认的一切判断”,对于人群表示猜疑,对于人类理性含藏着幽密的轻蔑,这种性情使他到处发觉自己与他人的欺罔及欺骗。
“他永远不相信别人的真诚。一切道德的跃动于他都是虚伪的。他对一个为他觉得没有说出实话的人,惯用他非常尖锐的目光逼视着他……”屠格涅夫说,他从没有感受到比他这副尖锐的目光,加上两三个会令人暴跳起来的恶毒的词句更难堪的了。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第一次会见时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远离之后,他们都镇静下来努力要给对方一个公正的评价。但时间的推移使托尔斯泰和这个文学团体分隔得更远。他不能宽恕这些艺术家一方面过着堕落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宣扬什么道德。
名师指导
托尔斯泰的想法与这些文学团体的行动大相径庭,为下文的分离埋下伏笔。
“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恶的、没有品性的,比我在军队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还要低下得多。而他们竟对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样。他们使我厌恶。”
他和他们分离了,但他在若干时期内还保存着如他们一样的对于艺术的功利观念。他的骄傲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艺术这种酬报丰富的宗教,它能为你争得“女人、金钱、荣誉……”
为了要完全献身给它,他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
但像他那种性格的人是不能长久闭上眼睛的。他相信进步,但到外国(法国、瑞士、德国)旅行了一次后,这个信念亦为之动摇了。1857年4月6日,在巴黎看到的执行死刑的一幕,告诉他“对于进步的迷信亦是空虚的……”
“当我看到头从人身上分离滚到篮中去的时候,在我生命的权力上,我懂得现有的维持公共治安的理论,没有一条足以证明这种行为的合理。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据着若干理论,认为这是必需的,我总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可以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
1857年7月7日,他在卢塞恩看到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这使他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中写出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者的幻想和在善与恶的领域中唱着幻想的高调的人的轻蔑:“于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些幻想的认识却毁灭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而谁将和我确言何谓自由、何谓奴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哪里善与恶才不互存并立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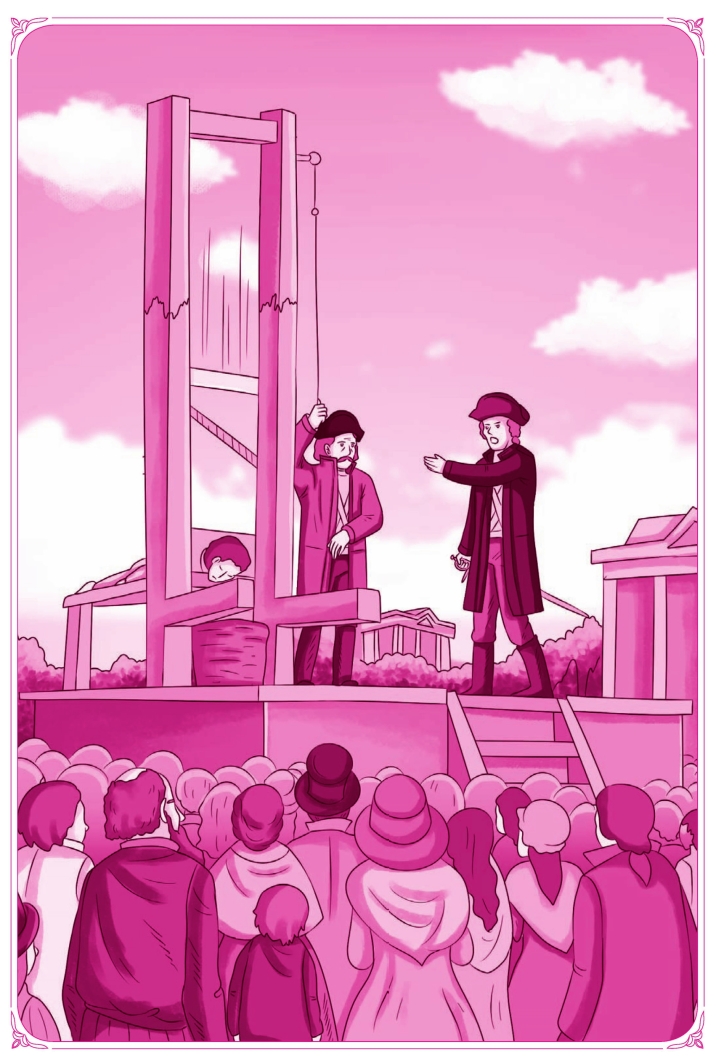
名师指导
自问自答显示出此时的托尔斯泰还是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于神灵。
回到俄罗斯后,他重新留意农人运动。他写道:“民众的宣道者徒然那么说,民众或许确是一般好人的集团;然而他们,只在庸俗、可鄙的方面,互相团结,只表示出人类天性中的弱点与残忍。”
因此他要启示的不是群众,而是每个人的个人意识,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意识。因为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学校,可不知道教授什么。为学习起见,他于1860年7月3日至1861年4月23日第二次旅行欧洲。他研究各种不同的教育理论,不用说,他把这些学说一齐摒弃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学校于他是显得可笑的——如报纸、博物院、图书馆、街道、生活,一切被他称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即是自然的学校,自由是他的原则。他不答应一般特殊阶级,“享有特权的自由社会”,把他的学问和错误,迫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众学习。这种强迫教育的方法,在大学里,从来不能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人,而产生了堕落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毫无目的地从旧环境中驱逐出来的人……少年时代已经骄傲惯了,此刻在社会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只能变成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应当由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不在乎“一般知识分子强令他们学习的读与写的艺术”,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有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试着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满足这些需求!
托尔斯泰试着在亚斯纳亚做一番实验,他在那里不像是他的学生们的老师,更似他们的同学。同时,他还努力将一种更为人道的精神引进农业经营中,并被任命为地方仲裁人,在田主与政府滥施威权之下成为民众保护人。
名师指导
表现了托尔斯泰对思想转变的渴求以及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经验的治学态度。
但我们不应当相信这些社会活动已使他满足并且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他仍然继续受着种种敌对的情欲支配。虽然他竭力接近民众,他仍爱,永远爱社交,他有这种需求。有时,享乐的欲望侵扰他;有时,一种好动的性情刺激他。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险去猎熊,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甚至他会受他瞧不起的圣彼得堡文坛的影响。从这些歧途中出来,他因为厌恶,陷于精神狂乱。这时期的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艺术上与精神上的犹疑不定的痕迹。《两个骠骑兵》倾向于典雅、夸大、浮华。1857年在法国第戎写的《阿尔贝特》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惯有的深刻与确切。《记数人日记》更动人、更早熟,似乎表现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憎恶。他的化身,涅赫留多夫亲王,在一个下流的地方自杀了:
“他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高超的感应;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为了什么剧烈的情欲,只是因为缺乏意志。”
死,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的心魂。在《三个死者》已可预见。在《伊万·伊里奇之死》一书中对于死的阴沉的分析,对于死者的孤独,对于生者的怨恨,他的绝望的问句:“为什么?”托尔斯泰自己亦不知道。
一年之后,1860年9月19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在耶尔患肺病死了,这噩耗使托尔斯泰大为震惊,以致“动摇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弃艺术:
“真理是残酷的……无疑,只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说出真理的欲望,人们便努力说出。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唯一的东西。这是我将实行的唯一的事物,可不是用艺术的形式。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
然而,不到六个月,他又在《波里库什卡》中重复“美丽的谎言”,这或许是除了他对于金钱和金钱的万恶能力的诅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纯粹为着艺术而写的作品,且亦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责备它的,只有它过于富丽的观察,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太丰盛的材料,和诙谐的开端与结尾的惨烈与之形成相对的有点残酷的对照。
名师指导
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对艺术已经没有了狂热的追逐,取而代之的是思想上的升华。
名师指导
通过两个人年龄的对比,衬托出了托尔斯泰对自己的不自信和对爱情的怀疑。
托尔斯泰在摸索,在怀疑自己,他似乎不耐烦起来,“没有强烈的情欲,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可是在这时期中产生了他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精纯的作品——《家庭幸福》,这是爱情的奇迹。
许多年来,他一直和别尔斯一家友善。他轮流地爱过她们母女四个,后来他终于确切地爱上了第二个女郎,但他不敢承认。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还是一个孩子——她只十七岁;他已经三十余岁——自以为是一个老人,已没有权利把他衰惫的、污损的生活和一个无邪少女的生活结合了。他隐忍了三年。以后,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讲述他怎样对她表露他的爱情和她怎样回答他的经过——两个人用一块铅粉,在一张桌子上描画他们所不敢说的言辞的第一个字母。如列文一般,他极端的坦白,使他把《日记》给他的未婚妻浏览,使她完全明了他过去的一切可羞的事,而索菲娅亦和基蒂一样,为之感到一种极端的痛苦。1862年9月23日,他们结婚了。
名师指导
形象生动地概括出婚姻在托尔斯泰的心中如诗一样的美好。
但早在三年前,在写《家庭幸福》时,这婚姻在诗人思想上已经完成了。他在生活中早已体验到:爱情尚在不知不觉间的那些不可磨灭的日子,爱情已经发酵了的那些醉人的日子,期待中的神圣幽密的情语吐露的日子,为了“一去不回的幸福”而流泪的日子,还有新婚时的得意,爱情的自私,“无尽的、无故的欢乐”;接着是厌倦,模模糊糊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着的灵魂慢慢地分解了、远离了,更有对于少妇含有危险性的世俗的迷醉——如卖弄风情、忌妒,无可挽救的误会——于是爱情掩幕了,丧失了;终于,心的秋天来了,凄凉的景况,重现的爱情的面目变得苍白无色,衰老了,因为流泪、皱痕,各种经历的回忆;互相损伤的追悔。虚度的岁月则更凄恻动人——以后便是晚间的宁静与清明,从爱情转到友谊,从热情的传奇生活转到慈祥的母爱的这个庄严的阶段……应当降临的一切,托尔斯泰都已预先梦想到、体味到了。
小说的故事在一个妇人心中展演,而且由她口述。何等的微妙!笼罩着贞洁之网的心灵的美……这一次,托尔斯泰的分析放弃了他微嫌强烈的光彩,它不再热烈地固执着要暴露真理。内心生活的秘密不是倾吐出来却是可令人窥测得到的。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形式与思想获得和谐的均衡:《家庭幸福》是一部具有拉辛式作品的完美。
托尔斯泰已深切地预感到婚姻的甜蜜与骚乱,这的确是他的救星。他疲乏了,厌弃了自己的努力。在最初的诸作获得盛大的成功之后,继而得来的是批评界的沉默与群众的淡漠。高傲的他表示颇为得意:“我的声名丧失了不少的普遍性,这普遍性原使我不快。现在,我放心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我有大声地说的力量。至于群众,随便他们怎样想罢!”
但这只是他的自豪而已——他自己也不能把握他的艺术。无疑的,他能主宰他的文学工具,但他不知用以做什么。像他在谈及《波里库什卡》时所说的:“这是一个会执笔的人抓着一个题目随便饶舌。”他的社会事业流产了。1862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职务。同年,警务当局把学校封闭了。那时托尔斯泰正好不在家,因为疲劳过度,他担心得肺病。
“仲裁事件的纠纷让我是那么难堪,学校的工作又是那么空泛,为了教育他人而要把我应该教授却为我所不懂得的愚昧掩藏起来,这一切所引起的怀疑,于我是那么痛苦,以致我病倒了。如果我不知道还有人生的另一方面可以使我得救的话——这人生的另一方面便是家庭生活,也许我早已陷于十五年后所陷入的绝望了。”
阅读鉴赏
文中多处运用语言描写、场面描写等手法,以及比喻、衬托等修辞方法,使托尔斯泰在艺术的道路上积累经验、寻求真理的形象跃然纸上,让读者见证了他的每一次蜕变与成长。
知识拓展
-”心灵辩证法”-
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价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技巧时提出的。托尔斯泰的人物心理描写是非常著名的,他善于深入人物的内心,抓住思想感情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一丝一毫地追索出人物思想感情巨大变化或剧烈转变的全过程,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刻画微观世界,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互相和谐的联系之中,充分展示人物从一种思想感情向另一种常常是相反的思想感情转变的“心灵辩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