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1887—1962),在北大时,黻用绂,原名毓玺,一名玉甫,字谨庵,别号千华山民,斋名静晤室,辽宁辽阳城北后八家子村人。他于1913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16年夏毕业。他入学时,陈汉章先生刚毕业留校任教。那时史学门未招生,汉章先生在预科、哲学门、国文门任教。在国文门教的是文字音韵、《尔雅》、《说文》、中国通史上古史。金毓黻自然成了他的学生。金对音韵极感兴趣,也颇有研究,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向汉章先生所提的九个问题(包括又问),其中七个有问有答,两个有问不见答。鉴于资料珍贵,也是首次露面,不妨照录如下:
音韵学疑问学生金毓黻
1.《广韵》于四声中分别轻清、重浊,可以正周氏上去声之阴阳之失,就先生轻清、重浊法,即阴、阳二象法之言推之,即上去声之轻清者为阳,上去声之重浊者为阴也。再推言之,上平、下平皆互转轻清、重浊之分,亦即皆有阴阳之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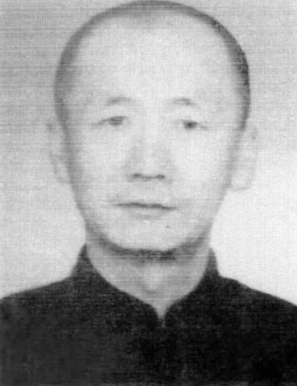
金毓黻
然周德清氏谓阴属下平声,阳属上平声,似尚未辨及上下乎声各有轻清、重浊之分,而先生独取是说,以证上去声合阴、阳者,其故岂别有在乎?孙氏《假借考》末段,《说文》,自为“经义概从”其正之语,王菉友以“思初始”等语驳之,恐非孙君之意。孙氏所谓“经义概从”其正者,指下文酉增诸字而言,非指所以祭也,益也、诸字两言也。王氏所引“惟初太始”一条,皆所以祭也、益也之类,而非酉增之类,不然一字下说解言多假借及无假借,不可以成文之理,孙氏岂不知之?必待王氏之辨而始明哉。《说文》中近于酉增之类者,皆用正字,独此数处同假借言,故孙氏举之耳。是否当?尚望先生以指正学生金毓黻谨问
2.先生就沙门斗神珙五音图,徐景安乐□谱,证明五音四声并非法歧而傅会,然《梦溪笔谈》谓切韵家以唇齿喉舌为宫、商、角、徵、羽,是三十六字母分配音也。今按江氏《四声切韵表》,每字母中皆有上下去入之分,四声是纵说,五言是横说,何以先生谓四声并非法歧而附会,其说必别有在,请指示之(此问如能另详讲义中,则此刻不必示及)。
3.金毓黻君问:《说文》 声,读若耿,古音读占如玷,在端母,耿在见母。而段氏谓占耿双声,其说是否?
声,读若耿,古音读占如玷,在端母,耿在见母。而段氏谓占耿双声,其说是否?
又问:蛭至声,与至音近。《尔雅·释虫》:“蛭蝚,至掌。”主掌双声字,即蛭字之转音,其说是否?
答:此说于郝氏《义疏》外,可自立一帜。再能解通蝚虮二字,更佳。
4.君问:郑樵《六书略》,谓会意字有二母三体,母与体有何分别?
答:夹漈《说文》有子母,一子一母为谐声,二母合为会意。谐声一体义,一体声;会意二体俱义;二母有三体之合者,非常道也。故另为二母之合,三体之合,其论子母也。谓《说文》眼学,以母统子;《广韵》耳学,以子该母。五百四十类,为字之母,其论子母所自也。谓乌与鸟同体,乌同而鸟独,鸟为母而乌为子;易与豸同体,豸同而易独,豸为母而易为子。然则夹漈所谓体者,字之形体为统词,所谓母者,字之部首,为专词。
答:学术无穷,圣教无隐;详说始能反约,温故可以知新。拙撰讲义,意在博取前辈诸说,俟善学者择善而从。谓莽字为会意正例者,黄元同先生;谓莽字为会意变例者,王菉友先生。异人之说,自不能合同,讲义以两说皆通,故未加驳正。初非前后不照,似不足相难。
又问:吏字不可言从史一,以《易象》泽上于天《夬》喻之,是言外可言从一史矣。此言与合两字为意并峙言之之例相背否?
答:王菉友以《易象》上天下泽《履》,拟并峙之会意,故演绎其意,谓《履》卦不可倒作《夬》,以正吏之从史从一,不可倒作从一史,谓此喻言外意与并峙之意背,似属误会。还请好学深思者,心知其意。
6.金毓黻又问:先生前言之类隔双声,是否与章太炎喉牙足以衍百音一语同意?如与章先生语同意,则类隔双声,以喉牙为主,而与齿舌唇诸音相衍矣。否则不以喉牙为主,而诸音皆可相衍,是否?请指示。
答:类隔音和始见《广韵》切音法,古音本无所谓类隔,后人以音纽不同,别为之名耳。《音韵学讲义》,已详言之矣。
7.又问:《尔雅》螾 入耳,(螾
入耳,(螾 皆喻母。入耳今音皆日母,古音皆泥母,从章氏说。)入耳为类隔双声字,以喻母喉音字,可与泥母舌音字相衍也。(《说文》能从
皆喻母。入耳今音皆日母,古音皆泥母,从章氏说。)入耳为类隔双声字,以喻母喉音字,可与泥母舌音字相衍也。(《说文》能从 声,
声, 喻母字,能泥母字,古音相谐,正与此同。)由是可证蛭蝚与至掌。(至由蛭生,掌与蛭为双声。)亦为双声。(蝚在今日母,古泥母。钱辛楣谓古时齿舌。有时旁转,故蛭蝚亦双声字。章太炎谓古舌头正齿,大较不别。)而至掌二字,亦不至难解矣。此说是否?
喻母字,能泥母字,古音相谐,正与此同。)由是可证蛭蝚与至掌。(至由蛭生,掌与蛭为双声。)亦为双声。(蝚在今日母,古泥母。钱辛楣谓古时齿舌。有时旁转,故蛭蝚亦双声字。章太炎谓古舌头正齿,大较不别。)而至掌二字,亦不至难解矣。此说是否?
答:以蛭蝚二字为双声,与至掌二字例同,亦可。但说双声不必拘泥字母,字母后起者也。(《陈汉章全集》第十八册上,第90—92页)
以上一、二题未见答疑,可能写在《音韵学讲义》中,其余几个问题先生均保留金毓黻所写的提问字条。
金毓黻学术观念前后不一,早些时候他反对博而不精。如他在《静晤室日记》中写道:“往世人多务博知,语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不知古籍充栋有江海,一人之腹岂能尽受?况自海通以后,西籍东来,学术复日新而月异,分门专攻且不能精,并骛兼营大圣犹病,故用心如何之嫥,而力终有不逮也。尝谓学问之道,只宜求精,不宜贪多,究一名物,研一理道,务必穷原意委,以求真知。其与于此事者,虽一无所知,无害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即千古为学之准。积知日久,自能贯穿百家,博虽未可骤语,通则庶几近之。故学者只宜求精、求通,不可求博,博则贪多而不能精,学不精则终无通之一日,不可不戒。”(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985—986页)但后来,金毓黻学术观念开始转变,从原来的主张求精,反对务博,转而提出:“博而不能精,则不免博而寡要之讥。然未有不博而能精者,博而能精,则专门名家矣。”(《静晤室日记》第4779页)金毓黻这一学术观念转变,体现在对汉章先生的评判上最为明显。他在日记中说:
曩岁陈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通史,繁称博引,累数百翻而不能终其物。叙上古史喜用《路史》《绎史》,多为荒邈无稽之说,而先生不加简载,遂为执业诸子所不满。然蕲春黄先生尝谓陈先生读书之多,称引之富,一时无两,难能可贵,自刘申叔以外为推重之一人,诚为服善之笃,亦见持论之公矣。今细译先生此作,则于探赜索引之中,时著平实可信之语,博综约取,允为传作,以视曩日判若天渊,岂非以年念高而学愈进,学愈进而心愈下欤?”(《静晤室日记》第4046页)
金氏对汉章先生著作前后评介判若两人,从以前认为汉章先生著作“不满”,而后却“以视曩日判若天渊”,这时他才认识到做学问要由博反约,博而后才能精。故他后读汉章先生历史就与先前完全不一样了。可有趣的是,汉章先生在答金毓黻音韵问答时,他就提出:“详说始能反约,温故可以知前辈诸说,俟善学者择善而从。”
金毓黻后来不是成为语言学家,而是对史学发生兴趣,并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九一八”事变,金遭拘禁,解禁令后,借故去日本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查阅资料之名,于7月从日本逃至南京,入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此时中央大学校长为罗家伦,史学系主任为朱希祖。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国文门当过系主任,教中国文学史(二年),金听过他的课,两人也是师生关系。金于1938年春担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金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教中国史学史,写了一本《中国史学史》,于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该书在当时影响极大,是教育部部定大学用书。除此他还有《东北史志》、《东北通史》、《奉天通志》、《宋辽金史》,以及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太平天国史料》等。现有《金毓黻文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