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 吴月娘壬子日求子 潘金莲花园夜偷婿
金莲听月娘说要去同瓶儿对证,慌得连连说道:“姐姐宽恕她吧。常言大人不责小人过,哪个小人没罪过?她在屋里背地调唆汉子,俺们这几个谁不吃她说。我和她紧隔着壁儿,如果和她一般见识起来,倒了不成。动不动只倚逞着孩子降人。她还有好话说哩,说她的孩子到明日长大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俺们都是饿死的数儿。你还不知道哩!”
吴大妗子说道:“我的奶奶,哪里有此话说。”
月娘一声儿也没言语。
不料,西门大姐在一旁听了,心中不平。大姐平日与瓶儿最好。大姐常没针线鞋面,瓶儿不论好绫罗缎帛就给她,好汗巾手帕两三方地也给她,银钱就不消说了。听了金莲的话,大姐便向瓶儿屋里走来。瓶儿正在为孩子做那端午戴的绒线符牌儿、各色纱小粽子儿、解毒艾虎儿,见大姐走来,连忙让坐,教迎春拿茶。
吃过茶,大姐说道:“有桩事儿,我也不是舌头,敢来告你说一说。你说过俺娘虔婆势?你这几日恼着五娘不曾?她在后边对着俺娘说了你一篇是非。”于是把金莲的原话照学了一遍。接着说:“如今俺娘要和你对话哩。你别说这是我对你说的,免得她怪我。你须预备些话儿打发她。”
瓶儿听罢此言,手中那针儿通拿不起来,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说不出话,只对着大姐掉眼泪。好一会,说道:“大姑娘,我哪里有一字儿闲话?昨晚我在后边,听见小厮说他爹往我这边来了,我就来到前边,催他往后边去了,我还说什么话儿来?你娘这样看顾我一场,莫不我这样不识好歹,敢说这个话?假如我就是说了,对着谁说的?也有个下落!”
大姐说道:“她听见俺娘说要来对证,如何就慌了?要是我,你两个当面锣、对面鼓地对个清楚。”
瓶儿说道:“我对得过她那嘴头子?自凭天罢了。她左右昼夜计着我。只是俺娘儿两个,到明日吃她算计了一个去,也就顺她的心了。”说毕,哭出声来。
大姐劝了一回。小玉来请六娘、大姑娘吃饭,二人就往后边去了。
瓶儿也不曾吃两口饭,回来房中,倒在床上睡着。西门庆从衙门中回来,见她睡了,问迎春怎回事。
迎春说道:“俺娘一日饭也没吃下哩。”
西门庆慌了,向前问瓶儿:“你怎的了?对我说。”见她哭得眼红红的,又问道:“你心里怎么的?对我说。”
瓶儿连忙起来,揉了揉眼,说道:“我只是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里不想吃饭。”金莲的事一字不提。
大姐在后边对月娘说:“我问了六娘,她说没有此话。只望着我哭,说娘这般看顾她,她肯说此话?”
吴大妗子也说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个人儿,她会说出此种谎来?”
月娘说道:“我也是这样想。想必两个人不知怎的有些小节不足,哄不动汉子,走来后边戳无路儿,拿我垫舌根。”
大妗子说道:“大姑娘,今后你也别要亏了人。不是我背地说,潘五姐一百个不及她为人,心地儿又好,来了咱家这二三年,你我找得出她一些歪样儿来?”
正说着,琴童儿背着蓝布大包袱进来。月娘一问,才知是韩伙计他们从关上挂了三万盐引的号来。吴大妗子听说西门庆回来了,想起身带着薛姑子和王姑子往李娇儿房里回避,不想西门庆已掀帘子进来。
西门庆见了薛姑子,便问月娘:“那个薛姑子贼胖秃淫妇。来我这里做什么?”
月娘不高兴了:“你好好地这般枉口拔舌,骂她怎的,她惹你了?你怎知道她姓薛?”
西门庆说道:“你不知她弄的乾坤事儿?她把人家陈参政家小姐,七月十五藏在地藏庵里,和一个小伙叫阮三的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她知情,受了三两银子。出事了,拿到衙门里,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她嫁汉子还俗。她怎的还不还俗?好不好,拿到衙门里,再与她几拶子。”
月娘说道:“瞧你说的,这样毁神谤佛。她一个佛家弟子,想必善根还在,平白还什么俗?你还不知她,好不有道行。”
西门庆说:“我不知她有道行?你问她有道行一夜接几个汉子?”
月娘见他越说越邪了,赶紧用话叉开,支了他出去。
晚夕,金莲在后面与众人喝酒,听见琴童说“爹不往后边来了,往五娘房里去了”,就坐不住,趔趄着脚儿就要走,又不好意思。
月娘看着她,见她不安的样子,说道:“他往你屋里去了,你去吧,省得你牵肠挂肚。”
金莲站起身,低着头,口里叽叽咕咕的,好像是在责怪西门庆,脚步儿却是越走越快。
西门庆已是吃了胡僧的药,教春梅脱了衣裳,在床上帐子里坐着哩。金莲见他那个样儿,笑道:“我的儿,今日好呀,不等你娘来,就上床了。俺们刚才在后边陪大妗子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几盅好的。独自一个儿,黑影子里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就走的来了。”又叫春梅:“你有茶,倒瓯子我吃。”
吃了茶,金莲撇了个嘴与春梅,那时春梅就知其意,那边屋里早已替她热下水。金莲在热水里抖了些檀香白矾在里面,洗了牝,摘了头饰,又重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回到这边屋来。春梅床头上取过睡鞋来,与她换了,带上房门出去。金莲将灯台挪近床边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边纱帐子来。褪去红裤,露出玉体。西门庆坐在枕头上,那话带着两个托子,一霎弄得大大的,露出来与她瞧。金莲灯下看见,唬了一跳,一手揝不过来,紫巍巍,沉甸甸,约有虎二。
金莲眤瞅了西门庆一眼,说道:“我猜你定是吃了那和尚药,弄耸得恁般大,一味来奈何老娘。那和尚的药给了几天了,你又在谁人跟前试了新,今日剩些残军败将才来我这屋里?俺们是雌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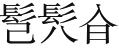 的,你还说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里,三不知你把那行货包子偷到她屋里去,原来和她干这营生,她还对着人撇清捣鬼哩!你这行货子,干净是个没挽回的三寸货。想起来,一百年不理你才好。”
的,你还说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里,三不知你把那行货包子偷到她屋里去,原来和她干这营生,她还对着人撇清捣鬼哩!你这行货子,干净是个没挽回的三寸货。想起来,一百年不理你才好。”
西门庆笑着,说道:“小淫妇儿,你过来。你若有本事把它咂过了,我输一两银子与你。”金莲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什么行货子,我禁得过它?”于是把身子斜 在衽席之上,双手执定那话,用朱唇吞裹,说道:“好大行货子!把人的口也撑得生疼的。”说毕,出入呜咂,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龟弦;或用口噙着,往来哺摔;或在粉脸上偎晃,百般抟弄。那话越发坚硬
在衽席之上,双手执定那话,用朱唇吞裹,说道:“好大行货子!把人的口也撑得生疼的。”说毕,出入呜咂,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龟弦;或用口噙着,往来哺摔;或在粉脸上偎晃,百般抟弄。那话越发坚硬 崛起来,裂瓜头凹眼圆睁,络腮胡挺身直竖。西门庆垂首窥见金莲香肌,掩映于纱帐之内,纤手捧定毛都鲁那话往口里吞放,一往一来动弹。不想旁边蹲着一只白狮子猫,看见动弹,不知是何物,扑向前来,伸爪便挝,被金莲夺过西门庆手中的扇子尽力打了一记,把那白狮子猫打出帐子外去了。金莲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儿替你咂来?我这屋里,尽着教你掇弄!不知吃了什么行货子,咂了这一日,一发咂了没事。”西门庆于是向汗巾儿上小银盒里,用挑牙挑了些粉红膏子药儿,抹在马口内,仰卧于上,教金莲骑在身上,金莲道:“等我
崛起来,裂瓜头凹眼圆睁,络腮胡挺身直竖。西门庆垂首窥见金莲香肌,掩映于纱帐之内,纤手捧定毛都鲁那话往口里吞放,一往一来动弹。不想旁边蹲着一只白狮子猫,看见动弹,不知是何物,扑向前来,伸爪便挝,被金莲夺过西门庆手中的扇子尽力打了一记,把那白狮子猫打出帐子外去了。金莲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儿替你咂来?我这屋里,尽着教你掇弄!不知吃了什么行货子,咂了这一日,一发咂了没事。”西门庆于是向汗巾儿上小银盒里,用挑牙挑了些粉红膏子药儿,抹在马口内,仰卧于上,教金莲骑在身上,金莲道:“等我 着,你往里放。”龟头昂大,濡研半晌,仅没龟稜。金莲在上,将身左右捱擦,似有不胜隐忍之态,因叫道:“亲达达,里边紧涩住了,好不难捱。”一面用手摸之,灯下窥见尘柄已被牝户吞进半截,撑得两边皆满,无复作往来。金莲用唾津涂抹牝户两边,已而稍宽滑落,颇作往来,一举一坐,渐没至根。金莲因向西门庆说:“今日这命死在你手里了,好难捱忍也!”两个足缠了一个更次,西门庆觉牝中一股热气,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暗想胡僧之药通神。看看窗外,东方渐白,鸡鸣不已。金莲道:“我的心肝,你不过怎样的?到晚夕,你再来,等我好歹替你咂过了罢。”西门庆道:“就咂也不得过,管情只一桩事儿就过了。”金莲道:“哪一桩事?”西门庆道:“法不传六耳,待我晚夕来对你说。”
着,你往里放。”龟头昂大,濡研半晌,仅没龟稜。金莲在上,将身左右捱擦,似有不胜隐忍之态,因叫道:“亲达达,里边紧涩住了,好不难捱。”一面用手摸之,灯下窥见尘柄已被牝户吞进半截,撑得两边皆满,无复作往来。金莲用唾津涂抹牝户两边,已而稍宽滑落,颇作往来,一举一坐,渐没至根。金莲因向西门庆说:“今日这命死在你手里了,好难捱忍也!”两个足缠了一个更次,西门庆觉牝中一股热气,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暗想胡僧之药通神。看看窗外,东方渐白,鸡鸣不已。金莲道:“我的心肝,你不过怎样的?到晚夕,你再来,等我好歹替你咂过了罢。”西门庆道:“就咂也不得过,管情只一桩事儿就过了。”金莲道:“哪一桩事?”西门庆道:“法不传六耳,待我晚夕来对你说。”
次日一早,西门庆去衙门去了,潘金莲直睡到晌午才扒起来。她又怕后边有人说她,连月娘请她吃饭也推辞不去。到大后晌,才出了房门,来到后边。此时,月娘趁西门庆不在家,安排下桌儿,和众人围着两个姑子和她们的两个徒弟,听演金刚科。
金莲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便想溜出去,先拉玉楼,不动;又扯瓶儿,被月娘看见了。
月娘对瓶儿说:“李大姐,她叫你,你和她去吧,省得急得她在这里百般不定的。”
瓶儿起身同金莲出来。
月娘瞅了一眼,说道:“拔了萝卜地皮宽。让她去了,省得她在这里跑兔子一般。她,原不是听佛法的人!”
金莲拉着瓶儿走出仪门,说道:“大姐姐专好干些这般营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让姑子来家中宣讲经卷。都在那里围着怎的?咱们出来走走,去看看大姐在屋里做什么哩。”
于是一直走出大厅,见厢房内点着灯,大姐和经济正在里面说话,说是不见银子了。金莲上前向窗棂上打了一下,说道:“不去后面听佛曲儿,两口子在房里拌的什么嘴儿?”
陈经济出来,见是二人,说道:“差点我要骂出来,原来是五娘、六娘来了,请进来坐。”
金莲一边进来一边说道:“你好大胆子,骂不是。”进来见大姐正在灯下纳鞋,说道:“这么晚,热剌剌地还纳鞋?”又问:“你两口子嚷些什么?”
陈经济说道:“你问她。爹使我们外讨银子去,她与了我三钱银子,要我替她捎销金汗巾子来。不想到了那里,袖子里摸,银子没了,汗巾子不曾捎得来。来家她就说我在外养老婆,和我嚷,骂我这一日,急得我赌身发咒。不想丫头扫地,地下拾起来。她把我银子收了不与我,还要我明日买汗巾子来。你二位老人家说,却是谁的不是?”
大姐骂道:“贼囚根子,别耍贫嘴。”
金莲问道:“有了银子不?”
大姐说道:“有了银子。刚才丫头地下扫发拾起来,我拿着哩。”
金莲说道:“那就不打紧了。我与你银子,明日也替我带两方销金汗巾子来。”
瓶儿问道:“姐夫,门外有买销金汗巾儿?也捎几方儿与我吧。”
经济答道:“门外手帕巷,有名王家,专一发卖各色改样销金点翠手帕汗巾儿,随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什么颜色,销什么花样儿,早说与我听,明日一齐都替你带来了。”
瓶儿说:“我要一方老金黄销金点翠穿花凤汗巾。”
经济忙说道:“六娘,老金黄销上金不显。”
瓶儿说道:“你别要管我。我还要一方银红绫销江牙海水嵌八宝汗巾儿,又是一方闪色芝麻花销金汗巾儿。”
经济问金莲:“五娘,你老人家要什么花样?”
金莲说:“我没银子,只要两方儿够了。要一方玉色绫琐子地儿销金汗巾儿。”
经济说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剌剌的要它做什么?”
金莲说道:“你管它怎的?戴不得,等我往后吃孝戴。”
经济问道:“那一方要什么颜色?”
“那一方,我要娇滴滴紫葡萄颜色四川绫汗巾儿,上销金,间点翠,十样锦,同心结,方胜地儿,一个方胜儿里面一对儿喜相逢,两边栏子儿都是缨络珍珠碎八宝儿。”金莲一连串报了出来。
经济听罢,说道:“耶 耶
耶 ,再没了?卖瓜子儿开箱子打
,再没了?卖瓜子儿开箱子打 喷,琐碎一大堆。”
喷,琐碎一大堆。”
金莲不高兴:“怪短命的,有钱买了称心货,随各人心里所好,你管它怎的!”
瓶儿从荷包里拿出一块银子儿递与经济:“连你五娘的都在里头哩。”
金莲不肯,摇着头儿说:“等我与他吧。”
瓶儿还是把银子递与了经济。
经济说道:“就是连五娘的,这银子还多着哩。”顺手取戥子称了,有一两九钱。
瓶儿说:“剩下的,就与大姑娘捎两方来。”
大姐听了,连忙道了万福。
金莲说道:“你六娘替大姐买了汗巾儿,把那三钱银子拿出来,你两口儿斗牌儿,赌了东道儿吧。若少,便叫你六娘贴些儿出来。明日等你爹不在了,买烧鸭子白酒咱们吃。”
经济对大姐说:“既是五娘这样说,拿出来吧。”
大姐拿了出来银子,递与金莲,金莲交付瓶儿收着。经济拿出纸牌,在灯下与大姐斗。金莲在一旁指点大姐,登时赢了经济。这时,前边有打门声,是西门庆来家,金莲与瓶儿出了厢房,各自回自己的房里去了。
西门庆在夏提刑家吃酒,又是宋巡按送了礼给他,心中高兴,夏提刑也更敬重他,多喝了几杯,人带半酣,进了金莲房。金莲又早向灯下除去冠儿,露着粉面油头,教春梅设放衾枕,搽抹凉席,薰香澡牝,专候西门庆。进门接着,见他酒带半酣,连忙替他脱了衣裳,教春梅点茶来与他吃了,打发上床歇息。西门庆见金莲脱得光赤条身子,坐在床沿上低垂着头,将那白生生的腿儿横抱膝上缠脚,换了一双刚三寸、恰半叉大红平底睡鞋儿,不觉淫心辄起,尘柄挺然而兴,便问金莲要淫器包儿。金莲忙向褥子底下摸出来递与他。西门庆把两个托子都带上,一手搂过潘金莲在怀里,笑着说道:“你达达今日要和你干个后庭花儿,你肯不肯。”
金莲瞅了他一眼,说道:“好个没廉耻的冤家!你成日和那书童儿小厮干得不值了,又缠起我来了,你去和那奴才干去不是!”
西门庆笑道:“怪小油嘴儿,罢么!你若依了我,又去稀罕小厮做什么,你不知你达心里好的就是这桩儿。管情放到里头去,我就过了。”
金莲被他再三缠不过,说道:“奴只怕挨不得你这大行货,你把头上圈去了一个,我和你耍一遭试试。”
西门庆真个除去硫黄圈,根下只束着银托子,令金莲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一边行事,一边说道:“好心肝,你叫着达达,到明日买一套好颜色妆花纱衣服与你穿。”
金莲正蹙眉隐忍,口中咬汗巾子捱着,听西门庆这样一说,便道:“那衣服我也有。我昨日见李桂姐来家穿的那玉色线掐羊皮金挑的油鹅黄银条纱裙子倒是好看,说是里边买的。她们都有,只我没这条裙子。倒不知多少银子,你倒买一条我穿罢了。”
西门庆正是快畅之时,说道:“不打紧,明日我替你买。”
次日,待西门庆去衙门了,王姑子、薛姑子告辞回庵去。月娘自是送礼施银,管待出门。薛姑子又嘱咐月娘别忘了壬子日吃药行房的事。
月娘回到后边,和众人在后边上房明间内吃了饭,在穿廊下坐着,忽见剃头的小周儿在影壁前探头探脑。
瓶儿连忙叫道:“小周儿,你来正好,进来与小大官儿剃剃头,头发都长长了。”
小周儿连忙向前都磕了头,说:“刚才小的给老爹篦头,老爹吩咐小的进来与哥儿剃头。”
众人才知西门庆已回来了。月娘道:“六姐,你拿历头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与孩子剃头?”
金莲要小玉去取了历头来,揭开看了一回,说道:“今日是四月二十一日,是个庚戌日,合是娄金狗当直,宜祭祀、官带、出行、裁衣、沐浴、剃头、修造、动土,宜用午时。好日期。”
月娘对瓶儿说道:“既然是好日子,教丫头热水,你替孩儿洗头,让小周儿慢慢哄着他剃。”
安排妥贴,才剃得几刀儿,这官哥儿“呱”的一声怪哭起来。那小周儿连忙赶着他哭只顾剃,没想把孩子哭得一口气憋下去,不出声,脸胀得通红。瓶儿见了,唬慌手脚,连忙说:“不剃吧,不剃吧!”那小周儿停下手来看看孩儿,唬得收不及家活,拔脚往外跑。
月娘说道:“我说这孩子有些不长俊,自家替他剪剪不就罢了。”
官哥憋了半日气,突然放出声来,“哇”的一声。瓶儿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只顾抱在怀里拍哄着他:“她小周儿,恁大胆,平白进来把哥哥头来剃去了,还不拿回来,等我打小周儿,与哥哥出气。”
月娘说道:“不长俊的小花子儿,剃头耍了你,失便益了,这等哭!剩下这些头发到明日做剪毛贼。”
引逗了一回,李瓶儿把孩子交给如意儿。月娘吩咐且休与他奶吃,让他睡一回儿与他吃。
奶子把官哥儿抱走了,来安儿进来取小周儿的家活,说小周儿唬得脸焦黄的,不敢进来取家活。
月娘问道:“他吃了饭不曾?”
来安答道:“饭吃了。爹赏了他五钱银子。”
月娘要来安拿一瓯子酒出去与他:“别唬着人家,好容易讨这几个钱。”
小玉连忙筛了一盏酒,拿了一碟腊肉,交来安拿出去与小周儿吃。
吴月娘对金莲说:“你再看看,几时是壬子日?”
金莲看了说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种五月节。”又问:“姐姐,你问壬子日怎的?”
“不怎的,问一声儿。”月娘淡淡地说了一句。
次日,西门庆早起,也没往衙门中去,吃了粥,冠带着,骑马拿着金扇,出城南三十里,往砖厂刘太监庄上赴席,书童与玳安两个都跟去了。
潘金莲等西门庆走了,与李瓶儿计较,将陈经济输的那三钱银子,再教瓶儿添七钱,交付来兴儿买了一只烧鸭、两只鸡、一钱银子的小菜、一坛金华酒、一瓶白酒、一钱银子裹馅凉糕,交来兴儿媳妇整理端正,请了月娘同玉楼、娇儿、雪娥、大姐,先在卷棚内吃了一回,又拿了酒菜儿,往最高的卧云亭上,下棋投壶喝酒。
月娘吃着,猛然想起,问道:“今日何不请陈姐夫来坐坐。”
大姐说道:“爹又使他今日往门外徐家催银子去了,也该回来了。”
不一会,陈经济交付银子清楚,来到花园,先向月娘众人作了揖,拉过大姐,一处坐下。于是传杯换盏,酒过数巡,各添春色。月娘与娇儿她们下棋,玉楼、瓶儿、雪娥、大姐同经济便向各处游玩观花草。只有金莲,在山子后那芭蕉丛深处,将手中白纱团扇儿扑蝴蝶为戏。
不妨经济蓦地走到背后,猛然叫道:“五娘,你不会扑蝴蝶,等我与你扑!这蝴蝶,就和你老人家一般,有些毬子心肠,滚上滚下的。”
金莲扭回粉颈,斜睨秋波,对着陈经济笑骂道:“你这少死的贼短命,谁要你扑!有人来听见找死。我晓得你也不怕死了,捣了几盅酒儿,在这里来鬼混。”又问他:“你买的汗巾儿哩?”
经济笑嘻嘻地向袖子中取出,递与她,说道:“六娘的都在这里了。汗巾儿捎了来,你拿什么来谢我?”说着,把脸向她挨过去。
金莲把经济一推,还未说话,就见瓶儿抱着官哥儿,奶子如意儿跟着,从松墙那边走来。见金莲和陈经济两个在这里嬉戏扑蝶,又见经济往山子洞那儿钻去,便叫道:“你两个扑个蝴蝶儿与官哥儿耍子。”
潘金莲心中着慌,恐怕瓶儿瞧见了什么,故意问道:“陈姐夫与了汗巾子不曾?”
瓶儿答道:“还没哩。”
金莲说道:“他刚才袖着,对着大姐姐不好与咱,悄悄递与我了。”
于是,两人坐在花台石上,打开汗巾包儿,分了。
瓶儿看看自己坐在芭蕉丛下,便说道:“这答儿里倒且是荫凉,咱在这里坐一回儿吧。”于是使如意儿叫迎春到屋里取孩子的小枕头儿带凉席儿,放到这里,让孩子睡会。再悄悄儿取骨牌来,要和金莲抹回牌儿。
金莲见官哥儿脖子里围着条白挑线汗巾子,手里拿着个李子往口里吮,问瓶儿:“这是你的汗巾子?”
瓶儿摇摇头说道:“是刚才他大妈妈见他口里吮着李子,流下水,替他围上这汗巾子。”
不一会,迎春取了枕席和骨牌来。瓶儿铺下席,把官哥儿放在小枕头儿上躺着,让他自在玩耍,自己便和金莲抹牌。抹了一回,又教迎春往屋里炖一壶好茶来。
迎春刚走,孟玉楼在卧云亭栏杆上看见瓶儿,招手儿叫道:“大姐姐叫你说句话儿,快来。”
瓶儿只得撇下孩子,交与金莲看着,说了声“我就来”,走了。
金莲心中记挂着经济,哪有心看顾孩子,赶空儿三步并做两步走到山子洞门首,压低声音叫道:“没人,你出来吧。”
经济出来了,又把金莲拉了进去:“里面长出大头蘑菇了。”
金莲进了洞,哪有蘑菇,只见经济折腿跪在面前,要和自己云雨求欢。金莲没言语,经济站起身来,两人搂抱着亲嘴。
瓶儿走到亭子上,月娘说:“孟三姐投壶输了,你来替她投两壶儿。”
瓶儿说道:“底下没人看孩子哩。”
玉楼说:“不是有六姐在么,怕怎的?”
月娘说道:“孟三姐,你去替她看看吧。”
瓶儿加了一句:“三娘,累你,一发抱了他来这儿。”
月娘便教小玉跟去抱孩儿。
小玉跟着玉楼走到芭蕉丛下,哪有金莲的影儿,只剩孩子一个人躺在席上,蹬手蹬脚地怪哭,旁边一只大黑猫见有人来,一滚烟跑了。
那潘金莲与陈经济正搂着亲嘴,就要交欢行乐,听见外面玉楼的叫声,赶紧松开。金莲从洞儿里钻出来,说道:“我在这里净了净手,谁往哪里去了?哪里有猫来唬了他,白眉赤眼儿的!”
玉楼哪有心思再去看洞里,只顾抱了官哥儿,拍哄着往卧云亭上去。小玉拿着枕席,跟在后面。金莲怕玉楼说什么,也跟上来。
月娘问:“孩子怎么又哭了?”
玉楼说道:“我去时,不知是哪里一个大黑猫,蹲在孩子头跟前。”
月娘说:“那不唬着孩子了?”
瓶儿说:“他五娘不是在看着他么?”
玉楼说道:“六姐往洞儿里净手去了。”
金莲走上来:“玉楼,你怎的这般白眉赤眼儿的?我哪里去讨个猫来?想必他是饿了,要奶吃,就哭起人了。”
瓶儿见迎春送上茶来,就使她叫奶子来喂哥儿奶。孩子不吃奶,只是哭,月娘吩咐瓶儿抱回去,好好打发他睡。
洞里的陈经济不曾与金莲得手,十分沮丧,蹲在洞里不敢乱动,听听没有了动静,才钻了出来,顺着松墙儿,转过卷棚,往外走去了。
月娘与众人在花园里又玩一会,身子有些疲倦,各自回房。月娘回房在床上靠着睡了约有更次,又差小玉去问瓶儿官哥现在如何。
瓶儿对小玉说:“你与我谢声大娘。哥哥自进了房,只顾呱呱地哭,打冷战不已;刚才住了,依在奶子身上睡下了,头上还有些热的。”
小玉回房,对月娘说了。
月娘道:“她们也太粗心了,哪里把一个小娃儿,丢放在芭蕉树下,自己走开?被猫唬了,如今才是愁神鬼哭的。定要把孩儿弄坏了,才住手。”
第二日早起,月娘心中牵挂官哥,先差小玉去前边问讯,自己随后就到。瓶儿昨夜没睡好觉,正躺在床上瞌睡,听说月娘就来,赶忙起来,要迎春拿洗脸水抹了把脸,急攘攘地梳了几下头,又教迎春烧茶点安息香。
月娘进来就到奶子床前,摸着官哥说:“不长俊的小油嘴,常常把做亲娘的平白地提在水缸里。”
官哥又是“呱”的一声怪哭起来,月娘连忙引逗了一番,就住了。
月娘对如意儿说道:“我又不得养,我家的人种便是这点点儿,要用心才好。”
如意儿忙说道:“这不消大娘吩咐。”
月娘就要出房,瓶儿说道:“大娘来了,泡好一瓯子茶,请坐坐再去。”
月娘坐下,见瓶儿乌云不整,问道:“六娘,你头鬓也是乱蓬蓬的?”
瓶儿说道:“都因这冤家作怪捣气,折腾一夜,头也不得梳。又是大娘来,匆匆忙忙地扭一挽儿,胡乱磕上 髻,不知什么模样。”
髻,不知什么模样。”
月娘笑了:“看你说的。自家养的亲骨肉,倒也叫他是冤家。像我,成日要个冤家也不能够哩!”
瓶儿说道:“是便是这等说,没有这些鬼病来缠扰他便好。如今不得三两日安静,常常闹病。人家的孩子都是好养,偏有这东西,剃个头哭得不成样儿,如今又被猫唬了,竟是灯草一样脆。”
说了一会,月娘走出房来,瓶儿随后送出。月娘说道:“你莫送了,进去看官哥吧。”瓶儿止步回房去了。
月娘走过来,只见照壁后有人说话,便立住听着,又在板缝里瞧觑,原来是金莲与玉楼两个靠着栏杆,絮絮答答地正说着哩。月娘仔细听着。
金莲正说道:“姐姐好没正经!自家又没得养,别人养的儿子,厚着脸作亲热,呵卵脬。我想穷有穷气,杰有杰气,奉承她做什么?孩儿长大了,只认自家娘,哪个认你?”
这时迎春走了过来,两个人赶紧走开了,金莲假装寻猫儿喂饭。
月娘听了这些话,怒生心上,恨落牙根,真想叫住金莲骂几句,但那只会反伤体面,只得忍耐,自己进房,睡在床上生闷气,不敢放声哭,自埋自怨,短叹长吁,正午的饭也不吃,暗自想道:“我没儿子,才受人这般看待。我求天拜地,也要求一个来,羞那些贼淫妇的毬脸。”于是起身走到后房,在文柜梳匣里取出王姑子整治的头胎衣胞来,又取出薛姑子送的药看。见药袋封得紧,小小封筒上面,刻着“种子灵丹”四个字,有诗八句:
嫦娥喜窃月中砂,笑取斑龙顶上芽。
汉帝桃花敕特降,梁王竹叶诰曾加。
须臾饵验人堪羡,衰老还童更可夸。
莫作雪花风月趣,乌须种子在些些。
后面还有赞曰:
红光闪烁,宛如碾就之珊瑚;香气沉浓,仿佛初燃之檀麝。噙之口内,则甜津涌起于牙根;置之掌中,则热气贯通于脐下。直可还精补液,不必他求玉杵霜;且能转女为男,何须别觅神楼散。不与炉边鸡犬,偏助被底鸳鸯。乘兴服之,遂人苍龙之梦;按时而动,预征飞燕之祥。求子者一投即效,修真者百日可仙。
后又有:
服此药后,忌萝卜、葱白。其交接,单日为男,双日为女,惟心所愿。服此一年,可得长生矣。
月娘看毕,心中渐渐地欢喜起来。用纤纤细指缓缓挑开封袋,解包开看,只见乌金纸三四层,裹着一丸药,外有飞金朱砂,十分好看。月娘放在手中,果然脐下热起来;放在鼻边,果然津津的满口香唾,不禁笑道:“这薛姑子果有道行,不知哪里去寻这样妙药灵丹!莫不是我合当得喜,遇得这个好药,也未可知。”想到此,连忙照原封好,锁进梳匣内。然后走到步廊下对天长叹道:“若吴氏明日壬子日服了此药,便得种子,承继西门香火,不使我做无祀的鬼,感谢皇天不尽了!”不觉日已偏西、月娘吃饭,回房歇息。
陈经济昨日不曾与金莲得手,好不难熬,那话儿硬了一夜。挨到这黄昏时,见各房掌灯,又知西门庆还未回来,使蹑足潜踪,进了花园走到卷棚后面,隐隐见到金莲也来了,真是苍天有眼,心心相通,窜了上去,紧紧抱住不放,把脸就挨了过去,对着嘴就亲起来。
金莲也是为昨日不曾上手,心中好不难过,一日坐立不安,见西门庆至晚未归,便来到卷棚边散心。她见有人扑了过来,抱住自己亲嘴,先是心中一唬,听到连叫“我的亲亲”,才知是陈经济。
陈经济说道:“我的亲亲,昨日孟三儿那冤家,打开了我们,害得咱硬梆梆撑起了一宿。”
“你这少死的贼短命,没些槽道的,把小丈母娘揪住亲嘴,不怕人来听见么?”金莲也搂住他,把舌头吐与他。
陈经济哪有回话的功夫,一手搂住金莲的粉项,一手就去解她的裤带。金莲半推半就,被经济一扯,扯断了。金莲故意失声,轻轻惊道:“怪贼囚,好大胆,就这等容易,要奈何小丈母娘?”
经济再三央求道:“我那前世的亲娘!要你儿的心肝煮汤吃,我也肯割出来。没奈何,只要今番成就成就。”这经济口里说着,腰下那话早已是硬梆梆露出来朝着金莲只顾乱插。金莲桃颊红潮,情动已久,哪有不迎合的。忽听有人说话,说是西门庆回来了,二人慌得赶紧分开,各归其所。
西门庆已是醉醺醺的,心里想着去金莲房,脚步却入了月娘屋。
月娘见了,暗想:明日二十三日,壬子日,今晚若留他,反挫明日大事。便对西门庆说道:“看你今晚醉昏昏的,不要在这里鬼混。我老人家月经还未净,不如去别的房里睡吧,明日再来。”说着,把西门庆推了出来。
西门庆进了金莲房,捧着金莲的脸说道:“这个是小淫妇了!方才不知怎的走到大娘房里去了。”
“那姐姐怎不留住你?”
“不知道。只说我醉了,要我明晚来。”说完,一把搂住金莲,伸手往她腰下摸去:“怪行货子,怎的夜夜干卜卜的,今晚里面有些湿答答的。莫不想着汉子,骚水发哩?”
原来金莲想着经济,还不曾澡牝。被西门庆无心打着心事,一时脸通红了,把言语支吾,半笑半骂,就澡牝洗脸,脱衣上床。
次日是壬子日,吴月娘清早起来,即便沐浴,梳妆,然后拜佛,念了一遍《白衣观音经》。这是王姑子教她念的。关上房门,烧香点烛,到后房,开取药来。又叫小玉炖酒。也不用粥,只吃了一些干糕饼食之类,双手捧药,对天祷告,先把薛姑子一丸药用酒化开,异香扑鼻,做三两口服下。再吃那头胎衣胞,虽说是粉末,终有些焦剌剌气味。月娘定了定心,把药末一把倒进口内,赶快把酒来大喝半碗,几乎呕将出来,眼睛都忍红了,喉舌间只觉得有些腻格格的,又吃了几口酒,再用温茶漱净口,向床上睡去。
这时,西门庆正走了过来,见门关着,便叫小玉开门:“怎么悄悄地关上房门,莫不道我昨夜去了,大娘有些二十四么?”
小玉答道:“我哪里晓得。”
西门庆走进房来,叫了几声。月娘正向里睡着,又吃了那下药的酒,哪里会答应他。西门庆讨了个没趣,怨怨地说了几句,走出房门,正好书童来说应伯爵在外边等。
到掌灯时分,西门庆回来,先进月娘的房里坐定。月娘也是起来不久,对西门庆说:“小玉说你曾进房来叫我,我睡着了,不知道你来。”
西门庆说道:“别说了,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哩。”
月娘笑道:“哪里说起,还会生你的气?”便叫小玉泡茶,又上夜饭吃了。
西门庆饮了几杯,加上这几日连连喝酒,只想早点睡。又因好几天不来月娘房里来,便想多加亲热奉承,把胡僧的膏子药用了些,胀得那阳物铁杵一般。
月娘见了,惊道:“那胡僧也这样没槽道的,唬人地弄出这样把戏来。”
西门庆搂过月娘,就要交合。
月娘心中暗忖:他有胡僧的法术,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是个好消息。于是脱衣上床。
次日,二人起得晚,直睡到日午的时候。潘金莲又是颠唇簸嘴,与孟玉楼说道:“姐姐前日教我看几时是壬子日,莫不是拣昨日与汉子睡觉?要不,怎这么凑巧?”
玉楼倒不在意,笑道:“哪有这事?”
这时,西门庆走来,金莲一把扯住,说道:“哪里人家睡得那般早,起得这样晏,日头都要落了。”
西门庆听了,一把反将金莲搂过来。玉楼见景,自回房去。西门庆把金莲按在床上,戏做一处。
吴月娘自从听见金莲背地讲她爱官哥后,两天不去官哥房里。这日,见瓶儿走来,听说孩子还是日夜啼哭,又打冷战不止,便劝瓶儿烧香许愿。月娘又把那天金莲背地说的话告诉了瓶儿,要瓶儿多防着她。瓶儿感激不尽。
正说着,迎春气吼吼地跑来,告诉瓶儿:“娘快去,官哥不知怎的,两只眼不住反看起来,口里卷些白沫出来。”
瓶儿唬得顿口无言,颦眉欲泪,一面差小玉报西门庆,一面急急忙忙回房来。
瓶儿刚进房,西门庆也赶到了,见了官哥果然放死放活的,惊得连连叫苦,一边骂奶子未用心看顾,一面差人立即请施灼龟来给孩子灼龟板,观祸福。灼了龟板,又请烧纸的钱痰火来赛神。说话间,孩子似乎平静了一些,睡起觉来,众人心里放了一半心。月娘高兴,差琴童去请刘婆子来收惊。一时,西门庆家一边是钱痰火穿戴法衣,仗剑执心,步罡念咒;一边是刘婆子念着“天惊地惊,人惊鬼惊,猫惊狗惊”地收惊。举家忙乱,西门庆跟着钱痰火拜神拜了个满身汗湿。只是那陈经济盯住潘金莲,金莲拉了陈经济,无人处亲嘴摸奶。进而又扯到屋里来,叫春梅闭了门,拿烧酒给他吃。陈经济得陇望蜀,又要亲嘴,被金莲打了一下,让春梅引了出去。不一会,西门庆安排好前边的事,进了金莲房,太乏了,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那官哥儿也退了热,睡得稳稳的。瓶儿摸了摸孩子的额头,流着泪,连连说道:“谢天谢天!”
次日,西门庆起得早,吩咐小厮挑了猪羊去城隍庙献神,自己冠带进庙,求签问卜。答是中吉,解云:“病者即愈,只防反复,须宜保重些。”打发香钱,骑马回家,告知瓶儿求签之吉,瓶儿心中又自在了一些。
此时,应伯爵已同几个帮闲在这里专等西门庆,已约好了十兄弟会中诸人,在郊园玩耍,喝酒听曲。众人来到河下,叫了两只小船,一只载食盒、酒,一只载人,又有韩金钏、吴银儿几个妓女,一直摇到南门外三十里有余的刘太监庄上。
玩闹了半日,书童走来,到西门庆身边,附耳低言道:“六娘身子不好,病得紧,快请爹回去,马已在门外备好了。”
西门庆一听,心中一惊,连忙对众兄弟作揖告辞。众人岂肯,西门庆以实情相告,翻身上马,直往家中奔驰而来。还未到门首,又翻身下马,两步做一步,一直走进瓶儿房里。迎春已在门口迎接,说道:“俺娘了不得的病,爹快看看她。”
西门庆走到床边,只见瓶儿“呀呀”叫疼,却是胃脘作疼。西门庆听她叫得苦楚,低首弯腰问道:“哪里不舒服?我这就请任医官来看你。”转身叫迎春:“快唤书童写帖,请任太医。”然后坐在床沿上,双手拥了瓶儿靠在自己身上。
瓶儿说道:“怎的这么重的酒气?”
西门庆说:“你胃虚了,便厌着酒气哩。”又问迎春:“你娘可曾吃些粥汤?”
迎春答道:“自早至今,一粒米也没有用,只吃了两三瓯汤儿。心口、肚腹、两腰子,都疼得异样的。”
西门庆颦着眉,皱着眼,连叹了几口气,又问如意儿:“官哥好些不?”
如意儿答道:“昨夜又起了点热,还在哭哩。”
西门庆叹道:“这般晦气,娘儿俩都病了,怎的好?留得娘的精神,还好去支持孩子哩。”
瓶儿又叫疼起来。
西门庆安慰道:“且耐心着,太医也就来了。待他看过脉,吃两盅药,就好了的。”
迎春忙着打扫房里,抹净桌椅,烧香点茶,又让奶子引逗得官哥睡着。
夜已深了,外边狗连连叫着。
不一会,书童掌了灯,照着任太医进了大门首坐在轩下。书童先进来报知西门庆。西门庆令拿茶出去,自己出房门迎接。
西门庆先看了太医的椅子。太医说道:“不消了。”也看了西门庆椅子,二人坐下。
迎春上前把绣褥垫着瓶儿的手,又把锦帕盖住玉臂,只从帐底下露出一段粉白的臂来与太医看脉。
任太医澄心定气,将三指搭了上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