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爱丁顿让钱德拉塞卡欲哭无泪
用权威作论证是不能算数的,权威做的错事多得很。
卡尔·萨根
1935年1月11日下午,在英国伦敦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年轻的印度天文学家钱德拉塞卡(1910—1995)当众宣读了自己在研究中的新发现:“相对论性简并”理论。25岁的钱德拉塞卡相信,他的新理论将会导致关于恒星演化的一个惊人而有趣的结论。
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发言之后,他一贯敬重的老师爱丁顿(1882—1944)却在会上嘲弄地宣称: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活着离开这个会场,但我的论文所表述的观点是,没有“相对论性简并”这类东西。
爱丁顿当时不仅在天文学界是功绩显赫的领袖人物,而且在相对论方面也是知名的权威,而25岁的钱德拉塞卡却只是刚刚获得博士头衔的无名之辈。在这一场势力极悬殊的“论战”(实际上几乎没有真正“战”过)中,“真理”的天平完全倾斜在爱丁顿一边,钱德拉塞卡几乎是落荒而逃。
但天文学后来的发展却明白无误地证实,钱德拉塞卡是正确的,爱丁顿错了。而且,由于爱丁顿的错误,加上他的权威性影响,天文学在恒星演化方面的研究被耽误了20至30年!
回忆这段历史,想必很有意义。
白矮星是一种什么星?
争论的起因是关于白矮星的看法,所以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白矮星。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亚当斯(1876—1956)利用分光镜研究双星天狼星中的天狼星B时,发现这是一颗十分奇特的恒星。它的奇特之处是亮度低(远不如天狼星A那么亮,只有后者亮度的1/10000),但表面温度却很高,在8000℃左右(太阳表面温度只有6000℃),与天狼星A的表面温度相差不大(天狼星A表面温度为10000℃左右)。温度高而亮度低,这说明天狼星B的表面积要比天狼星A小得多,据计算只能是天狼星A表面积的1/2800左右。这样,天狼星B的体积很小,与地球相仿;但是,它的质量却大得惊人,与太阳相仿。所以天狼星B的密度也高得惊人,大约是106克/厘米3,大大高于人们熟悉的物质的密度。例如,这个密度比地心物质的密度高几万倍!
亚当斯的发现说明天狼星B属于一类全新的恒星,它与普通恒星相比简直像一个侏儒,正是根据这一特点,天文学家把这种恒星称为“白矮星”(white dwraf,dwraf的意思就是“侏儒”、“矮子”)。没过多久,人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其他的白矮星。
在亚当斯发现白矮星之前4年,卢瑟福已经证明,原子的大部分质量集中在极小的原子核里。核外广大的空间被在一定轨道上高速转动的电子占据。白矮星的超高密度似乎只能想象为原子被压“碎”了,即原子核外沿轨道运动的电子被压得不再沿原来的轨道高速转动,也不再占据核外广大空间,而被压得紧靠着核,好像成了一种自由运动的电子。但科学家们一时接受不了这种设想,因而大部分天文学家对白矮星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爱丁顿很前卫,他不仅相信白矮星是真实的,还根据白矮星的特点,算出天狼星B的表面引力应该是太阳的840倍,是地球的23500倍。如果真是如此,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天狼星B发出的光线“红移”(red shift)现象则会比太阳光的红移明显得多。为此,爱丁顿建议亚当斯对天狼星B的红移现象做一次测试。1925年,亚当斯进行了测试,结果他测定的白矮星的红移数值与爱丁顿的预计完全相符。
从此以后,人们不再怀疑星空真的有白矮星了。
但是,形成白矮星的物理机制仍然是一个谜。这个谜使当时的天文学家和天文物理学家,包括爱丁顿在内的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与天文学似乎毫不相关的量子力学的一项新的成果,却为天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满意的解释。

英国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爱丁顿爵士,他是当时科学界研究相对论和天文学的权威
1926年,费米和狄拉克在利用量子力学的方法研究“电子气”时证明:在高密度和(或)低温条件下,电子气的行为将背离经典定律,而遵守他们两人重新表述的量子统计规律(费米-狄拉克统计规律)。在新的量子统计规律中,压强-密度的关系与温度无关,压强值仅为密度的函数,即使在绝对零度时,压强仍然有一定的值。量子统计规律刚一公布,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福勒(1889—1944)立即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白矮星这一特殊的物质状态。在白矮星的条件下,电子离开了正常情形下的运动轨道,被“压”到一块儿,成了所谓“自由”的电子,而原子核则成了“裸露”的核,这种状态称为“简并”(degeneracy)态。福勒证明:高密度白矮星中电子气的“简并压力”非常大,大得足以抵抗引力的收缩压力;在白矮星那样的压力和密度条件下,物质的能量确实比地球上普通物质的能量高得多;任何质量的恒星发展到晚年时,都将以白矮星告终——白矮星是所有恒星的坟墓。1926年12月10日,福勒在英国皇家学会公布了他的发现。
福勒的这一发现是当时刚诞生的量子力学的一个合理的外推,这一结论使爱丁顿十分满意。爱丁顿和许多天文学家认为:与白矮星有关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人们不必再为它操心了。
有趣的是,科学史上有无数事例说明,每当科学家认为某一个重大发现已经被“万无一失”的理论解释得令人非常满意的时候,巨大的危机就会“乘虚而入”。这次也不例外。正当人们额手相庆、竞相祝贺之时,一位到英国求学的印度年轻人钱德拉塞卡却有了不同的看法。
1928年,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索末菲(1868—1951)访问印度,这时正在马德拉斯大学读书的钱德拉塞卡听了索末菲的讲演后,才知道什么是“费米-狄拉克统计”。由于福勒的论文中有该统计的应用,于是他仔细阅读了福勒的文章。虽然当时钱德拉塞卡的各方面知识很欠缺,但他已经拥有的知识足以使他对福勒的结论产生疑问。于是他决心继续钻研这个爱丁顿认为“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

索末菲和家人野游
经过几年的研究,钱德拉塞卡有了比较明确的新观点。星体到了晚期,由于引力超过星体内部核反应产生的辐射压力,星体被压缩而变小,星体物质处于简并态;由于这时物质粒子相距愈来愈近,因而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粒子间将产生一种与引力相抗衡的排斥力,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处于平衡状态,于是形成白矮星。钱德拉塞卡经研究发现,当考虑到相对论效应,星体由于收缩而变得足够密时,不相容原理造成的排斥力不一定能抗衡引力。这里有一个临界质量1.44M⊙(M⊙代表太阳质量,开始时,钱德拉塞卡计算的临界质量是0.91M⊙),如果星体质量超过这个临界质量,星体的引力将大于排斥力,恒星在成为白矮星之后,将继续收缩……并不一定像福勒和爱丁顿他们设想的那样,所有恒星的晚期均以白矮星告终。
一场争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了
1930年,钱德拉塞卡带着两篇论文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篇论述的是非相对论性的简并结构,另一篇则论述了相对论性简并机制和临界质量的出现。福勒看了这两篇文章,对第一篇文章他没有什么意见,赞同钱德拉塞卡已取得进展;然而第二篇所说的相对论性简并及由此而生的临界质量,福勒持怀疑态度。福勒把第二篇论文给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米尔恩(1896—1950)看,征求他的意见。米尔恩同福勒一样,也持怀疑态度。
虽然两位教授对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持强烈怀疑态度,但钱德拉塞卡通过与他们的讨论和争辩,愈加相信临界质量是狭义相对论和量子统计结合的必然产物。1932年,钱德拉塞卡在《天文物理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观点。
1933年,钱德拉塞卡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被推举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几年下来,他与米尔恩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和深厚的友谊,也逐渐与爱丁顿由相识到相知。爱丁顿经常到三一学院来,与钱德拉塞卡一起吃饭,一起讨论问题,爱丁顿几乎了解钱德拉塞卡每天在干什么。
到1934年底,钱德拉塞卡关于白矮星的研究终于胜利完成。他相信他的研究一定具有重大意义,是恒星演化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他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两篇论文,交给了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皇家天文学会作出决定,邀请他在1935年1月的会议上简单说明自己的研究成果。
会议定于1935年1月11日星期五举行,钱德拉塞卡踌躇满志,自信在星期五下午的发言中,他宣布的重要发现将会一鸣惊人。但在星期四晚上发生了一件事,使钱德拉塞卡感到疑惑和不安。那天傍晚,会议助理秘书威廉斯小姐把星期五会议的程序单给他时,他惊讶地发现在他发言之后,爱丁顿接着发言,题目居然与他的题目一样,也是“相对论性简并”。钱德拉塞卡曾多次与爱丁顿讨论过相对论性简并,并且将他所知道的公式、数字都告诉了爱丁顿,而爱丁顿从来没有提到过他自己在这一领域里的任何研究,但是明天他也要讲相对论性简并。钱德拉塞卡觉得,“这似乎是一种难以置信的不忠诚行为”。
晚餐时,钱德拉塞卡在餐厅里碰见了爱丁顿,钱德拉塞卡以为爱丁顿会对他作出某些解释,但是爱丁顿没有任何解释。他只是十分关心地对钱德拉塞卡说:
你的文章很长,所以我已要求会议秘书斯马特作出安排,让你讲半个小时,而不是通常规定的15分钟。
钱德拉塞卡很想趁机问一下,爱丁顿在他自己的论文中写了些什么,但出于对他的高度尊敬,他不敢问,只是回答说:“太感谢您了。”
第二天会议前,钱德拉塞卡和天文学家麦克雷正在会议厅前厅喝茶,爱丁顿从他们身边走过。麦克雷问爱丁顿:
爱丁顿教授,请问相对论性简并指的是什么?
爱丁顿没有回答麦克雷的问题,却转身向钱德拉塞卡微笑说:
我要让你大吃一惊呢!
可以想见,钱德拉塞卡听了这句话后,除了感到纳闷以外,大约多少会有些不安。
星期五下午会议上,钱德拉塞卡简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一颗恒星在烧完了它所有的核燃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如果不考虑相对论性简并,恒星最终都塌缩为白矮星——这是当时流行的理论。但是,当人们考虑到相对论性简并的时候,任何一颗质量大于1.44M⊙的恒星在塌缩时,由于巨大的引力超过恒星物质在压缩时产生的简并压力,这颗恒星将经过白矮星阶段继续塌缩,它的直径越变越小,物质密度也越来越大,直到……
啊,那可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明确地宣称:
一颗大质量的恒星不会停留在白矮星阶段,人们应该推测其他的可能性。

印度裔美国天文学家钱德拉塞卡,198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米尔恩对钱德拉塞卡的发言作了一个简短的评论后,大会主席请爱丁顿讲“相对论性简并”,爱丁顿开始发言了。钱德拉塞卡怀着异常紧张的心情,等待着这位权威的裁定。
钱德拉塞卡博士已经提到了简并。通常认为有两种简并:普通的和相对论性的。……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活着离开这个会场,但我的论文所表述的观点是,没有相对论性简并这类东西。
钱德拉塞卡惊呆了!这对于钱德拉塞卡不啻为迎头一棒。怎么爱丁顿从来没有与他讨论过这一点呢!?在那么多的相互讨论中,爱丁顿至少应该表明一下他的观点才对呀!但是,爱丁顿并没有办法驳倒钱德拉塞卡的逻辑和计算,他只是声称,钱德拉塞卡的结果过于稀奇古怪和荒诞。钱德拉塞卡认为,超过临界质量的恒星“必然继续地辐射和收缩,直到它缩小到只有几千米的半径。那时引力将大得任何辐射也逃不出去,于是这颗恒星才终于平静下来”。爱丁顿非常肯定地说:
这个结局简直荒谬透顶。
钱德拉塞卡说的这种最终结局实际上就是现在已被广泛承认的黑洞(black hole),这个名称是30多年后于1969年由美国科学家惠勒(1911—2008)正式定下的。但1935年1月11日的那天下午,爱丁顿断然宣布它是绝不可能存在的。他的理由是:
一定有一条自然规律阻止恒星做出如此荒谬愚蠢的行为!
一场争论,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了。
无法孤军作战,只好改弦更张
1935年1月11日的下午,对于钱德拉塞卡来说,真是一个惨淡得可怕的下午。他曾经心痛地回忆过那天下午会议结束后的惨况,他写道:
在会议结束后,每个人走到我面前说“太糟糕了,钱德拉塞卡,太糟糕了。”我来参加会议时,本以为我将宣布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结果呢,爱丁顿使我出够了洋相。我心里乱极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还要继续我的研究。那天深夜一点钟左右我才回到剑桥,我记得我走进了教员休息室,那是人们经常聚会的场所。那时当然空无一人,但炉火仍然在燃烧。我记得我站在炉火前,不断地自言自语地说:“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不是砰的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
第二天上午,钱德拉塞卡见到了福勒,把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福勒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其他一些同事也私下安慰钱德拉塞卡。钱德拉塞卡不喜欢这些“关怀”,因为从大家说话的语气中,他听出人们似乎都已经肯定爱丁顿是对的,而他肯定是错了。这种语气让钱德拉塞卡受不了,因为他相信自己肯定是对的。爱丁顿反对他的结论,却提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爱丁顿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不相信大自然会“做出如此荒谬愚蠢的行为”。但这种“理由”在钱德拉塞卡看来未免有些滑稽可笑:他怎么就知道大自然喜好什么?
爱丁顿没有停止对钱德拉塞卡的“错误”的批评。193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天文学会会议期间,爱丁顿再次在讲话中批评钱德拉塞卡的研究结果,说那简直是异端邪说,而所谓“临界质量”在爱丁顿看来简直是愚蠢可笑之极。钱德拉塞卡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会议主席没有让他对批评作出回答。钱德拉塞卡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本能地认为大家之所以赞同爱丁顿的意见,是因为他是权威和名气大;而之所以反对他的结论,只不过是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无名小卒。这公正吗?
钱德拉塞卡的想法是合乎事实的,这可以从麦克雷在1979年11月写的一封信中看得十分清楚。麦克雷在信中写道:
我记得在一次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爱丁顿发表了讲话,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是一种不能应战的争论。……当我聆听了爱丁顿的讲话以后,我不可能考虑他所说的所有含义,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可能是对的。
麦克雷接着以勇敢的精神解剖了自己:
使我感到羞愧的是我没有试图去澄清爱丁顿引起的争论。假如是其他人而不是爱丁顿引起这样的争论,我想我会去澄清的。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满意爱丁顿的发言,既然大家都满意,坦白地讲,我也情愿事态如此发展,更何况我不是研究恒星结构的。然而,我承认我知道一些狭义相对论,我本应该从这方面深入研究一下爱丁顿提出的问题。
钱德拉塞卡知道,他和爱丁顿争论的是一个物理学问题,只在天文学圈子里争是争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的。他决定求助于玻尔、泡利这些物理学大师和量子力学的开拓者们。1935年1月下旬,钱德拉塞卡写了封信给他的好友罗森菲尔德(1904—1974)。罗森菲尔德那时正在哥本哈根工作,当玻尔的助手。钱德拉塞卡在信中将他和爱丁顿争论的焦点作了详细的介绍后,接着写道:
如果像玻尔这样的人能作一个权威性的声明,那么,对这个争论的解决将有很大的价值。
可惜的是玻尔当时正在忙于研究原子核,以及与爱因斯坦争论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根本没有精力专心地研究一个新课题,所以无法满足钱德拉塞卡的愿望。但罗森菲尔德在几次通信中,将他与玻尔几次初步的讨论结果告诉了钱德拉塞卡。他们认为爱丁顿的意见没有什么价值,并且高度评价了钱德拉塞卡的观点。罗森菲尔德在一封信里写道:
在我看来,你的新工作非常重要。我认为除了爱丁顿以外,每个人都会承认它建立在完善的基础上。
罗森菲尔德还建议钱德拉塞卡把争论的焦点告诉泡利,请这位被誉为“物理学的良知”的大师进行仲裁。钱德拉塞卡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把他的“相对论性简并”的推导,以及爱丁顿的论文等有关资料寄给了泡利。泡利给了令人鼓舞的回答,他认为,把他的不相容原理应用于相对论系统时,没有任何可以犹豫的;爱丁顿的主要错误是在把不相容原理应用于相对论的情形时,过分地依赖天体物理计算的结果。不幸的是,泡利的主要兴趣不在天体物理学,因此他也不愿意卷入这场争论。
由于玻尔、泡利等物理大师不愿介入,结果正如钱德拉塞卡预料的一样,混乱一直在天文学中蔓延,而且持续了20年。钱德拉塞卡想从玻尔等人那里得到权威性评述,他的原意并非想让人们相信他的理论的正确性(对此他几乎没有怀疑过),而是想尽快消除天文学中的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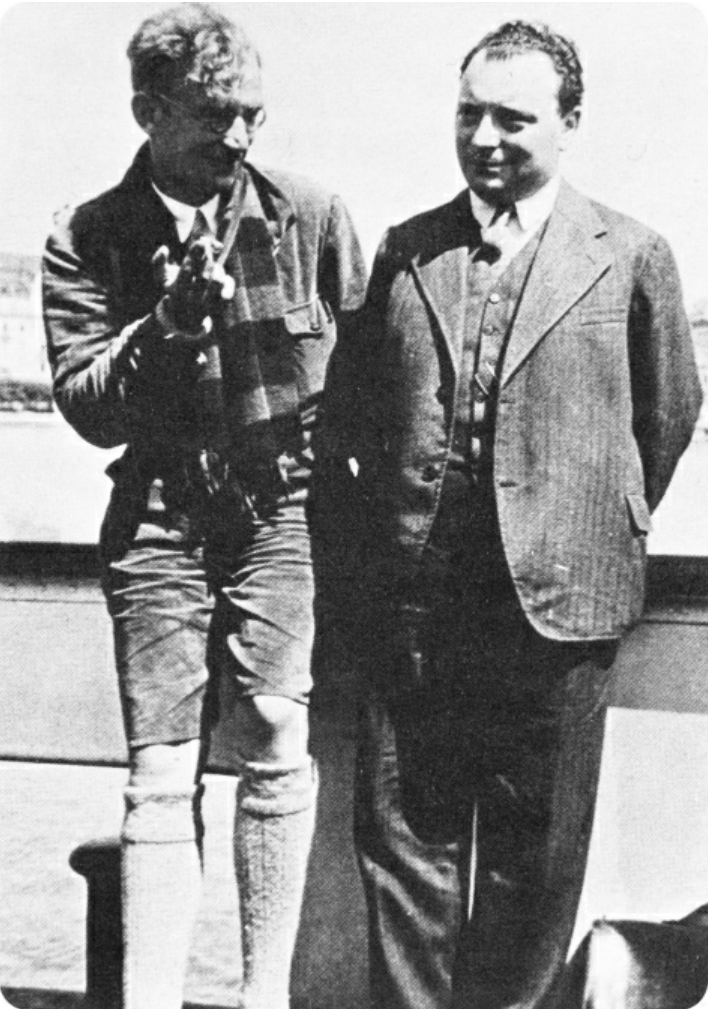
泡利(右)与伽莫夫合影于瑞典一个湖边
由于物理学家们无心介入,钱德拉塞卡的处境变得十分不利,他几乎失去了在英国寻找一个职位的任何机会,人们对爱丁顿的嘲笑记忆极深。没有办法,他只得于1937年来到美国,很幸运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找到了一个教职。与此同时,钱德拉塞卡决定暂时放弃恒星演化的研究,但他坚信他的理论总有出头露面的一天。于是他把他的整个理论推导、计算、公式等统统写进了一本书中,这本书的书名是《恒星结构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ellar Structure)。
写完了这本书以后,他改弦更张,开始研究星体在星系中的概率分布,后来又转而研究天空为什么是蓝颜色的。有趣的是,钱德拉塞卡后来似乎十分满意这种不断转换研究领域的做法,以致他后来又全面地研究了磁场中热流体的行为、旋转物体的稳定性、广义相对论,最后他又从一种全然不同的角度回到了黑洞理论。1983年,他终于因为“对恒星结构和演化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因为对白矮星的结构和变化的精确预言”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这已是他最初提出这种理论后的48年了!
真理超越了最强有力的科学家
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好:
人生的命运是多么难以捉摸啊!它可以被几小时内发生的事而毁灭,也可以由几小时内发生的事而得到拯救。
我们的确可以从历史上找到许许多多欧文·斯通所说的被“毁灭”或被“拯救”的例子。有时候这种毁灭和拯救完全取决于命运,人几乎没有机会去改变它;但在更多的情形下,命运却可以取决于当事人本身。法国著名作家蒙田曾意味隽永地说过:
命运对于我们并无所谓利害,它只供给我们利害的原料和种子,任那比它更强的灵魂随意变换和利用,因为灵魂才是自己的幸与不幸的唯一主宰。
钱德拉塞卡后来的经历可以说是蒙田说法的一个佐证。1935年1月11日那天下午突然落到钱德拉塞卡头上的严重打击,有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人生;但对于具有“更强的灵魂”的钱德拉塞卡,这一严重的打击却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什么样的深刻道理呢?且看他1975年(距1935年整整40年)一次演讲中提出的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1975年4月22日在芝加哥大学,钱德拉塞卡作了题为“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创造性的模式”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文学家和艺术家,如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他们的创作生涯不仅一直延续到晚期,而且到了晚年他们的创作升华得更高、更纯,他们的创造性也在晚年得到更动人的发挥;但科学家则不同,科学家到了50岁以后(甚至更早),就基本上不再会有什么创造性了。
1817年,贝多芬47岁,在此前他有好久没有写什么曲子了,这时他却对人说:
现在我知道怎么作曲了。
钱德拉塞卡对此评论说:
我相信没有一个科学家在年过40时会说:“现在我知道怎样做研究了。”
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代(1877—1947)曾经说:
我不知道有哪个数学奇迹是由50岁开外的人创造的……一个数学家到60岁时可能仍然很有能力,但希望他有创造性的思想则是徒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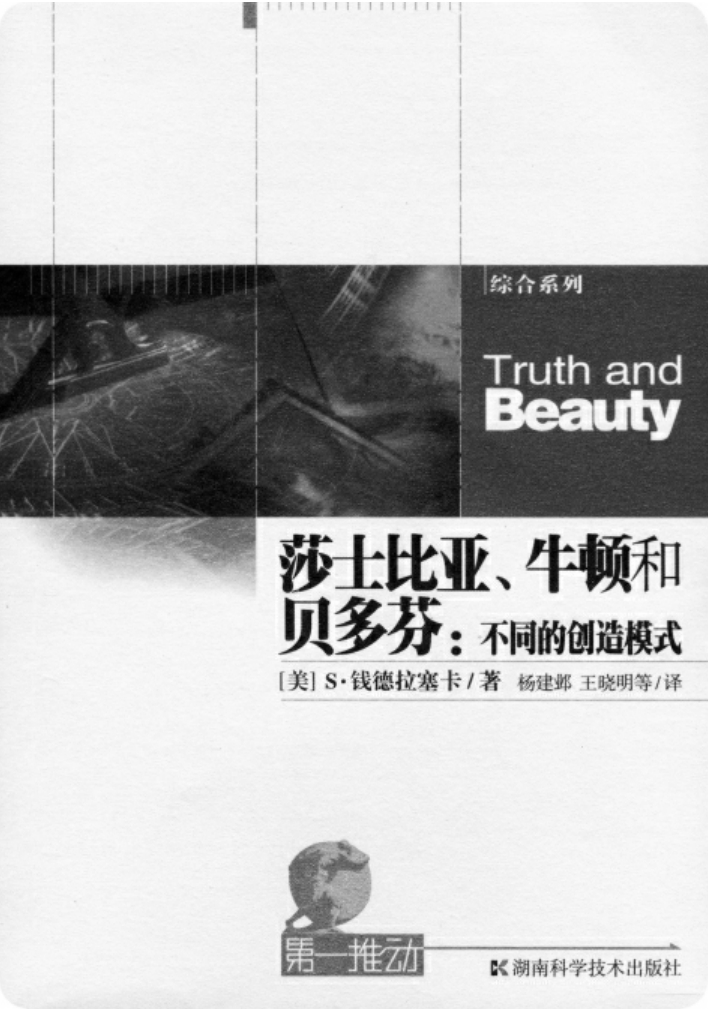
钱德拉塞卡写的《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中文译本(英文书名为Truth and Beauty)
他还说过:
一个数学家到30岁已经有点老了。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也讲过:
科学家过了60岁,益少害多。
有意思的是,当英国物理学家瑞利67岁时,他的儿子问他对赫胥黎的话有什么看法时,瑞利回答:
如果他对年轻人的成就指手画脚,那可能是这样;但如果他一心一意做他能做的事,那就不一定益少害多。
钱德拉塞卡还举了一个惊人的例子——爱因斯坦。他指出,爱因斯坦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1916年他发现了举世震惊的广义相对论,那时他37岁。到20世纪20年代初,爱因斯坦还做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工作,但从那个时期往后,“他就裹足不前,孤立于科学进步潮流之外,成为一位量子力学的批评者,并且实际上没有再给科学增添什么东西。在爱因斯坦40岁以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洞察力比以前更高了”。
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像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那样不断地具有创新精神呢?这正是钱德拉塞卡感到非常值得探讨的地方。钱德拉塞卡通过自己奇特的经历,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
由于没有更恰当的词,我只能说这似乎是人们对大自然产生某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有过伟大的洞见,作出过伟大的发现,但他们此后就以为他们的成就足以说明他们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必然是最正确的。但是科学并不承认这种看法,大自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构成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超越了最强有力的科学家。
钱德拉塞卡举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为例:
以爱丁顿为例,他是一位科学伟人,但他却认为,必然有一条自然定律阻止一个恒星变为一个黑洞。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无非是他不喜欢黑洞的想法。但他有什么理由认为自然规律应该是怎样的呢?同样,人们都十分熟悉爱因斯坦的那句不赞成量子力学的话:“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的。”他怎么知道上帝喜欢做什么呢?
钱德拉塞卡的话是很有启发性的。真正伟大的发现固然是由一些有“傲慢”精神的人作出的,他们正是敢于对大自然作出评判才作出了伟大的发现。但是,要想持续不断地在科学探索中作出新的发现,又必须对大自然保持某种谦虚精神。
有一次,当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听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人很谦虚时,他不无妒意地说:
他有许多需要谦虚的地方。
这句话用到科学家头上倒是非常合适的。一位科学家,无论他曾经作出过多么伟大的发现,都应该对大自然“有许多需要谦虚的地方”!
但要长期保持谦虚精神并不那么容易。仅仅知道“需要谦虚”是不能保证一个人真正谦虚的,似乎还应该有一定的方法、程序来保证人们时时刻刻不得不谦虚。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保证这一点呢?钱德拉塞卡提出了一个良方,他说:
每隔十年投身于一个新领域,可以保证你具有谦虚精神,你就没有可能与青年人闹矛盾,因为在这个新领域里他们比你干的时间还长!
这肯定是钱德拉塞卡通过自己的经历得出的体会。1935年的打击,使他不得不离开他研究了近7年的恒星演化领域,转而研究其他新领域。这种被迫的转向想不到给钱德拉塞卡带来了意外的好处,使他终生习惯,甚至喜欢不断转换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也使他明白了一个长期令人迷惑的奥秘:科学家的创造性生涯为什么远比文学家和艺术家短?
当钱德拉塞卡晚年回忆1935年的这场争论时,他似乎已经忘了当年的绝望心情,而颇为感谢爱丁顿当年给他的沉重打击(请读者注意,钱德拉塞卡和爱丁顿终生保持着亲密的友谊),使他幸运地放弃了原来的专业。下面是他的一段回忆:
假如当时爱丁顿肯定自然界有黑洞存在,他就会使这个领域成为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黑洞的许多性质也可能提前20~30年发现。那么,理论天文学的形势将大不相同。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对我会是有益的,爱丁顿的称赞将使我的地位有根本变化,我会很快变得十分有名气。但我确实不知道,在那种诱惑和魅力面前我会变得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体会,以及许多伟大科学家未能对大自然始终保持谦虚的教训,应该说是科学史中令人瞩目的事情,它会为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