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年,雅典人已经进入他们驱逐僭政、建立自由以来的第100年。这100年里,在绝大部分时候——自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508/507年改革以来——,雅典人享有的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开始的时候,这个民主政体比较温和;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经过埃斐亚提斯(Ephialtes)和伯利克里变革,这个民主政体从温和走向彻底。时间流逝,施行民主政体的雅典权势增长、日渐繁荣,雅典人也就再无动力去摧毁民主政体、代之以寡头政体。然而,寡头政体才是希腊人最为熟悉的政治体制。关于寡头阴谋的流言时有出现,但无一得以付诸行动。[1]雅典的绝大部分上层民众是接受民主政体的,他们要么在民主政体之内参与竞争、争取民主政体的领导权,要么就远离政治。然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出身显耀。
即便如此,对于民主理念和民主政体的敌意并没有消失。毕竟,希腊的贵族政治传统压倒一切。荷马史诗呈现的世界,价值观念全然是贵族传统的,而荷马史诗是所有希腊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决策、下命令的是贵族,平民只需恪守本分,遵守命令。[2]在墨伽拉的第欧根尼(Theognis of Megara)的诗歌中,6世纪时,贵族遭遇政治与社会剧变,心怀怨恨(-106,107-);在民主政体的敌人那里,第欧根尼的言辞和理念一直深入人心,颇具影响,直到公元前4世纪时还被柏拉图援引并予以肯定。第欧根尼将人类分作截然不同的两类:善而高贵的,坏而低贱的。这种分类的基础是出身,将社会地位和德行清晰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高贵的人掌握判断(judgement,gnome),常怀敬畏(reverence,aidos);因此,也只有高贵的人有能力行使温和、节制、正义。这些品质只有少数人具备,多数人都不具备;而那些不具判断且不怀敬畏的人,自然不知礼耻、傲慢自许。此外,这些优等品质只能通过出身获得,不能通过教育养成:“[要造就好人],生养容易,教养困难。驽钝之辈不可教,恶劣之徒不可改。……如果能够人造并灌输思想,则善人之子屡从善教,绝无可能变得邪恶。然而,欲教化邪恶之徒,徒劳也。”[3]
忒拜诗人品达(the Theban poet Pindar)——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称他为“贵族之音”——对于雅典上层民众的影响势必较第欧根尼更大。品达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其凯歌(odes)赞美的是运动场上的胜利,而这正是贵族文化非常珍视的成就。品达凯歌所传达的理念与第欧根尼几无二致:出身显耀者相对于芸芸大众而言,在智力与德行方面都天生优越;这种差别无法被教育抹去。
血统煊赫者质地贵重;
以学窥道者却如临深夜,辗转各路,
步履永迟疑,思绪常不定,
徒劳尝试,所及却不过是德行的枝末。[4]
理解能力同样是与生俱来。只有生来智慧的人能够理解他的诗篇及其他重要事务:
在我臂弯之中,诸箭颤抖待发;(-107,108-)
它们与理解之人谈话;大部分人与之交谈却需要翻译。
天赋智慧者才真正博知;庶民就得教。
他们无所不谈,然嘈杂喧闹,徒劳一如
乌鸦之于宙斯的神鸟。[5]
这些观念,最起码也是在暗示,民主政体并不明智;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既不公平,也不道德。
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指出民主之不公正,必定是在重复那些针对民主的古老怨言:“……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否相互平等”[6];民主正义“不主张按照功勋为准的平等而要求算术平等”。[7]这些观点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作品,这表明,这些关于应赏阶层与非应赏阶层(the deserving and undeserving classes)之间自然而永久之差序的古老理念,自第欧根尼和品达开始,一直持续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还有一部小册子,《雅典政制》(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该书被发现于色诺芬著作之中,大约写于420年代,但肯定并非色诺芬所写——作者是个不知名的人,一般用“老寡头”(The Old Oligarch)指称之。这本小册子清楚反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这股类似情绪。[8]《雅典政制》的作者有着智术师般的沉静客观,但书中也隐藏着激昂的不满。“对于雅典人的政治体制而言,我不因为雅典人选择了这样的政治体制而赞扬他们,因为雅典人选择了这样的政治体制,也就将政体中更好的那一部分给予了庶民败类(vulgar people,poneroi),而没有将之给予善类士族(the good,chrestoi)。”他们靠抽签决定那些安全、有偿之职位的归属,却把将军和骑兵指挥官这样的危险职位留给选举,留给“最能胜任之人”。[9]
到了420年代,时间和变迁已经改变了阶层划分的基础。高贵的出身是第欧根尼和品达的准绳,但《雅典政制》作者强调的却是金钱能够塑造嘉言善行和政治才干:(-108,109-)“在所有国家中,民主制都被视为贵族制的对立面;最善之人最不放纵、最不邪魅,他们是德行最敏锐的眼睛;相反,芸芸大众往往无知、无序、无德行;这是因为,贫穷日益败坏着德行,无教和因贪婪而导致的无知也日益败坏着德行。”[10]无疑,《雅典政制》的作者及他所属的那个阶层的人们,都仔细思考过何谓善的政体,而这种善的政体是与民主政体截然对立的。他们想要的是“优诺弥亚/善治”(eunomia)。悌尔泰俄斯(Tyrtaeus)将斯巴达政体称为“优诺弥亚”,品达将科林斯寡头政体称之为“优诺弥亚”。在这样的政体中,最善之人、最能胜任之人制定律法。善类惩罚败类;只有善类士族会就公共事务进行思考,“他们不会允许疯子在贵族议事会中就坐,也不会允许疯子在公民大会上讲话。但是,以上诸条充分执行的话,庶民势必陷入被奴役的状态”。[11]因此,《雅典政制》作者懂得,“劣治”(bad government,kakonomia),亦即民主政体,服务于庶民利益,他也预见到,庶民将出于一己之利努力维护这种政体。“但是,任何人——如果他不属于庶民之列——宁愿生活于民主之治下而不愿生活于寡头之治下,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变得不道德,因为他非常了解,在民主制国度中坏人可以不被发现,而在寡头制国度中坏人无所遁形。”[12]这些言辞意思十分明确,表明作者及其同党视倾覆民主政体并代之以更好的政体这一举动为道德责任。但是,在《雅典政制》作者写作之时,民主政体看起来十分坚固,不可动摇。[13](-109,110-)
到了411年,民主政体所面临的实践问题,连同其失败与踉跄一起,加剧了人们对民主体制的不满,也给人们攻击民主体制提供了机缘。受人尊敬的领袖客蒙(Cimon)、伯利克里、甚至尼基阿斯都逐一退位,替代他们的是克里昂、海珀布鲁斯、甚至是出身高贵但臭名昭著的阿尔喀比亚德,这类人员变动令贵族更难接受民主之治。缺乏强有力、受尊敬的政治领袖,雅典人内部的分歧开始显现并不断扩大。411年,领袖真空似乎日益被党社(hetairiai,clubs)所填满,这些党社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日渐升温,特别是在民主政体的敌对阵营那一边。[14]
这些党社的成员及有财产阶层的其他一些人过去和现在所承担的经济负担之沉重,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因为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存在时刻威胁着雅典帝国及其粮食供给,雅典人不得不尽可能扩大舰队规模并全年维持,打仗比以前更加昂贵了。其次,公共财政支出方面,对平民的支出也许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15]与此同时,纳赋盟邦叛乱、贡赋流失,战争干扰商业、关税减少,公共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最后,雪上加霜的是,有能力为城邦承担宗教与军事义务产生的经济负担的富裕雅典人,数目日益减少。在431年,战争爆发前夕,有资格担任重装步兵或更高职务的雅典人——这些是有资格参与宗教仪式的人——可能高达25000人。[16]到411年,因为瘟疫流行和战斗伤亡的缘故、特别是因为在西西里损失的缘故,这一人数似乎减少到了9000。[17]两个数字都未必精确,也未必准确;但是,对该数据的任何修订也必定仍然能够反映:411年能够承担国家义务的雅典人数急剧下降了。
只要看看以吕西阿斯(Lysias)之名留存至今的那些演说辞,我们就知道,公务支出委实高昂。在其中一篇演说辞中,吕西阿斯提到了一个名叫亚里斯托芬尼(Aristophanes)的人参与公共服务的花费高达15塔伦特(-110,111-),其中包括特别战争税和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费用。[18]在另一篇吕西阿斯演说辞中,这位雄辩家叙述了他从411/410年到404/403年的支出,一共差不多是10塔伦特。他列出了当时雅典富裕公民承担的一系列公共义务,可为参考:制作悲剧和喜剧;支付合唱比赛、舞者、运动竞赛、及三列桨战舰竞技;在7年之内,装备6艘三列桨战舰参战;同时,他两次缴付应缴的特别战争税。[19]诚然,他吹嘘说,自己所付是按律法应付金额的4倍之多。因此,考虑到他所属阶层的公民中必定有不如他慷慨之人,在相同时段内,这些人所付大约不超过2.5塔伦特。即便如此,2.5塔伦特亦是一笔巨款。我们得知道,1个塔伦特价值6000德拉克马,而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1个德拉克马是相当不错的日薪。同时,在那些年里,在舰队划桨的雅典公民指望着靠半个德拉克马勉力支撑。对于如此巨款,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事实当中来进行理解。尼基阿斯,雅典最富裕的人之一,留下一份不超过100塔伦特的财产给儿子;尼基阿斯之子——也不是什么出名的败家子——留下一份不超过14塔伦特的财产给嗣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雅典许多家族的财产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公务支出而严重缩水。[20]到411年,特别是自西西里惨祸以来的年份,前所未有的开支情况必定令人非常痛苦;有财产阶层不需太大想象力就可以预见,在未来,开支定会有增无减。
民主政体不仅道德立场堪忧,据说还政策愚蠢,执行不力,政治领导日渐衰败,民众经济负担沉重,这本来就是雅典之“疑民主派”长久以来关注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在西西里惨祸之后都变得更加严重。411年带来的新事态是,西西里惨祸之后,雅典人普遍觉得在对伯罗奔尼撒人的这场战争中,胜利无望,存亡堪忧。但很快,西西里惨祸之后的消沉沮丧就化为了决心与行动。对于帝国内部叛乱,雅典处置(-111,112-)相当得力,叛乱似乎马上就要被全部扑灭。如果雅典军队能够收复米利都和开俄斯的话,那么波斯人很可能就会想到,说雅典覆亡在即未免太过夸张,同时,波斯人也可能就此撤回他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支援,斯巴达的爱琴海冒险以及由此对雅典帝国形成的威胁将不复存在。
然而,这样一个机遇因为斐林尼库斯的米利都决策而丧失了。事与愿违,帝国叛乱向海勒斯滂地区继续扩散,威胁到了雅典生命线。紧急储备基金一分不剩,公共金库空空如也。[21]替萨斐尼修复了与斯巴达人的分歧,允诺将会把腓尼基舰队投入战场,与雅典人作战。[22]最终,斯巴达人在海勒斯滂地区获得了一个据点,威胁着雅典的供给线,并赢得了战争。413年,贤哲制度的建立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民主的政治体制。在如此困难险阻之中,不难想象,许多雅典人愿意进一步改变国内状况,他们希望削弱民主实践,作出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甚至希望更迭政权。历史长河中,一个国家——甚至是个民主国家——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危机时期选择摒弃和平时期政治实践模式的例子屡见不鲜。1940年,英国搁置了平时采用的政治竞争,建立联合政府。内阁组成有所变化,政府管理职能被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而同时担任首相和国防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则掌握了几近独裁的权力。就算是对于忠实的民主派而言,对民主做些限制也有相当的理据,遑论那些敌视民主的人们。
民众普遍支持传统的全面民主,寡头无力牵头发动运动,这些证据表明,改变政治体制的运动并非始自雅典。革命运动的煽动者是叛徒阿尔喀比亚德。他一心求自保,对权力与荣誉胃口不减,希望重归雅典,重归这个几年前刚刚谴责并诅咒了他的城邦。在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那里,他都是个亡命之徒,(-112,113-)安全的希望全然在乎替萨斐尼给他的保护;即便如此,他自身的情形也颇为脆弱,因为节度使替萨斐尼诡计多端,野心勃勃,十分清楚并相当注意自己的利益。替萨斐尼之利用阿尔喀比亚德,不亚于任何一个想利用他的雅典人;替萨斐尼为了一己之利而抛弃这门徒傀儡,也是迟早的事。因此,阿尔喀比亚德的计划,就是利用他对替萨斐尼的影响,取得波斯支持,保障自身安全,替雅典赢得胜利。[2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遣人与“那些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些人”沟通——应当就是将军们、三列桨战舰舰长们、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个人,请求他们“向最善的人”多多提及他自己——当然,还要提提他对替萨斐尼的重大影响。[24]阿尔喀比亚德期望他们说,阿尔喀比亚德想要回到雅典,但条件是雅典人抛弃那个曾经流放阿尔喀比亚德的邪恶民主政权,建立寡头政权。如果他们满足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一条件,那么,他就会回到雅典,顺便带回替萨斐尼的友谊与支援。这些信息如阿尔喀比亚德所愿发挥了作用,“因为萨摩司的雅典士兵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对替萨斐尼有影响”,同时,有使者从萨摩司营寨离开,前来同他商讨情势。[25]
对于阿尔喀比亚德在发动寡头运动这一举措中所发挥的作用,修昔底德叙述得很清楚,却并未以之为重点。“但是,除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影响和承诺以外,在萨摩司的三列桨战舰舰长和雅典要人们也是出于自愿想要摧毁民主政体。”[26]大部分学者都强调是阿尔喀比亚德发起运动,忽视了修昔底德字里行间的微妙之意,而我们不应无视个中深意。[27]我们在此处读到的这句话,不是陈述事实,而是作出解释,解释为何萨摩司的全部雅典将领都会如此行动(修昔底德并未作出[-113,114-]区分,也未指出例外),解释萨摩司的雅典将领这样做的意图。细心读者早就指出,必须对修昔底德史书中的叙事部分与论说部分加以区分:我们应当把修昔底德之史书叙事当作金科玉律,但对修昔底德之史书论说则要保持开放态度。[28]在这件事上,我们特别应当审慎,因为在一处可以勘误的细节中,修昔底德明显错了。“雅典要人”是哪些人,我们只能依靠猜测;在萨摩司的三列桨战舰舰长是哪些人,我们也几乎完全不知道,只有一个人除外:斯代里亚的吕库斯(Lycus of Steiria)之子色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29]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萨摩司民众得知推翻萨摩司民主政体的阴谋之后,他们特别找到了色拉叙布卢斯,“因为他看起来特别反对阴谋家们”。[30]于是,色拉叙布卢斯及同僚召集水手,保卫萨摩司民主政权,镇压寡头起义。很快,他们迫使所有士兵,特别是与寡头们有所牵连的那些士兵们,发一个誓,誓忠于民主政权。[31]接着,刚刚向民主政体宣了誓的民主军队罢黜原任将军们,选举了可靠的民主派新将军们来替代原任将军们,其中就包括色拉叙布卢斯。[32]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接下来的进程中,他扮演了忠诚的民主派将军角色,并成为(-114,115-)反抗并打倒三十僭主寡头政权(Thirty Tyrants)、在雅典重光民主政权的英雄。在雅典,没有人比色拉叙布卢斯更配得上坚定民主派这一称号,也没有人比色拉叙布卢斯更不可能“迫切急于摧毁民主政体”,然而,修昔底德却把色拉叙布卢斯当作了“急于摧毁民主政体”之流中的一员。修昔底德能在这一个人的问题上出错,也就能在其他人的问题上出错。所以,我们绝不能径直接受修昔底德观点而不加质疑;我们应当详细考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实,在萨摩司热情招待阿尔喀比亚德并听信其说辞、愿意他回归雅典的那些人,色拉叙布卢斯是其中一员。[33]对于色拉叙布卢斯来说,至少,阿尔喀比亚德的提议不同于以往那种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愿望;同时,有理由相信,这样想的不止色拉叙布卢斯一个人。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阿尔喀比亚德回归、改变雅典政体的运动,既是由雅典流亡者阿尔喀比亚德为一己私利而提议的,也是由萨摩司雅典将领因为自身原因而选择接受的。但是,萨摩司的雅典将领们这样做的原因,显然不尽相同。在萨摩司雅典将领的内部,即便在较早阶段(也许早至412年11月),[34]我们都可以清楚分辨出立场观点彼此迥异的两个派别。一个派别属于色拉叙布卢斯。“他的观点从未变过”,修昔底德提到,“他们必须召回阿尔喀比亚德”。[35]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时候,色拉叙布卢斯至少是愿意接受对雅典民主政体加些限制的,因为阿尔喀比亚德最开始向萨摩司雅典要人们传达的信息就有这个意思。[36]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修昔底德对阿尔喀比亚德要求的记载足够精准确实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色拉叙布卢斯也准备好了要去推翻民主政权、代之以寡头政权。然而,考虑到色拉叙布卢斯后来的行动,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位伟大的民主英雄会这样做;故而可能的情况是,修昔底德的信息来源人搞错了这件事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阿尔喀比亚德这样措辞,但是色拉叙布卢斯和与他差不多的人回避这种措辞并且要求阿尔喀比亚德改变措辞。不管怎么说,阿尔喀比亚德在与跨海而来的萨摩司使团会谈时,没有再使用令人感到被冒犯的“寡头政权”一词;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应允回归雅典,表演奇迹——“如果雅典人(-115,116-)不保留民主政权的话”。措辞上的微妙改变很可能是真实的,同时,阿尔喀比亚德也准备向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属作出让步,政体将有所改变,但寡头政体不会到来。[37]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解释其措辞,让人无法不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早至412年11月开始,色拉叙布卢斯就已经准备好约束并改变雅典民主政权所拥有的权力。尽管色拉叙布卢斯已经清楚阿尔喀比亚德回归的条件,他仍然说服萨摩司雅典军队投票,保证阿尔喀比亚德免于受到起诉,重获职位,选举他为将军;同时,是色拉叙布卢斯自己亲自远渡而来,找到了替萨斐尼,把阿尔喀比亚德带回了萨摩司。[38]杰出的民主斗士色拉叙布卢斯何以行为如此?修昔底德的答案简单明了:“他把阿尔喀比亚德带回萨摩司,想着雅典安全的唯一指望就在于,阿尔喀比亚德能把替萨斐尼从伯罗奔尼撒人那边给争取过来。”[39]色拉叙布卢斯深信,如果波斯人与斯巴达人没有分歧,雅典就会遭遇灭顶之灾。要赢得战争,就必须赢得波斯;同时,他还相信,只有阿尔喀比亚德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拯救雅典意味着必须对民主政权有所限制,色拉叙布卢斯是情愿接受这一点的,尽管他会反对进一步背弃当前政治体制的一切举动。[40]
411年夏天,雅典四百人政权派遣使团前往萨摩司军队,从阿尔喀比亚德对该使团的回复中可以看出,色拉叙布卢斯可以接受的是什么样的限制措施。到那时为止,雅典四百人政权还没有接受阿尔喀比亚德,四百人政权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并非寡头政权的“恰当”人选。阿尔喀比亚德的前程取决于萨摩司的雅典部队,特别是取决于色拉叙布卢斯。叛国者阿尔喀比亚德能屈能伸,他不太可能违背色拉叙布卢斯的意愿,将条件细化为色拉叙布卢斯所不愿意见到的那样。事实上,这些条件如果不是多少按照色拉叙布卢斯的观点来塑造的,倒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阿尔喀比亚德要求解散雅典寡头政权的统治机构四百人议事会,他要求恢复过去民主政权的五百人议事会。但是,阿尔喀比亚德赞成缩减(-116,117-)公共服务开支,也不反对五千人议事会的统治。五千人议事会由部分公民组成,这些人所行使的基本权利之前是由完全民主的公民大会全体享有的。[41]
色拉叙布卢斯不愿意接受以四百人议事会为组织形式的寡头政权,但是他愿意限制民众权利,愿意限制民众获取报酬、行使全面政治职能等基本权利,他所接受的这种限制程度的上限大约是,他接受一个完全能够胜任且规模小至五千人的公民机构。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属于哪个政治类别?一方面,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不能把他叫作寡头派;没有古代作家称色拉叙布卢斯为寡头派,也没有与他同时代的雅典人会认为应当把色拉叙布卢斯称作寡头派。另一方面,色拉叙布卢斯也不是一位拒绝妥协的“激进”民主派,而现当代史学家传统上是把色拉叙布卢斯称为“激进”民主派的;如果色拉叙布卢斯是“激进”民主派,那么他就会拒绝任何限制民众权力的措施。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另一个传统标签“温和派”,这个标签对色拉叙布卢斯来说再适合不过。同时,考虑到上面所分析的色拉叙布卢斯的立场,“温和派”这一标签并非语焉不详,相反,它清楚反映了色拉叙布卢斯的政治立场。[42]
至于与阿尔喀比亚德谈判的另一个派别,修昔底德的描述就十分正确:他说,他们自愿力图摧毁民主政体,并建立寡头政权。关于这个派别在萨摩司的阴谋行动,修昔底德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斐林尼库斯和派山德。[43]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寡头派。事实上,这两个人还都有(-117,118-)民众煽动家的名声;在415年那几桩丑闻中,派山德扮演了重要的检举角色,而斐林尼库斯呢,很明显,是名成功的民主派政治家。[44]411年的时候,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这两位民主派政治家加入建立寡头政体的阴谋活动,究竟是因为信念更迭,还是因为私人利诱,我们无从分辨。吕西阿斯演说辞《对颠覆民主政体罪名的抗辩》发表于战后短短数年。这位雄辩家控诉派山德与斐林尼库斯协助建立寡头政权,概因二人对雅典民众犯下许多罪行,他们害怕惩罚。[45]这篇演说言辞偏颇,指控不详,但也多少算得上空穴来风,事出有因。415年,派山德热情洋溢去从事检举之时,定然结怨不少。在415年,派山德把调查搞成了普遍白色恐怖,提出解除刑讯逼供禁令。[46]意欲起诉派山德者众多,派山德有太多解释工作要做。至于斐林尼库斯,他在412/11年之前的职业生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到了412年11月,斐林尼库斯作为将军的表现肯定已经饱受争议。在此大约一年以前,斐林尼库斯独力反对其他所有将军的一致意见,从米利都退兵,不打海战,从而导致雅典人未能一举镇压爱奥尼亚叛乱。[47]这一决策的直接后果是抛弃阿墨基司,将他丢给了波斯人。从那年开始,雅典时运江河日下,雪上加霜。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些雅典人已经准备为此谴责斐林尼库斯了。[48](-118,119-)因此,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很可能因为迫切的个人困境而疑惧民主政体之存续,进而祈愿政体有所改变。
然而,无论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有什么样的目的,他们都没有加入色拉叙布卢斯加入的这场运动。这场运动令阿尔喀比亚德得以回归,波斯援助由敌转我,因而让雅典得到胜利。斐林尼库斯从一开始就拒绝阿尔喀比亚德回归,认为他根本无法做到应承之事,所以力图阻止阿尔喀比亚德归来。因此,斐林尼库斯是在阿尔喀比亚德和波斯援助之可能性完全消失之后,才加入阴谋活动的。[49]派山德则是在得知阿尔喀比亚德不会、也不能带来波斯支援这一情况之后,才加入其中,阻止阿尔喀比亚德参与他们日后的所有计划,带头尝试在雅典建立寡头政权。[50]斐林尼库斯和派山德自从加入这场运动后,就矢志不渝,热情洋溢,忠于寡头派的事业。修昔底德谈到斐林尼库斯的时候,说“对于寡头政体,他显示了超乎所有其他人的热情;……自从他表现出自己就是最可靠的那个人之后”。[51]至于派山德,是他提出了建立四百人寡头政体的动议,同时,根据修昔底德史书,在公开场合鼓吹抛弃民主政体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也是他。派山德还设计并领导了萨摩司的寡头派阴谋活动。后来,当雅典抛弃了寡头政权,派山德奔向了德西利亚的斯巴达军营。[52]尽管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很可能是出于纯粹的投机心理才选择寡头派政治立场,但是至少,给二人贴上“寡头派”标签也是实至名归。那么,在萨摩司的雅典要人,集聚起来决定同阿尔喀比亚德谈判的那些雅典要人,一开始就分别属于迥异的两个派别,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派别分别叫作“寡头派”与“温和派”。
在萨摩司的“三列桨战舰舰长和(雅典)要人们”给阿尔喀比亚德的回复,就是派遣代表前去与阿尔喀比亚德商谈。关于这些代表,修昔底德一个名字也没提到,但是派山德和色拉叙布卢斯很可能是代表团中的成员。[53]在那里,代表们得到了相同的承诺,说会给雅典(-119,120-)带来替萨斐尼、甚至是波斯大王的支持。这次,阿尔喀比亚德提出的条件——如果修昔底德重述确切无误的话——是“(雅典人)不保留民主政权,这样大王会更加信任他们”。[54]我们可以猜到,像色拉叙布卢斯这样的温和派对于阿尔喀比亚德最初措辞中的“寡头政权”一词定是反应激烈,因此,流亡者阿尔喀比亚德留了心,调整了措辞,这样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摩擦。温和派与寡头派对于“不保留民主政体”这一说法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温和派与寡头派对于“用寡头政权代替邪恶的民主政体”这样的说法可不会有什么不同解读。[55]当代表们回到萨摩司进行汇报的时候,那些派代表出去谈判的雅典要人们感到十分鼓舞。修昔底德仍然没有对这些人加以区分;修昔底德说,所有的雅典要人都热切希望将亲手掌控政府,所有的雅典要人都热切盼望打败敌人。[56]我们已经分清楚这两个不同派别,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在这两项希望之中,这两个派别各有侧重。
领袖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挑选“恰当人选”,共同盟誓,组建能够发挥作用的统治机构。[57]修昔底德将这个统治机构称为“蓄诺默下”(xynomosia),该词往往意味着阴谋团体,足以令人联想到“阴谋”一词的所有凶险卑鄙含义;修昔底德大约是有意为之,意正在此。但是,这个词本身也可能只是指具有政治目的而团结起来的一个盟誓集体。对于长久存在于雅典的政治党社,修昔底德使用的也是“蓄诺默下”这个词;色拉叙布卢斯在萨摩司组织起民主军队,他也提到,这些士兵盟誓忠于民主政体。[58]无论修昔底德意图如何,我们都不应当认为该蓄诺默下仅由少数阴谋家秘密组成。所谓的“恰当人选”很可能涵盖了普通士兵,因为雅典派遣了数以千计的重装步兵前往米利都作战,这些士兵彼时在萨摩司。[59]该蓄诺默下肯定包括了色拉叙布卢斯,因此,也就不可能只是个纯粹的寡头派阴谋集体。
蓄诺默下的下一步作为表明,秘密行事并非其重要特征。蓄诺默下把雅典(-120,121)在萨摩司的部队召集起来,“公开告诉许多人说,只要大家同意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并不再生活于民主政体之下,那么波斯大王将会成为大家的朋友,给大家带来金钱”。[60]如此,步兵和水兵们就知道了蓄诺默下成员所知道的一切。没有人使用“寡头政权”这个词,但这个词已经被阿尔喀比亚德自己主动抛弃了:在同蓄诺默下领袖私下谈话的时候,他已经不再使用“寡头政权”一词。如果普通民众不知道蓄诺默下某些成员内心深处渴望并计划建立一个持久寡头政权,那么蓄诺默下的某些内部人员如色拉叙布卢斯对此应当也是一无所知。
“暴民”,修昔底德指的是步兵和水兵组成的士兵大会,“就算此刻因为之前的事情有些不满,但也逐渐安静了下来,因为这些人对波斯大王要发的薪饷满怀期待”。[61]这次论争必定既热烈又冗长,修昔底德如此描述,未免偏颇且失于简单。从这段描述可以推出,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已经准备好允许叛徒阿尔喀比亚德复职,也已经准备好削弱他们所钟爱的民主政体——仅仅因为贪婪。[62]这段文本让人想起修昔底德是如何描写415年民众对西西里远征的热切拥护的。“此时,大部分民众和士兵都希望挣到钱,也希望为他们的帝国添上永不枯竭的收入源泉。”[63]无论普通的雅典士兵是基于什么理由曾经支持了西西里远征,晚至412年,面对如此无法设想、无法接受的提议,他们必定有其他更加强烈的动机去接受这种提议,而非仅仅出于贪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拯救城邦,或许还有他们自己与家人的性命问题;这是因为,雅典人实在无法想象,胜利又嗜复仇的敌人会不会像雅典人处置司基昂人(Scione)和弥罗斯人(Melos)那样处置雅典人。无疑,提到要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反对之音一定不绝于耳,遑论提及抛弃民主政体。可能的情况是,值得信赖之辈如色拉叙布卢斯多少平息了反对之音,还提醒大家说,吞下如此苦果,才有指望赢得金钱、继续战争、打败敌人。[64](-121,122-)
寡头革命领袖们会见了步兵与水兵之后,就同对此事比较友善的那些人一起,进一步开会商谈阿尔喀比亚德的提议。除了斐林尼库斯之外,每个人都赞成;只有斐林尼库斯一人全盘反对。他的演说辞逐条反驳了对阿尔喀比亚德提议的支持理由。他不相信波斯大王能够转向雅典一方,因为波斯大王的利益与和雅典合作所能得到的好处完全背道而驰。雅典人已经不再垄断爱琴海制海权,帝国的许多主要城邦也被伯罗奔尼撒人夺取,所以,比起以前来,波斯人要收买雅典人的友谊理由更不充分了。波斯人不信任雅典人,多年来,雅典人让他们非常不好受,但伯罗奔尼撒人却没有给波斯人吃过什么苦头。还有人定会指出,说雅典人若将民主政体转为寡头政体就能解决他们的帝国问题;叛乱城邦多数都在寡头治下,一旦雅典改弦易帜,这些城邦就会重投帝国,将来的叛变也可一并避免。对于帝国问题,斐林尼库斯用冷静的分析予以回应:帝国现实是,阶级斗争并不是首要问题。上述预测没有一个会成为现实,因为这些盟友没有一个“情愿被寡头政权或是民主政权奴役,他们情愿在原有制度下享受自由,无论他们原本使用哪种制度”。[65]甚至,这些盟邦会觉得被雅典上层统治甚至比被雅典庶民统治更加糟糕,毕竟,上层贵族从帝国之中获益最多,对所需的程序正义也不甚关心。[66]
话说回来,斐林尼库斯最重要的论据还是,阿尔喀比亚德不可信。阿尔喀比亚德才不关心寡头制或民主制;他想要对政体有所改变是为了让同党们制造可能,召他回归。如果阿尔喀比亚德计划继续实施,那么雅典就会被内争撕裂;当前,祖国殆危,不容生变。阿尔喀比亚德无法带来波斯人的支援,也无法劝回叛乱的盟邦,更无法制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叛乱。因此,此时此刻,斐林尼库斯看不到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些提议能够发挥什么作用。[67]
斐林尼库斯的建议是,拒绝阿尔喀比亚德提议,继续(-122,123-)旧有政策;但是具体来说,斐林尼库斯之所以拒绝,是因为这场革命运动所形成的路线看起来既无益又危险。如果接受斐林尼库斯的建议,那么寡头运动就会半途而废;有些学者据此认为,阻止寡头运动本身就是斐林尼库斯的意图,这是因为,晚至412年年底,斐林尼库斯都还没有转变立场、反对民主制度。[68]这种观点很难成立。一方面是因为,斐林尼库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迅速擢升为这一阴谋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说得更确切些,斐林尼库斯若是敌对派,那么他是不会被邀请参加阴谋活动私下会议的。与其说斐林尼库斯反对革命运动是出于其政体偏好,不如说他的反对必定是出于更加务实的理由:对阿尔喀比亚德的厌恶与恐惧。斐林尼库斯对阿尔喀比亚德的厌恶与恐惧何时产生、理由为何,我们没有资料。有人在法庭上指斐林尼库斯为谄媚之徒,说他是收人钱财的告密者。如果这指控并不全然是诽谤的话,斐林尼库斯肯定很招一类人烦:那种生活方式天然就招探子注意的人。[69]还有一个更有可能造成他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嫌隙的理由在于,斐林尼库斯作为一名民主派政治家,必定早在他去西西里之前就和他结了怨。以上所有,只是推测;但是,我们至少对于这一点不该有所怀疑:在萨摩司同寡头运动积极分子们会面谈话时,斐林尼库斯就已经将阿尔喀比亚德当作了危险的敌人。[70]也许有些人了解斐林尼库斯的个人动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人支持斐林尼库斯。不管怎么说,斐林尼库斯谁也没说服,会议还是决定接受阿尔喀比亚德的提议。与会者指派派山德带领使团,前往雅典,尝试召回阿尔喀比亚德,摧毁现有民主政权,赢得替萨斐尼。[71](-123,124-)
这样一来,斐林尼库斯发现自己陷入了最为危险的境地。他在会议上一力反对阿尔喀比亚德这件事情一定会很快传到阿尔喀比亚德那里去,同时,召回这叛徒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斐林尼库斯必须想个办法,阻止敌人阿尔喀比亚德回归;斐林尼库斯想了个奇招,同时也是个险招。斐林尼库斯给当时正在米利都的斯巴达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写了封密函,透露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具体计划,包括把替萨斐尼和波斯人争取到雅典一方来。他的借口,如前所述,是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敌意,还有这种敌意对他自己的安全所形成的威胁。很明显,斐林尼库斯还不知道阿尔喀比亚德已经从伯罗奔尼撒人的军营里逃走了,他还以为阿斯提欧库斯能够轻易制服雅典的流亡者阿尔喀比亚德。[72]因此,如果阿斯提欧库斯只是按照一般人的猜测、无视这封他对之根本无能为力的密函的话,那么这个计谋从一开始就会遭到失败。阿斯提欧库斯没有这么做,相反,他采取主动,前往玛尼西亚(Magnesia),会见替萨斐尼和阿尔喀比亚德。阿斯提欧库斯把密函的内容告知替萨斐尼和阿尔喀比亚德,藉此同替萨斐尼建立了密切关系。后来有传言说,阿斯提欧库斯在寡头运动中和在其他事务中的行动都是受到节度使替萨斐尼收买驱使的。[73]
阿尔喀比亚德的回应是,给萨摩司雅典要人写信,揭发斐林尼库斯的叛徒行径,要求雅典要人处死斐林尼库斯。斐林尼库斯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他弄错了阿尔喀比亚德的行踪,误判了阿斯提欧库斯的立场和行动,令自己很有可能在敌人阿尔喀比亚德被召回之前就被萨摩司的雅典要人们处死。当前,斐林尼库斯采取了更奇更险的招。他又致信阿斯提欧库斯,抱怨他背信弃义,但又提供了一次绝妙的机遇。斐林尼库斯准备替伯罗奔尼撒人想个办法,来摧毁萨摩司的全部雅典军队,因为萨摩司反正也没有长墙。斐林尼库斯又一次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解释为日益受到自身最大敌人的威胁。阿斯提欧库斯又一次将消息传给了阿尔喀比亚德。
斐林尼库斯以某种方法得知,阿斯提欧库斯已经背叛了他,行事完全与其诉求南辕北辙。[74]阿尔喀比亚德再次致信萨摩司,揭发斐林尼库斯的最新叛国行径;这封信差一点就及时到达了萨摩司。(-124,125-)斐林尼库斯又一次急中生智,想出对策。在被提起诉讼之前,斐林尼库斯告诉萨摩司军队说,他得到消息,将有敌袭;其实,正是斐林尼库斯自己秘密促成了这次敌袭。他告诉雅典人须加倍小心,建造防事,迎战敌军,雅典人照做了。很快,阿尔喀比亚德的信函到达,因为斐林尼库斯诡计先行的缘故,这封信函的作用被大大削减了。原本就有大批雅典人疑惧阿尔喀比亚德;这样一来,大家更有理由怀疑阿尔喀比亚德。雅典人深信,阿尔喀比亚德早就知道了伯罗奔尼撒人的计划,因为他一直就与伯罗奔尼撒人关系密切;雅典人还相信,阿尔喀比亚德在信函中说斐林尼库斯同样早就知道这个计划,定是出于私人愤怨。阿尔喀比亚德的信函没有对斐林尼库斯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反而使斐林尼库斯信誉飞升,因为是斐林尼库斯向雅典人精确通报了阿尔喀比亚德提及的危险。[75]
以上就是事情的始末。整件事情差不多都是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的,彻底理解其来龙去脉并不容易。有位学者的观点走向了极端,从根本上否认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这位学者假定,根本就没有这些信函往来,整件事情都是阿尔喀比亚德捏造出来、诋毁政敌斐林尼库斯的。如此极端的观点难以成立。[76]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诡异的书信往来确有其事;接下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试图理解涉事其中者的行为与动机。如果我们承认书信往来确有其事的话,许多问题就应运而生:精明如斐林尼库斯,为何会如此愚蠢,在渴望阿尔喀比亚德回归的同党面前公开说出他反对阿尔喀比亚德的计划来?勇敢果断如斐林尼库斯,为何因为恐惧就如此行动,一如修昔底德所描述?已经知道阿斯提欧库斯背叛了自己以后,斐林尼库斯为何还要给这位斯巴达海军主将写第二封信?如果阿斯提欧库斯没有接受贿赂、又不是为了私利的话,那么该如何解释他采取的行为?一种解释是,接受修昔底德的论说,承认斐林尼库斯行为的根本原因就是恐惧。但是,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斐林尼库斯要给阿斯提欧库斯写第二封信,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斐林尼库斯将此当成其精妙计谋的一部分——斐林尼库斯知道自己在这个计谋里将被背叛,也期待使用这个计谋去扰乱阿尔喀比亚德的回归计划。[77]不管怎么说,“计谋论”能够解释的问题太少,与(-125,126-)修昔底德的叙述也相互矛盾;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可知,斐林尼库斯对此是十分吃惊的。[78]
还有一种解释假定斐林尼库斯知道自己的第二封信会被出卖,他利用对方的背叛、使之成为其计谋的一部分;该解释还假定斐林尼库斯的动机中没有恐惧的因素。相反,“斐林尼库斯用此计谋,多少也是为了雅典利益而去影响军事与政治状况”。[79]斐林尼库斯在萨摩司的演讲真挚、明智、勇敢。因为演讲未能说服萨摩司雅典要人,斐林尼库斯就从言辞转向计谋,一定要拯救雅典人、不能让他们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在如此危殆的时刻陷入内争漩涡。阿斯提欧库斯被斐林尼库斯作为计谋的一部分,是因为阿斯提欧库斯没有经验、缺乏能力。“修昔底德叙事清楚表明,失败完全可能是因为阿斯提欧库斯性格缺陷和智识缺陷,不必拿什么凶兆来当借口,那是他恼羞成怒的部下所找的借口。”[80]这种解释也与修昔底德的论述相抵触。同时,尽管这种解释把阿斯提欧库斯的行为考虑进来,算是有所改进,但这种解释却用无能和愚蠢来解释阿斯提欧库斯的行为。阿斯提欧库斯固然无能和愚蠢,而无能和愚蠢也固然能够解释许多军事政治行为。但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诉诸如此万应理由之前,理应先穷尽别的可能。即便无能和愚蠢确乎对事件造成影响,我们也应当弄清楚,这个人在计谋失算时是如何考虑的。
在此,我给出对这诡异事件的另一种叙述。如果我们认定阿尔喀比亚德和斐林尼库斯为敌已久,如修昔底德史书所示,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理解,斐林尼库斯在萨摩司发表反对政敌阿尔喀比亚德归来之演讲的意愿乃至必需。[81]这样一来,斐林尼库斯的行为既是出于恐惧,也合情合理。斐林尼库斯在萨摩司会议的演说之所以收效甚微,大概是因为他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不睦众所周知,所有人都觉得斐林尼库斯对于阿尔喀比亚德素有不睦,因而难免存在偏见,故而没有把斐林尼库斯的演说当回事。接着,斐林尼库斯给阿斯提欧库斯写信,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忧虑。斐林尼库斯给阿斯提欧库斯写信,犯下了两个错误:他(-126,127-)不知道阿尔喀比亚德此刻已经不在斯巴达军营,并判断错了阿斯提欧库斯的反应。
斯巴达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已经无法再轻易搞定阿尔喀比亚德,尽管阿斯提欧库斯当然愿意保持这种能力。阿斯提欧库斯也无法忽视整个计谋成功、雅典叛徒阿尔喀比亚德成功将替萨斐尼笼络至雅典一方的可能。于是,阿斯提欧库斯去了玛尼西亚。阿斯提欧库斯揭露了信函内容,表明自己对于这次阴谋有所了解。这一举动定然重创阿尔喀比亚德,震惊替萨斐尼——替萨斐尼本来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无论替萨斐尼的真实意愿是什么,总之,他没有做任何承诺;同时,替萨斐尼得知阿尔喀比亚德在还没有同他说好的情况下就大方承诺会将波斯人笼络到雅典人一方,对于阿尔喀比亚德而言,那真是异常尴尬。韦斯特莱克说得对:“阿斯提欧库斯在这一幕中的动机和目标,修昔底德显然全然不知。”[82]韦斯特莱克的另一个观点也是对的,他说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的玛尼西亚之行不单单是为了传达信息,也是为了要讨论和商谈此次事件。我们得承认,阿斯提欧库斯是来“劝诫阿尔喀比亚德和替萨斐尼的……也是来制止替萨斐尼同雅典达成某种协议的”。[83]阿斯提欧库斯只需将计谋透露给替萨斐尼,然后说清楚他自己所知几多,阿尔喀比亚德同节度使替萨斐尼的关系就会立马急转直下,这无疑就能有效制止波斯人与雅典接近。[84]替萨斐尼很可能将阿斯提欧库斯的泄密行为视为友善之举,从而改善同他的关系。替萨斐尼报偿阿斯提欧库斯以金帛谢礼——东方政客习惯于此,不止一名希腊官员习惯于收受谢礼。也许,这就是贿赂传言的根源:协助先行、报酬后至的行为被曲解为钱财先行、收买服务的贿赂;但是,贿赂传言也很有可能是因为,阿斯提欧库斯和替萨斐尼在这次会见中建立了不错的关系,这也许能够解释阿斯提欧库斯后来为何并不怎么热心替伯罗奔尼撒舰队水兵争取更多薪饷。[85]
阿尔喀比亚德恼羞成怒,马上致函他的朋友们——萨摩司雅典要人们,告诉他们斐林尼库斯给阿斯提欧库斯写了信,要求他们立即处死斐林尼库斯。斐林尼库斯惊惶绝望,再次致函阿斯提欧库斯,告之其大可以现在过来萨摩司,袭击雅典部队,定然大获成功。修昔底德将此举视为斐林尼库斯求胜心切,丝毫没有(-127,128-)提到斐林尼库斯是否预见到计划会失败。现当代历史学家们认为,斐林尼库斯丝毫没有预见到计划失败,这不可能。无疑,既然第一封信被出卖,那么斐林尼库斯肯定会想到,第二封信的遭遇也会一样。在第一封信中,斐林尼库斯请求阿斯提欧库斯有所作为,他没有得偿所愿;同时,就算阿斯提欧库斯真能帮他做点什么,这也不会决定甚至逆转整个事件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斯提欧库斯的举动并没什么特别。然而,在第二封信中,斐林尼库斯请求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在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有所行动,还向他保证说这样能够一举终结战争。正如韦斯特莱克所说,“想到也许能够摧毁雅典在萨摩司的部队、从而加速战争结束,真是叫人心驰神往,阿斯提欧库斯没法不被这等好事吸引”。[86]斐林尼库斯陷入绝境,很可能指望阿斯提欧库斯不会像对待第一封信那样对待第二封信。可以推断,如果阿斯提欧库斯和斯巴达取得了胜利,他们就会表彰并回报那些帮助他们得到胜利的人。无论怎么说,斐林尼库斯笃定能够避免那因为死敌阿尔喀比亚德回归而必定要招致的厄运。雅典政治家能屈能伸,为了堂皇浮夸的个人野心、自身安全、事业精进而不惜背叛城邦,阿尔喀比亚德不是唯一一个。[87]
人们通常认为,斐林尼库斯的袭击邀约对于阿斯提欧库斯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很难拒绝;人们通常还认为,阿斯提欧库斯之所以拒绝这个邀约,不是因为替萨斐尼的所谓贿赂,就是因为阿斯提欧库斯“缺乏创见与想象力”,“孱弱”以及缺乏“外交手腕”,还有阿斯提欧库斯那“斯巴达式的审慎与疑惧”。[88]但是,如果阿斯提欧库斯当真信任斐林尼库斯的提议,当真信任一个他明知是叛徒的人,那么阿斯提欧库斯也未免太过愚蠢。要看清楚并对斐林尼库斯的“陷阱”感到害怕——韦斯特莱克是这么描述的——当真无需非斯巴达式的想象力、创见和勇敢,斯巴达式惯常的“审慎和疑惧”足矣。(-128,129-)无疑,这是阿斯提欧库斯不接受斐林尼库斯提议的主要理由;同时,对阿斯提欧库斯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无视第二封信。阿斯提欧库斯这样做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斐林尼库斯被逮捕并处决。但是,阿斯提欧库斯这样做的话,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并以之笼络替萨斐尼的计划就会继续顺畅无阻地实行下去,对斯巴达的战争事业形成威胁。于是,阿斯提欧库斯将第二封信的内容告诉了阿尔喀比亚德和替萨斐尼。[89]阿斯提欧库斯这样做,就能明确表明雅典仍然在准备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而这无疑将削弱阿尔喀比亚德同节度使替萨斐尼之间的纽带,并使得阿尔喀比亚德无法通过损害斯巴达利益来完成他笼络替萨斐尼至雅典一方的承诺。[90]
阿斯提欧库斯这样做,更深远的后果是,斐林尼库斯能够警告雅典人袭击在即,并完全抵消阿尔喀比亚德来信的作用。一方面,这不会给斐林尼库斯带来损害,反而会证实其警告,从而暂时巩固其地位。另一方面,这还会使雅典阵营更加不信任阿尔喀比亚德。[91]此事明显割裂了替萨斐尼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关系,寡头运动的阴谋家们最终派遣使团前往玛尼西亚与节度使替萨斐尼谈判之时,阿尔喀比亚德所承诺的一切已经变得不可能。与节度使替萨斐尼商谈破产,寡头派阴谋家们再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已经无利可图,斯巴达和波斯反而就此签订了新的条约。[92]斯巴达人的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与经验丰富、诡计多端者如阿尔喀比亚德、斐林尼库斯、替萨斐尼周旋,竟然能有如此成效,斯巴达人应该满意至极,别无所求。也许,阿斯提欧库斯根本未如你我所猜想那般天真简单。在雅典,反民主运动不再指望召回阿尔喀比亚德来反对斯巴达,也不再指望依靠波斯来援助雅典。无论是(-129,130-)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还是依靠波斯,雅典城邦内争都不可避免,而斯巴达也就渔翁得利了。又或者,最坚定的寡头派倘若成功颠覆了民主政权,也许他们会代表雅典提出斯巴达愿意接受的和约。无论是哪种情况,斯巴达都可谓境况上佳。
[1] 修昔底德(Thuc. 1.107.6)疑心,在457年塔纳格拉(Tanagra)战役之前,有一次推翻民主政体的阴谋;他还疑心(Thuc.6.60.1),就在415年西西里远征之前,还有一次建立寡头政体或僭主政体的阴谋。
[2] Iliad 2.188—278;参见芬利(M.I.Finley),《奥德修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Odysseus),纽约,1964年,第2版,第113页,第118—119页。
[3] Theognis 429—438.
[4] Nemea 3.40—42,载里奇蒙·拉悌摩尔(Richmond Lattimore)译,《品达凯歌》(The Odes of Pindar),芝加哥,1959年,第101页。
[5] Olympia 2.86—87,里奇蒙·拉悌摩尔译,同上,第7—8页。
[6] Plato,Republic 558C.
[7] Arist. Pol. 1317b.
[8] 关于这部小书《雅典政制》及其理念,参见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38—140页。关于该书成书日期,参见弗罗斯特(W.G.Forrest),《克丽娥学刊》,第52卷,1970年,第107—116页以及圣·克洛瓦,《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308—310页。
[9] Pseudo-Xenophon,Athenaion Politeia 1.1,3.
[10] Ibid,1.5.
[11] Ibid,1.9. 在1.8和1.9中,“优诺弥亚”,以名词和动词形式出现了3次。弗李希(H.Frisch)(《雅典人的政治制度》[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哥本哈根,1942年,纽约重印,1976年,第201页)提到,“该词较保守的用法仅仅是指古老淳朴的寡头式社会组织形式”。修昔底德(Thuc.1.18.1)将该词用于描述斯巴达政体。
[12] Pseudo-Xenophon,Athenaion Politeia 2.19.
[13] 西里(R.Sealey)(《希腊政治文选》[Essays in Greek Politics],纽约,1967年,第111—132页)曾争论说,“关于政府形式的不同观点”(第130页)对于革命者决策来说微不足道。然而,如果考虑到这些人的智识训练与德行教养、以及《雅典政制》所提及的证据的话,那么,西里的观点将难以成立。更改政治体制,并非一本正经的学生和智术师派的政治科学家玩的一个智识游戏,如佛罗斯特(《耶鲁古典学研究》[YCS],第24卷,1973年,第37—52页)似乎暗示的那样;更改政治体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的阶级斗争,这是道德上的必需。关于针对西里观点的逐条反驳,参见罗德斯(P.J.Rhodes),《希腊研究期刊》,第92卷,1972年,第115—127页。
[14] 关于hetairiai(党社)的讨论,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第204—205页(原书页码)。
[15] 参见上书,第3页。
[16] 这是汤森(R.Thomsen)的估算:《特别战争税》(Eisphora),哥本哈根,1964年,第162—163页。
[17] 参见上书,第2页。这一数字是一篇吕西阿斯演说辞(Lys.20.13)中的雄辩家所提及的,他说,这一数字是能够携带武器的人的数目,那么也就是重装步兵和骑兵的数目。
[18] Lys.19.42—43. 这篇演说日期被勘定为388/387年科林斯战争结束的时候,所以,其中一大部分应当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支出。然而,其中提到的一笔支出却是用于415至413年西西里远征。因此,这其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在早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支出的花费。
[19] Lys.21.1—5.
[20] Lys.19.45—48.
[22] Thuc.8.98—99.
[23] Thuc.8.47.
[24] Thuc.8.47.2.
[25] Thuc.8.47.2;8.48.1.
[26] Thuc.8.47.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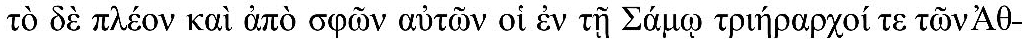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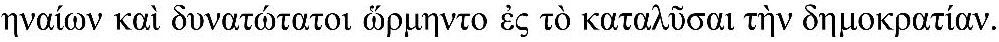
[27] 大部分学者都极为强调阿尔喀比亚德的作用。关于这类看法最有力的陈述,恐怕要算格罗特的(《希腊历史》,第8卷,第7页):“关于那短暂却几乎将雅典送入绝对毁灭之深渊的灾难,这就是它的元初萌芽:四百人寡头政体。提出这一建议的那个流亡者,就是把句列普斯(Gylippus)派到西西里的那个人,此人为此已经重创其祖国一次……”;关于这类看法最有力的陈述,恐怕也要算上麦格雷戈(M.F.McGregor)的,他说阿尔喀比亚德“阴谋策划了寡头革命,带来了四百人寡头政体”(《凤凰学刊》,第19卷,1965年,第42页)。布劳多(E.F.Bloedow)援引上文注释26所引用的一段话,强调萨摩司的雅典阴谋家们对于改变政体的迫切渴望(《重审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威斯巴登,1973年,第34页,注释213)。
[28] 参见圣·克洛瓦富有洞见的评论:“作为史家,修昔底德如此客观,连驳斥自己的论据材料都已准备充足。打个比方来说,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新闻栏目同其史书中的社论栏目是互相冲突的。社论作者并不总是与自己同声同气”(《历史学刊》,第3卷,1954—1955年,第3页)。罗德斯就修昔底德411年叙事作出的提醒同样相当贴切:“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在流放之中,好的方面是他不会直接被牵连到事件之中去,坏的方面是他只能依赖他人转述。在叙事之外,修昔底德加上了不少阐发论说。作为作家,修昔底德自豪于自己善于刺探表象、揭示真相的能力,他要看到底发生何事、人们所欲为何;同时,尽管我们完全可以假定修昔底德判断精明不错,但是我们在接受其意见时,仍然必须小心谨慎。人们当然可能怀抱一些未必愿意公之于众的目的;但是,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行动都有多重动机,以及尽管他们可能同时还有其他目的,他们所公开宣称的那些目的未必就全然不真。过分关注一个动机而忽视其他动机,这种做法就是值得怀疑的,最可信的古代史料来源沉湎于此时,我们应当怀疑它,当代学者沉湎于此时,我们也应当怀疑它。修昔底德对人们‘真实’所欲的论说是阐发论说,而不是事实记载,不同于他所记载的那些公开言论和公开行动;如果我们只接受修昔底德侦破的那些潜在动机,难免会误认事实真相,较之接受修昔底德所否认的那些表面动机,歪曲事实之程度可能更甚”(《希腊研究期刊》,第92卷,1972年,第115—116页)。
[29] 关于色拉叙布卢斯,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4页;以及戴维斯(Davies),《雅典有产家庭论》(APF,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第240页。
[30] Thuc.8.73.4.
[31] Thuc.8.73.58;75.
[32] Thuc.8.76.2.
[33] Thuc.8.76.7;81.1.
[3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67页。
[35] Thuc.8.81.1.
[36] Thuc.8.47.2. 此处及此卷中关于雅典政治的讨论,我都极大受益于麦柯伊(W.J.McCoy),“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Theramenes,Thrasybulus and the Athenian Moderates”),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
[38] Thuc.8.81.1;82.1.
[39] Thuc.8.81.1.
[40] 关于此刻雅典和萨摩司对于城邦安全暨拯救城邦之问题的关注, (安全),莱维(E.Lévy)有很不错的论说:《雅典在404年战败前夕:一部意识形态危机史》(Athènes devant la défaite de 404,histoire d'une crise idéologique),巴黎,1976年,第16—27页。
(安全),莱维(E.Lévy)有很不错的论说:《雅典在404年战败前夕:一部意识形态危机史》(Athènes devant la défaite de 404,histoire d'une crise idéologique),巴黎,1976年,第16—27页。
[41] Thuc.8.86.6. 关于五千人议事会的基本权利,参见本书第八章。争议的关键点在于,五千人议事会是独自享有全面公民权利,还是仅仅享有担任公职的资格。
[42] 有种看法认为,最好将411年的雅典政治分为三个派别来加以理解:激进民主派(或简单称为“民主派”),温和派(温和民主派,温和寡头派,或简单称为“温和派”),以及寡头派——这一看法肇始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包括贝洛赫,梅耶,以及布索特,并从此成为研判该时段局势的惯用思路。西里(《希腊政治文选》,纽约,1967年,第110—132页,特别是第127—130页)不仅否认温和派的作用,甚至否认温和派的存在,他认为,至少从政府的基本制度来看,是不存在这样一个“温和派”的。西里指出,阿尔喀比亚德配不上“温和派”这一标签,这是对的;西里还指出,塞剌墨涅斯也配不上“温和派”这样一个标签,这就不甚正确了。然而,对于色拉叙布卢斯应当贴上哪个派别的标签,西里却什么都没说,这是重大缺失。有证据能够清楚表明,一些雅典人明确青睐寡头政体,另一些雅典人无论如何也不想有任何改变,还有一些雅典人游离于这两种明确立场之外。显然,较之前两类人,第三类人的构成更为多样,彼此之间共性更少。有些人更为倾向于两种明确立场之中的某一种。但是,如果把这类人称为温和派,那真是方便、准确、明晰。如果真的不存在这样一个政治派别,那么我们也得制造这样一个概念出来。
[43] Thuc.8.48.4;49.
[44] 吕西阿斯(Lys.25.9)谈到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的时候,说他们开始是民众煽动家、后来转变成了寡头。派山德的情况确如吕西阿斯所言,他一直是喜剧诗人的常用笑柄(《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6页);同时,安多基德斯(And.1.36)将派山德和喀力克勒斯(Charicles)相提并论,提到在415年的时候,派山德和喀力克勒斯被认为是最为倾向于民众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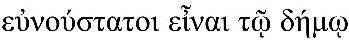 。关于派山德在415年的检举角色,参见And.1.27,36,43,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383—388页。关于派山德伪善、投机、自私,伍德海德为他进行了辩护,参见伍德海德,《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75卷,1954年,第132—146页。斐林尼库斯在411年之前的立场相对比较难以确定,但是,吕西阿斯将斐林尼库斯与派山德相提并论,将二人作为民主派转向寡头派之政治家的出名例子,恐怕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吕西阿斯的这一记载。《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9—60页)的谨慎结论合情合理:“可以确定的是,斐林尼库斯公共服务生涯漫长,任职记录(良好),那么,他贴上民主派的领袖标签、索得足够的民众信任而在411年以高龄当选将军,并非不可能。”
。关于派山德在415年的检举角色,参见And.1.27,36,43,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383—388页。关于派山德伪善、投机、自私,伍德海德为他进行了辩护,参见伍德海德,《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75卷,1954年,第132—146页。斐林尼库斯在411年之前的立场相对比较难以确定,但是,吕西阿斯将斐林尼库斯与派山德相提并论,将二人作为民主派转向寡头派之政治家的出名例子,恐怕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吕西阿斯的这一记载。《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9—60页)的谨慎结论合情合理:“可以确定的是,斐林尼库斯公共服务生涯漫长,任职记录(良好),那么,他贴上民主派的领袖标签、索得足够的民众信任而在411年以高龄当选将军,并非不可能。”
[45] Lys.25.9.
[46] And.1.36,43.
[47] Thuc.8.27.
[48] Thuc.8.54.3.
[49] Thuc.8.48.4—7;50—51;68.3.
[50] Thuc.8.56;63.3—4.
[51] Thuc.8.68.3. [译注:原文作8.63.3,应为笔误。]
[52] Thuc.8.67;73.2;98.1.
[53] Thuc.8.48.1. 修昔底德只说到  从萨摩司远渡而来。奈波斯(Nepos Alc.3)提到了派山德,说他是中间人之一,并以将军称呼他,但派山德并不是将军。派山德可能是名三列桨战舰舰长,尽管我们对此也没有证据。不管怎么说,派山德如此积极带头参与整个行动,那么他前去出任谈判代表亦是很有可能的(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67页,注释2)。之所以认为色拉叙布卢斯参与了整个行动,是因为他的职位就是三列桨战舰舰长,同时也是因为他一直与阿尔喀比亚德联系密切。
从萨摩司远渡而来。奈波斯(Nepos Alc.3)提到了派山德,说他是中间人之一,并以将军称呼他,但派山德并不是将军。派山德可能是名三列桨战舰舰长,尽管我们对此也没有证据。不管怎么说,派山德如此积极带头参与整个行动,那么他前去出任谈判代表亦是很有可能的(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67页,注释2)。之所以认为色拉叙布卢斯参与了整个行动,是因为他的职位就是三列桨战舰舰长,同时也是因为他一直与阿尔喀比亚德联系密切。
[54] Thuc.8.48.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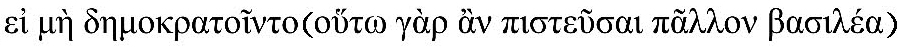 .
.
[55] 这是麦柯伊的看法,参见“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第24页。麦柯伊似乎是第一个发现阿尔喀比亚德措辞变化的人。
[56] Thuc.8.48.1. 这是我对于这段极难疏解之文本的理解。关于此处的文本训诂问题,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07—108页。
[57] Thuc. 8.48.2.
[58] Thuc.8.54.4;74.2.
[59]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06、108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67页,注释2。
[60] Thuc.8.48.2.
[61] Thuc.8.48.3.
[62] 梅耶(《古代历史》[GdA,Geschichte des Altertums],第4卷,第286页)捕捉到了这层意思:“对于那群听闻了阿尔喀比亚德要求和承诺的水兵来说,有人将要支付给他们大笔薪饷这一点是他们最为欢迎的。”亦可参见哈茨菲尔德(Hatzfeld),《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33页。
[63] Thuc.6.24.3.
[64] 麦柯伊,“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第25—26页。
[65] Thuc.8.48.5. 我同意布拉丁(D.W.Bradeen)(《历史学刊》,第4卷,1960年,第268—269页)所说,对于雅典帝国内部希腊人所持的态度,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修昔底德也是这样认为的,参见Thuc.8.64。相反的观点,参见圣·克洛瓦,《历史学刊》,第3卷,1954—1955年,第1—41页。
[66] Thuc.8.48.4—6. 对于这些观点,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0—113页。
[67] Thuc.8.48.4,7.
[68]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0页)说:“尽管斐林尼库斯后来成了寡头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但这是发生在寡头运动与阿尔喀比亚德脱离关系、转为敌对之后的;然而,考虑到实际情况,斐林尼库斯一直是全盘拒绝的。”亦可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34页),他提到,此时,斐林尼库斯是“积极的民主分子”。
[69] Lys.20.11—12.
[70] 这一点可以由斐林尼库斯在会谈之后立即写给阿斯提欧库斯的信予以证明。在这封信里,斐林尼库斯通知斯巴达海军将领阿斯提欧库斯,告知此次阴谋,提及阿尔喀比亚德角色,并为自己的变节行为找借口,说“与自己的敌人对抗,哪怕牺牲国家利益,这都是可以谅解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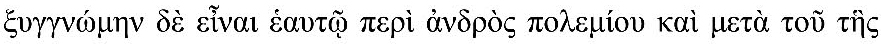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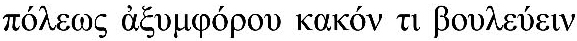 (Thuc.8.50.2)。但是,斐林尼库斯没有理由会知道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因为斐林尼库斯在萨摩司的演说而成为了他的敌人。就我们所知,斐林尼库斯这篇演说在那时还没有被告知给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也没有对这篇演说作出什么反应。证据似乎表明,斐林尼库斯和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敌意是早就存在的(而非因这篇演说而引发的)。
(Thuc.8.50.2)。但是,斐林尼库斯没有理由会知道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因为斐林尼库斯在萨摩司的演说而成为了他的敌人。就我们所知,斐林尼库斯这篇演说在那时还没有被告知给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也没有对这篇演说作出什么反应。证据似乎表明,斐林尼库斯和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敌意是早就存在的(而非因这篇演说而引发的)。
[71] Thuc.8.49.
[72] 韦斯特莱克(H.D.Westlake)(《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1页)对该论点讲得很清楚。尽管他有部分结论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从他对修昔底德文本详尽而富有洞见的训诂解读中获益良多。
[73] Thuc.8.50.3;83.3.
[74]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9—120页,提及了斐林尼库斯有可能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75] Thuc.8.51.
[76] 哈茨菲尔德持这样的观点(《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35—236页)。韦斯特莱克很好地驳斥了这种观点,《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99—100页。
[77] 这是格罗特提出的观点。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2—13页。有许多学者认同这一观点。
[78]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9—120页。
[79]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0页。
[80] 韦斯特莱克,《修昔底德史书人物列传》(Individuals in Thucydides),剑桥,1968年,第305—306页。关于阿斯提欧库斯之无能,更加详尽的论说参见《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2页。
[81] 韦斯特莱克断定,“修昔底德没有明说,也没有暗示说,斐林尼库斯此刻被反感阿尔喀比亚德的情绪所影响”(《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99页,注释1)。韦斯特莱克的观点没错,但我的观点是,修昔底德的叙述表明阿尔喀比亚德和斐林尼库斯之间存在宿怨是很有可能的。
[82]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2页。
[83]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2页。
[84] Thuc.8.56.2.
[85] Thuc.8.50.3;83.3.
[86]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1页。
[87] 为了证明第二封信是个计谋且是策划者故意为之,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1—102页)不得不作出了如下假定,但这些假定与事实证据并不尽相符。第一个假定是,斐林尼库斯给阿斯提欧库斯下达了攻击指令,这也许会带来伯罗奔尼撒人的失败,但修昔底德丝毫没有提到这个可能。第二个假定是,斐林尼库斯从一开始就想要警告雅典人受袭在即,催促雅典人修建防御工事。但是这与修昔底德的叙述正好相反。修昔底德的记载清楚表明,斐林尼库斯仅仅在得知阿斯提欧库斯正在反对他之后、阿尔喀比亚德第二封信函正在途中的时候,才警告雅典人受袭在即(Thuc.8.51.1;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9—120页)。修昔底德明显认为,斐林尼库斯如果不知道阿斯提欧库斯第二次背叛了他,定会对袭击保持缄默。
[88]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2—103页。
[89] Thuc.8.50.5. 修昔底德说,阿斯提欧库斯把信函给了阿尔喀比亚德,但是显然,我们不能不认为阿尔喀比亚德顺便将这封信的内容也透露给了替萨斐尼。
[90]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3页)认为,阿斯提欧库斯出示第二封信,是因为他相信阿尔喀比亚德甚于相信斐林尼库斯,也是因为他“确信阿尔喀比亚德仍然倾向于斯巴达一方,也并不想使计谋为雅典赢得替萨斐尼的支持”。但事实上,阿斯提欧库斯不仅了解阿尔喀比亚德的双重背叛行为,自己也收到了斯巴达政府处死叛徒阿尔喀比亚德的命令。如果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阿斯提欧库斯还相信阿尔喀比亚德仍然忠实于斯巴达一方的话,那么他头脑简单到都不配为斯巴达人了。
[91] Thuc.8.51.3.
[92] 关于替萨斐尼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分歧,参见8.56.2;关于使玛尼西亚使团及其结果,参见Thuc.8.56;关于斯巴达与波斯的新条约,参见Thuc.8.57—5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