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努赛(Arginusae)胜绩理应为雅典人带来慰藉,欣喜,团结。但是它没有。阿吉努赛战役成了苦涩、分裂、众怒的起源,是雅典历史中最为耻辱不堪的一页。在大捷之后不久,参与指挥阿吉努赛战役的6名将军被雅典民众控诉并处死,而他们为雅典民众赢得了如此胜绩;其余两名参与战役的将军逃过一劫,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召他们回雅典接受详细调查的传唤,自愿选择了流放。指控这些将军的罪名是他们没有能够营救战役的幸存者,而仅仅只救回了他们的尸体。从一开始,关于指控的合法性、调查与审判的程序、裁定判决、以及处罚手段的争议就沸反盈天。我们所掌握的古代文献资料没有一样是全面、冷静、令人满意的;所有这些文献资料也都无法得到完善的综合利用,来为这个事件构建一个可靠的透彻全貌。因此,在此呈现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解读。[1](-354,355-)
在阿吉努赛战役的最后一阶段,雅典舰队在海面上流移四散。战役开始时摆出的阵列已经很长,所用策略又要求侧翼舰船进行侧面包抄攻击,这进一步拉长了初始阵列。后来,右翼必定已经前行至列斯堡马里亚海角(Cape Malea on Lesbos)以西两英里的地方,封锁敌军,提防北逃。接着,一些雅典舰船将会向南方航行,追击溃散的敌军。雅典舰队左翼舰船也将向南追击败退的敌舰。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追击行动都如星流霆击,迅猛异常,因为摧毁尽可能多的敌军舰队事关重大。[2]雅典舰队所失去的25艘舰船中,除了13艘沉入海底以外,其余12艘舰船的残骸,[3]随残骸浮沉的幸存者1000多人,还有无数雅典划桨手尸体翻浮于涌浪之间,绵延至少4平方英里。[4]雅典人停止追击敌军之后,四散的雅典舰船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去营救幸存者,也没有打捞尸体,却急遽赶回阿吉努赛诸岛重整列队,商讨下一步。[5]
格罗特热切为雅典民众对阿吉努赛诸将的审判举动而辩解。格罗特谴责雅典将军(-355,356-)未能立即营救幸存者,也未能在回阿吉努赛岛之前营救幸存者:
在任何一支英吉利舰队、法兰西舰队、或美利坚舰队那里,都不会发生阿吉努赛大捷之后的那种事情。司令也好,水兵也好,取得了胜利又赶走了敌军,他们都绝不会匆促赶回自己的锚地,而把无人收拾的舰船残骸丢在海面上,任其翻滚,把无法自救、只能依赖他们来脱险的同袍留在涌浪上,任其自生自灭……
如果这些将军在告捷之后没有航行驶回陆地,首先就前去营救那些倾覆不沉的舰船,那么他们必定有足够的时间履行职责,营救所有还活着的船员……任何一支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舰队司令都必定视此为不可推卸之责任。[6]
要与雅典民众的阿吉努赛战役之痛产生切肤的共鸣,除了幸存者们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丧葬对于希腊人的重要性;对希腊人来说,葬得其法是一项极为紧要的宗教义务。对于许多雅典人来说,无法打捞亡魂如同无法营救生者一样令人震惊。我们如何来解读雅典将军与舰队司令如此昭然的麻木昏聩——他们无视险恶波涛之中的同袍,径直驶回阿吉努赛岛去开会?
如果能够注意到阿吉努赛战役与411年以来雅典人所从事的其他海战之间的诸多区别,那就也许能够多少理解将军与司令们的麻木昏聩。犬坟战役与阿卑多斯战役是在海勒斯滂的狭窄水域里打起来的,库济科斯战役(Cyzicus)是在阿尔塔奇海滩(Artaki Bay)的有限空间里进行的,诺提昂(Notium)战场的宽度不过是夹在斯巴达人的以弗所海军基地和雅典人的诺提昂海军基地之间的短短距离。在这些战役中,失败一方的海军能够快速回到陆地上,故而战役之后不会发生长时间、远距离的追击行动,舰队船只也不会星落四散。告捷一方的舰船能够轻易找到战后开会的处所,商定营救幸存者和打捞阵亡者尸体的有效方法,有充分时间来执行商定的计划,进而得偿所愿。在这些战役中,也没有一场是胜者在其他地方又展开战斗了的,因为在这些战役中,附近地区并无敌军。阿吉努赛诸将被控没有提前规划好(-356,357-)营救战役幸存者的方案。[7]可是,这样的批评似乎是不公正的。阿吉努赛诸将必定是认为,在之前战役中使用过的程序,同样适用于本次战役。如果我们确信阿吉努赛的雅典将军初始的战斗规划是要建立一种双重包围、以陷敌军舰队于诸岛和雅典舰船的封闭包围圈之内的话,适用之前数次战役的所用计划似乎并无不妥,长距离追击与舰船星落四散的情况似乎并不会出现。所有战斗都将在岛屿附近展开,营救工作应该是挺简单的。
这次战役的实际情况使得他们不能适用惯常的处理方法。敌军舰队远远逃逸,雅典人必定要予以追击。营救计划很可能不得不临危急就,但这就要求制定计划的将军信心充分,经验足够,在三列桨战舰舰长和同行将军之中已经树立起了个人威信。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在不假思索之间制定出新的营救计划,同其他舰船用旗语或其他信号语言进行沟通,这正是色拉叙布卢斯在库济科斯战役中的做法。[8]但是,色拉叙布卢斯在阿吉努赛战役中仅仅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指挥阿吉努赛战役的将军们都不具备色拉叙布卢斯这样的经验和威信——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来主持大局。因为阿吉努赛战役的联合指挥团体中没有一位可靠而有威信的人物,因此,雅典人不可以就此指责阿吉努赛诸将在战后麻乱中按照惯例行事,尽管这次确实不该依从惯例。
船舰都回到了阿吉努赛岛后,将军们召开会议,这时,很可能仍有时间组织营救生还者与打捞阵亡者行动,多少也能够取得一些效果。但此时的战略情势不同往常。在以往几次战役中,敌军或兔脱成功登陆,或被涤荡于海,或战事告捷——无论敌军是哪种情况,雅典人都无需再采取任何举动——然而,阿吉努赛战役的结束留下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在阿吉努赛诸岛西北不过12英里之外,仍然停泊着一支50艘舰船的斯巴达舰队,在密提林(Mytilene)封锁着刻农舰队。只要斯巴达的舰队司令埃迢尼库斯(Eteonicus)得到斯巴达主舰队战败的消息,他就一定会即时逃跑。如果埃迢尼库斯逃向开俄斯、加入阿吉努赛战役的逃亡舰只的话,那么开俄斯的斯巴达舰队规模将超过90艘三列桨战舰,与莱山德在诺提昂取得胜利的那支舰队(-357,358-)同等规模,很快,这支舰队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消解阿吉努赛大捷的战果。这样一来,雅典将军完全有理由着急尽快前往密提林,切断埃迢尼库斯舰队的去路,并摧毁埃迢尼库斯舰队。营救生者并打捞亡魂,追击埃迢尼库斯舰队,将军们所面临的这两个任务都非常重要,但却互相冲突,争论很快爆发在商讨会议之中。狄奥梅冬力促整支舰队回去营救生者并打捞尸体。伊拉司尼德(Erasinides)曾与刻农在密提林共事,还曾逃过封锁溜回雅典通风报信。[9]因此,伊拉司尼德会特别注意到密提林的斯巴达舰队,还会建议整支部队立即赴敌,这自然毫不稀奇。色拉叙卢斯提出折中方案,赢得了大家的认同:舰队的一部分舰船留在此地,营救生还者、打捞阵亡者尸体,同时,舰队的其余舰船前往密提林。8名将军每人从自己的分舰队中拿出3艘舰船来,再加上原来在中心列队中占据主要位置的23艘舰船,也就是萨摩司来的10艘舰船加上载有雅典舰队副将和舰队长(navarchs)的13艘舰船,组成营救行动组共47艘三列桨战舰。对于那12艘仍然浮在浪尖的雅典舰船残骸来说,每艘残骸差不多对应了4艘舰船营救力量。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尽管只是三列桨战舰舰长,也受命执行该项任务;同时,所有8名将军,包括狄奥梅冬,则领着余下三分之二的舰队前往密提林。[10]
当代学者批评阿吉努赛诸将,认为他们不该径自驶离战场,将营救任务交给下属,还就此提出了将军们的一系列动因,例如,他们想要投身进一步战斗,邀名射利,而不是把自己困在营救任务这种无法提供名利的行动里;例如,天气转坏,营救危险;又例如,任务危险,失败可能性很高,将军们既怕危险,又怕完不成任务,还怕因为牵扯上营救失败的罪名而见诟于政敌,因此想要尽快摆脱这个危险的任务。[11]政治动机方面的指控没有什么基础。8名将军中只有4人——狄奥梅冬、伊拉司尼德、小伯利克里、色拉叙卢斯——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党”,[12]但他们(-358,359-)总还是不如色拉叙布卢斯更是个民主党:色拉叙布卢斯是他们所谓的政敌,那个于411年与色拉叙卢斯一起在萨摩司拯救民主政权的色拉叙布卢斯。[13]此外,在诸位将军之中还有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他曾与塞剌墨涅斯紧密协作,建立五千人议事会。[14]如果把与阿尔喀比亚德合作视为党派试金石的话,我们就必须看到,色拉叙卢斯部队与阿尔喀比亚德部队最开始的那些不快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还必须看到,色拉叙卢斯与阿尔喀比亚德合作、也同塞剌墨涅斯合作,于409年到407年之间在双海峡地区肃清敌军,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抵牾不快。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余的三列桨战舰舰长、连同海军舰队副将和舰队长一起,也都共担着风险,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分享同样的命运。我们不知道这些舰长、舰队长、副将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与那些更加有名的同袍是否持有同样的政治立场,从属于同样的政治派别。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时段的一点儿政治情势,不足以说服我们认为,阿吉努赛诸将在作决策时的主要考虑是派别政治。
我们也不知道,追逐荣誉的过分愿望和拒绝承担艰险任务的心态在此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是要充分理解阿吉努赛诸将的决定,并不需要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动机。雅典人既然要去追击敌军,那当然要派出在之前战役中表现出色的舰只和将军。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阿吉努赛战役的话,留下来进行救援行动的大部分舰船在战斗中处于中间的阵列,而中间阵列在战役中几乎没有经历什么战斗。如果有人还要提出营救和打捞行动离不开指挥官领导的话,那么将军们也完全可以回答说,他们将任务布置给了之前曾经担任最高指挥官的人来做这件事,这其中就包括了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他们早已多次证明自己的才干。[15]
阿吉努赛诸将作出决策、分配任务,然后自己前往密提林,将营救任务留给他们所指派的军官。[16](-359,360-)舰长们向船员们下达命令开始行动,但遭到据违。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士兵们“因为在战斗中受了苦,同时也因为风浪太大,据理反对去打捞尸体”。[17]狄奥多罗斯写作这段历史时所依据的来源很可能记载下了士兵们的具体言辞,这是因为,士兵们被漫长战斗消耗得精疲力竭,被不断升级的风暴吓得心神不宁,难免多少要粉饰一下自己的疲乏和恐惧,断言已经无人生还,而打捞尸体不应负上人命风险。也许这就是狄奥多罗斯自始至终只提及尸体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舰长们根本无法驱使士兵们行动,然后风暴渐强,海上作业已然完全无法进行下去。风暴初现恶劣端倪这一情况必定要被士兵们屡屡提及,用来为营救任务和打捞任务的失败辩护,但格罗特同时质疑了这两者:“存在强有力的可推定证据,该证据能够证明,那天的风暴并不足以令有责任心、认真勇敢的希腊海员退却。”[18]
格罗特的举证是这样的:埃迢尼库斯得到雅典胜利消息的时候,从密提林安全驶往开俄斯,“顺风”而行。[19]密提林和开俄斯之间风偃浪止,这条航路距离阿吉努赛并不远,阿吉努赛岛那边又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风高浪急、连营救工作也不能开展呢?然而,格罗特在此处揭示的矛盾并不存在;事实上,有证据能够证明阿吉努赛附近的风暴是兀自出现的,并进而阻止了营救任务和打捞行动。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各自都叙述了风暴渐长的情况。色诺芬记载了战事前夜的大雨和雷暴,这令卡利科拉提达(Callicratidas)没法进行攻击;色诺芬还提到了风和“大风暴”,这令雅典人无法营救同袍,也无法在密提林攻击埃迢尼库斯。根据色诺芬的叙述,我们知道,刻农是在“敌军溜走、风偃浪止”[20]之后才从密提林航行至阿吉努赛会师(-360,361-)的。狄奥多罗斯则告诉我们,战斗前夜大风狂作,还提及了风暴渐长,令雅典水兵无法进行营救任务,也无法前往密提林,迫使意欲前往密提林的分舰队回到阿吉努赛;最后,狄奥多罗斯还提到,疾风狂作,尸体和船骸向阿吉努赛岛的南边和东南边漂流,一直漂到佛该亚(Phocaea)和叙姆(Cyme)。[21]通过这些证据,我们能够轻易复原这一系列事件的真相。那时正处于风暴季节,粗风暴雨如家常便饭。有些风暴泥于局部,几英里之内天气全然不同。战斗结束不久,西北偏北方向涌起密云疾风,逐渐加强。在疾风暴雨到来之前,雅典舰队仍然在追击敌舰,报信艇逃过追击,抵达密提林,向当时正在密提林的埃迢尼库斯通报了战况。埃迢尼库斯即时启航前往开俄斯,得渐偃渐止的清风相助,成功渡过了马里亚海角的狭窄通路,而此时,雅典人可能还在阿吉努赛岛上开会。而当雅典人出发前往密提林追击敌军时,风暴已经大到令他们不得不折返阿吉努赛岛的地步了。同时,在阿吉努赛诸岛上,风暴阴沉低霾,吓得船员们惊惶沮丧,而浪已经翻涌到不太适合三列桨战舰下海了。很快,风暴大作,讨论已无意义,营救也绝无可能。风暴自北向南而来,首先在密提林有所缓和,刻农趁机出发,前往阿吉努赛岛。刻农在阿吉努赛附近才与大部队会师,而此时大部队趁风浪渐止刚刚离岸。这样的事实重建符合所有证据。此外,毫无疑问,是这场风暴的规模与发生时间导致了战斗之后的两项任务的失败;毋庸置疑,舰长们合理执行了命令,但舰长们没有完成任务,先是士兵们违拒命令,再是风暴已然不允许继续行动了。
如若我们对事实的分析足够冷静、公正、信息完备的话,那我们就不难知道,将军们与舰长们都不应为未能营救生者、打捞死者而受到责难;但是,极少有涉事者能做到冷静和公正,而能全面获悉情况者就更加寥寥。舰长的指挥遭到士兵违拒,阿吉努赛诸将并不在场。(-361,362-)阿吉努赛诸将中的一些人定会确信这是舰长的错,他们纪律不严,没有严格管束自己的士兵。而诸如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之类担任过将军、战绩彪炳、能够在战斗中随机应变的那些舰长,则会埋怨阿吉努赛八将军,埋怨他们漫长的追击敌军之旅,埋怨他们没能在回到阿吉努赛岛之前就营救伤者归来。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之辈大概也怨恨接到的这些任务;这些任务最终是没有完成的,而这一失败很可能早已被舰长们所预见到;然而,舰长们仍然势必要为营救任务的失败承担责难。风暴止息后,不难想象,将军们在两支雅典舰队会师时得知营救任务没有完成时,该是多么的诧异、沮丧、甚或愤怒。我们也不该忘记,军官们和船员们失去了同袍,他们的悲痛之情不轻于其他任何一个雅典人。所有人都在恼怒,都认为自己无罪无辜,都准备为此责备他人。会师之时,将军和舰长必定有为此恼怒不已,互相指责。
无论情况如何,风偃浪止之后,会师后的整支雅典舰队再次起航前往密提林。还没走出多远,雅典舰队遇上刻农,他正要前来报告一个消息:埃迢尼库斯带着50艘舰船向南逃走了。这是个坏消息,但是将军们还不愿就此接受未能在海上驱逐一切敌方海军这一事实。雅典舰队继续前往密提林,在那里短暂停留,接着尾随斯巴达人的航迹前往开俄斯。但斯巴达人已经安然在港,明智地拒绝出港应战。雅典人不得不接受既有胜绩,驶回他们自己在萨摩司的营地。[22]将军们当然有理由为他们在阿吉努赛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这一胜利的喜悦难免被营救行动和打捞任务的失败所冲淡,也定会为无法对敌军造成致命一击——就像在库济科斯那样——这一事实所冲淡。雅典将军们没有能够将敌军舰队完全驱逐出海上,留下了足以成为一支舰队之核心的大量舰船,而这些舰船势必很快再起战端。
阿吉努赛战役诸将在萨摩司数次劫掠突袭了敌方领土,[23]但他们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向雅典民众写份战报。营救任务和打捞行动的失败无法(-362,363-)隐瞒,问题并不简单。第一个反应是,实事求是,如实叙述,包括向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等舰长布置营救和打捞任务、以及舰长们未能完成任务这一事实。[24]然而,小伯利克里和狄奥梅冬劝服将军们,不要提及营救生者和打捞死者的任务,径直怪罪天气不佳即可。[25]将军们接受了小伯利克里和狄奥梅冬的建议,这一点都不难理解。这是因为,一份战报,倘若要将过错归咎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的话,一定会引起争议,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受了指责,也一定会调转矛头将过错归咎于将军们。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都是了不起的雄辩家,有权势的政治家,朋友和支持者众多。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为敌实在最危险不过。[26]结成统一战线则要好得多,别谴责什么人,归咎于自然力量就可以了。无疑,问题和抱怨仍然是少不了的,但如若将军们和舰长们的证词一致、没有破绽的话,定然天衣无缝。
雅典人喜迎捷报,投票通过嘉许令,嘉奖阿吉努赛诸将,但与此同时,雅典民众获悉生还者没有得到营救、阵亡者没有被打捞上来,也是十分愤怒的。[27]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回到萨摩司后,就匆匆赶回了雅典。[28]无疑,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意识到他们正处于那个最危险、最脆弱的位置,一旦有需要,他们就迫切想要为自己进行辩护。没有证据表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受到指控,因为在雅典,没有人知道是他们获得了这项任务,但却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同时,也没有理由相信,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责难了将军们,甚至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公开说过什么话。[29]然而,不满情绪仍然出现,人们将过错归咎于将军们。当骚乱与指控的消息(-363,364-)传到萨摩司时,将军们确信,一定是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把事情说出来的。因为确信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已经背叛了攻守同盟,阿吉努赛诸将重新写信给公民大会,在这次的信里,将军们揭露说营救生者和打捞尸体的任务是交给舰长们去做的。[30]
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这个举动“是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的原因”,因为这个举动使得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等显要政客转友为敌,成了阿吉努赛诸将“愤怨的控诉者”。[31]然而,麻烦无论如何逃不掉了。毕竟,有数以千计的雅典人对此约略知晓,总会把事情说出来。无疑,许多人并不明白为什么不去进行营救行动,他们迟早要问责于将军们、舰长们、甚或是所有人。无论将军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人们都会低声质疑,私下抱怨,乃至提起正式的控诉。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同意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一个事实——将军们确乎改变了初始计划。新写来的信件激怒了塞剌墨涅斯及同党,迫使他们为自己辩护。既然把没有营救行动完全归咎于风暴已经不可行,塞剌墨涅斯和同党只好将矛头指向将军们。塞剌墨涅斯等人并未否认风暴的重要性。[32]相反,他们声称,他们这些舰长在接到命令的时候,风暴已经强到无法出海执行命令的程度了。狄奥多罗斯还告诉我们,塞剌墨涅斯等人对自己的辩护令公民大会迁怒于阿吉努赛诸将。[33]所以,公民大会肯定要谴责将军们耽搁延误,不及时下达命令给舰长们;公民大会还可能指责将军们追击敌军漫长又徒劳无功,没有在回到阿吉努赛岛之前就实施营救计划,且在商议讨论中浪费了太多时间。这样的任何一种指责,产生的效果无疑不外是保护舰长、责备将军,但这些指责未必不是实情实意。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担任将军时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不是阿吉努赛诸将中的任何一位可以比拟的。(-364,365-)但是,塞剌墨涅斯等人因为政治考量而不得不担任低级职务,恼于上司驽钝不堪,怒于战场失败,同时塞剌墨涅斯等人还确信,只要他们自己亲自上阵,所有这些力不逮心和战场失败都将荡然无存。对于塞剌墨涅斯等刚刚取得一连串不间断的辉煌海上胜绩的人来说,这么想难道不是最正常不过了吗?
塞剌墨涅斯等人的自辩和对阿吉努赛诸将的控诉立时产生了作用。公民大会投票罢免了阿吉努赛8名将军的职务,命令他们回到雅典来接受控诉。[34]阿里斯托根尼(Aristogenes)和普罗托马库斯(Protomachus)选择自愿流放,“他们害怕民众的怒火”。[35]阿里斯托根尼和普罗托马库斯两人的逃跑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罪,仅仅只能表明他们的神经比其他6名将军更为脆弱,又或者是他们对雅典民众更加不信任。但是,阿里斯托根尼和普罗托马库斯两人的逃跑无疑仍然多少令人对回到雅典接受审判的那6名将军产生偏见。将军们的遣返程序似乎是离任审查程序(euthynai)——雅典的所有公职人员在其公职任期结束都必须接受的。该程序具体包括经济审计和履职调查两个部分。[36]
第一个进行自我辩护的将军是伊拉司尼德,但是雅典民众对他的陈述并不满意。那时的头号民主派政治家、双鸥帛津贴(diobelia)的负责人阿奇德慕斯(Archedemus)把伊拉司尼德带到民众法庭上,控诉伊拉司尼德滥用公款、指挥失误。民众法庭判决伊拉司尼德有罪,并把他投入监狱。[37]从所有将军中首先特别挑出伊拉司尼德这一位将军来进行审判,有些学者在这个现象中看到了其背后的政治动机。这些学者认为,攻击伊拉司尼德的做法是民主党人的策略,为的是牺牲伊拉司尼德一个(-365,366-),挽救其他人。[38]然而,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民主党人会想去攻击伊拉司尼德,因为伊拉司尼德几乎是阿吉努赛诸将中最有可能自命为民主派的一位。[39]同时,一个民主党人又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去拯救那样一些人——比如说,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四百人议事会成员之一,五千人大会的主导人物之一?如果不是上述理由,那么,之所以选择攻击伊拉司尼德,最可能的理由是伊拉司尼德自己有其独特的弱点。阿吉努赛诸将回到雅典后不久,开会商议的情况和伊拉司尼德建议整支舰队不顾生还者性命前往密提林的事情就已经广为人知。阿奇德慕斯单独攻击伊拉司尼德,很可能是因为阿奇德慕斯相信这个流言,认为只有伊拉司尼德一人是有罪的——或者至少是比其他将军罪愆更大的。或许阿奇德慕斯是要确保,一定有人要受到惩罚;或许阿奇德慕斯是希望,单独拎出伊拉司尼德可以迫使他指证其他将军。无论这些推测具有何种价值,要理解阿奇德慕斯的行动,我们其实无需去创造一些背后的政治动机。
接下来,另外5名将军来到五百人议事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这5名阿吉努赛将军似乎刚刚完成其初步自辩归来,而他们的自辩理据应当是风暴。[40]如果对阿吉努赛诸将返回雅典后的雅典情势作一番考察评判的话,阿吉努赛将军们就会发现,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并不是导致他们被起诉的信息源头,因此,对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继续怀有抵触和敌对情绪似乎也没有必要。如果继续抵触敌对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那么他们就没有机会重新施行之前的统一战线策略。在某个提莫克拉提斯(Timocrates)的动议下,五百人议事会投票将将军们投入牢狱,还押公民大会接受审判。[41]在那次公民大会上,几个雅典人——其中领头的就有塞剌墨涅斯——控诉将军们应当为生还者的阵亡承担责任。塞剌墨涅斯和一些人论称,应当迫使将军们就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营救遭遇海难的雅典船员作出解释。为了举证说明将军们是唯一应当为此负责的人群,塞剌墨涅斯念出了他们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们仅仅将此归咎于风暴而无他。[42]
将军们已经收敛羽翼,因为他们不再认为是塞剌墨涅斯等人出卖了他们;那么,此时此刻,塞剌墨涅斯及同党为何仍然采取攻势、而不退守之前与将军们的统一战线、力争不责失任何一人呢?人们总是希望在派别政治中找寻政治动机,但是正如我们所见,政治动机(-366,367-)在此没有说服力。[43]我们应当来看更加基本、更加普适的人性动机。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党十分愤怒,而且惊恐。在第二次向雅典写信时,将军们将自己肩上的责任推给了舰长们,令舰长们境地危如累卵。在舰长们看来,将军们第二次写回雅典的那些信件含义虚假,同时,那些信件本身就意味着之前的同盟默契就此破裂,破裂得心照不宣,甚或几近直白。愤怒,阐明自身清白和让过失者得到应有谴责的决心,还有报复背叛同盟者的热望,一齐涌上舰长们心头,演化成了他们接下来行动的动机。除此之外,舰长们还有理由害怕,单单归咎于风暴恐怕是不足以为自己进行有效辩护的。只要事件的细节没有被人知晓,单单归咎于风暴是有可能的。然而,到了现在,雅典人已经知道,营救伤者、打捞死者的任务是交给舰长们的;雅典人也已经知道,在阿吉努赛所召开的会议、会议中各人的立场、还有会议最后的决议。雅典人听闻这些情况,或许还了解了更多,雅典法庭已经据此判决其中一名将军有罪,五百人议事会则起诉了其他的将军们。另一方面,塞剌墨涅斯和其他舰长把矛头指向将军们,成功转移了雅典人的怒火。事已至此,为了自己的信誉考虑,为了不至于令自己也被和将军们一起送上审判台,这时的塞剌墨涅斯和舰长们不太可能再给事情的整个经过编个别的版本。
塞剌墨涅斯及同党的控诉起到了很大作用。为阿吉努赛将军们辩护的声音被打断,被众人的呼喊声所淹没,将军们自己甚至没有得到法律应许的完整自辩时间。[44]塞剌墨涅斯等人的攻击迫使将军们改换自辩说辞。在这个时候还不说出细节,只是泛泛而谈风暴,这么做已经不大可能了。因为舰长们已经将矛头转向将军们,将军们就别无选择,只能直接指出,营救伤员、打捞死者的任务是交给舰长们去做的。将军们驶去追击敌军,将营救和打捞任务交给有能力的军官——就是曾经担任过将军的那些舰长,比如说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等人:“如果真要为了营救任务这件事情怪罪什么人的话,那也不能怪罪别人,只能怪罪那些接受这项任务的人。”尽管如此,将军们仍然拒绝怪罪舰长们——那些控诉他们有罪的舰长;相反,将军们仍然坚称“是狂风暴雨(-367,368-)阻止了营救任务”。[45]为了论证这一点,将军们提供了领航员和其他编入舰队的船员的证词。这样温和的自辩真是令人钦佩、信服和感动。将军们的言辞前后一致,貌似可信,富有同理心的中立听众是能够相信这些话的。将军们此前之所以不说出营救任务是交给了舰长们,是因为阻止营救任务的只有暴风雨这一个因素,他们确信营救任务交给谁这种细节与控诉是没有关联的。许多雅典人如此确信将军们的说辞,甚至提出为将军们出保释金,整个公民大会也差不多要被将军们说服了。[46]在那个关键时刻,夜晚降临,机运就以这样的方式干预了人间的事务。那天时间已晚,没有时间完成清点投票票数的工作。于是会议决定将行动推迟到下一次公民大会召开的时候。与此同时,五百人议事会将起草一份草案,以此草案确定审判程序。[47]
晚间降临导致会议中断,这还不是命运的最后一次干涉。在这次公民大会召开后不久,雅典人要依例举行伊翁胞族祭(festival Apaturia),具体时间应当是406年10月中旬的某天。[48]举行祭典的“胞族”(phratriai),或曰“手足”,是历史悠久、备受尊敬的宗族组织。所有亚狄珈家族都要聚集到一起庆祝伊翁胞族祭,持续3天左右。在伊翁胞族祭上,需要登记注册头一年出生的男婴,同时还要庆祝头一年缔结的婚姻和一些青年男子年及弱冠。“因此,伊翁胞族祭主要是家族祭典——关乎新生、成人、婚姻。”[49]一般来说,节庆的气氛是欢愉活泼甚或喧闹狂欢的,但406年的这次伊翁胞族祭并非如此。家族和胞族汇聚到一处,阿吉努赛战役伤亡造成的区别是如此明显,实在令人触景落泪。许多人肯定认为,致使他们失去手足的并非敌军屠刀,而是雅典人自己的疏忽、胆怯。雅典再次召开公民大会来讨论阿吉努赛诸将命运,这时,阿吉努赛阵亡者的许多遗属也参加了公民大会,他们身着衰絰;同时,许多遗属剪发要求(-368,369-)报复那些没能营救战役生还者的人,“请求公民大会,惩处竟敢让慷慨就义、为国捐躯之士没能得到安葬的那些人”。[50]
色诺芬谴责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说是他们雇佣了一些人来冒充阿吉努赛阵亡者的遗属,玩弄诡计、激起民众对阿吉努赛诸将的憎恶。[51]一些学者接受了色诺芬对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的谴责。[52]但我们很有理据拒绝色诺芬的这一谴责。狄奥多罗斯认为这些缟衣素服者确实是阿吉努赛战役的遗属,且丝毫没有提及塞剌墨涅斯对这些人的行为有何影响。但狄奥多罗斯的这段叙述意义有限,一方面是因为狄奥多罗斯在此叙述简略疏阔,一方面是因为狄奥多罗斯在其史书内提到塞剌墨涅斯时态度一以贯之,十分友善。在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吕西阿斯的演说。吕西阿斯演说对塞剌墨涅斯少有褒扬之词,但关于塞剌墨涅斯与阿吉努赛事件,吕西阿斯却从来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遑论谴责。[53]最后,在406/405年左右,即便塞剌墨涅斯有如此诡计,也没有多少人对此有所怀疑,因为雅典民众开始憎恶那些控诉阿吉努赛诸将的人的时候,他并没有遭到检控,同时,在接下来的405年春天,塞剌墨涅斯就被选举为将军,他依然受到雅典民众的欢迎。[54]要进行如此欺诈,未免愚蠢又危险。一方面,真正的阵亡者遗属——无论如何总有一些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辨认出那些假扮的遗属来。另一方面,此时的雅典,群情慷慨激愤,民意瞬息万变,没人知道谁会得到民众憎恶、谁又会得到民众同情。在这样一个时刻用如此粗略的方法来激荡民情,对于塞剌墨涅斯来说,未免太过冒险。[55]很久以前,格罗特的论断就可以为这个事件下一个定论了:“在这个事件中,欺诈无用。人类天性中自有同情,而同情的情绪在此如此强烈、如此清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就该事件去深挖政治煽动家的诡计动机就不仅仅是多余,而简直是有意误导了。”[56]
很明显,伊翁胞族祭的举行深深激荡了民众情绪。悲恸愤怒取代了同情理解,而在第一次公民大会中,许多雅典人原本带着同情理解的心情接受了阿吉努赛诸将的自辩。五百人议事会的一名成员(-369,370-)卡利克辛努斯(Callixeinus),利用群情与气氛的转向,提出了审判将军们的具体程序,而这种程序对将军们是最为不利的。该程序假定,所有控诉和辩护都已经在阿吉努赛战役后第一次公民大会时陈述完毕,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将不再进行关于控诉和自辩的讨论。这一审判程序使得投票——无论是投票赞成有罪判决,还是无罪裁定——必定会在当前这样一种敌对气氛中进行,这样一来,将军们及其辩护者将不再有机会通过辩护来改变民众的意见。在这次公民大会中,雅典民众将针对将军们是否对“未能营救赢得阿吉努赛海战胜利的人”负有责任这一问题进行投票,投票一个德谟、一个德谟地进行。这样设置投票议程,对于阿吉努赛诸将的辩护者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阿吉努赛诸将一旦被判有罪,他们将被处以极刑,财产将被没收,什一缴归雅典娜。这些惩罚措施几乎比得上斐林尼库斯(Phrynichus)、安提丰(Antiphon)和阿奇普托勒穆斯(Archeptolemus)因为叛国罪而受到的惩罚,而且,斐林尼库斯等人都得到了单独受审的机会,有充分时间在普通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享受到了基本程序正义。与此相反,卡利克辛努斯的提议令阿吉努赛诸将不得不在公民大会集体受审,而他们在此前的第一次公民大会上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自我辩护。尽管卡利克辛努斯所提议的审判程序在程序上是如此不公正,但其提议仍然在五百人议事会获得投票通过,并主导了第二次公民大会上的审判程序。[57]
第二次公民大会对阿吉努赛问题的讨论开始时,很明显,群情激愤,伊翁胞族祭是其滥觞,五百人议事会所选择的审判程序是其结果。据色诺芬记载,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有这么一个人,他说自己参与了阿吉努赛战役,因为紧紧抓住了一个盆才侥幸活下来;在海上,他听到附近正在溺水的同袍对他说话,请求他告诉雅典民众“他们为国奉献,死而后已,将军们却没有营救他们”。[58]在此种谈话所引起的白热化气氛之中,反对主流意见、坚持自己看法就格外需要勇气,但佩先纳克斯(Peisianax)之子游里普托勒穆斯勇敢地站了出来。游里普托勒穆斯是阿尔喀比亚德的表亲,也曾经是阿尔喀比亚德最亲密的同党之一。在阿尔喀比亚德与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游说斡旋时,游里普托勒穆斯曾经担任阿尔喀比亚德的代表。同时,在407年,阿尔喀比亚德从海勒斯滂回来后,正是看见了游里普托勒穆斯,他才有勇气在比雷埃夫斯港登陆。(-370,371-)[59]也正因为有了游里普托勒穆斯为阿吉努赛诸将所进行的辩护,我们才有充分理据来驳斥阿吉努赛问题上的某种“党争论”。“党争论”将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视为对阿吉努赛诸将进行审判的主要原因,认为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对阿吉努赛诸将的攻击实际上是阿尔喀比亚德派别对与其敌对的民主党人的攻击。[60]然而,一方面,在受到控诉的阿吉努赛诸将中,小伯利克里是其亲戚,狄奥梅冬是其朋友,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在为阿吉努赛诸将辩护的主要人等中,也有游里普托勒穆斯这样与阿尔喀比亚德极其亲近的人。单单这个情况就足以说服我们抛弃“党争论”:审判阿吉努赛诸将,并非阿尔喀比亚德派别对民主党人的阴谋攻击。
游里普托勒穆斯,还有其他一些人谴责卡利克辛努斯,说他的动议非法,因此恳请动用司法核覆程序(graphe paranomon)。根据司法核覆程序,卡利克辛努斯必须先接受司法核覆审判,被判无罪后才能继续使用其之前的这项动议。[61]一些人为游里普托勒穆斯的动议喝起彩来,但也有一些人尖叫着反对游里普托勒穆斯的动议,理由是阻止民众意愿得以实现,这是很糟糕的。这时,一个名叫吕西司库斯(Lysiscus)的人站了出来,动议以相同罪名控诉那些要求进行司法核覆程序的人,除非游里普托勒穆斯等人收回要求进行司法核覆程序的动议。吕西司库斯的提议得到了热烈拥护,游里普托勒穆斯等人不得不收回要求司法核覆的动议。接下来,五百人议事会的执行委员会(prytanies)中的一些人,暨公民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拒绝就诉讼案本身提交公民大会投票,理由是这样做是违法的。于是,卡利克辛努斯建议,谁不同意投票,就把谁拉出来对他进行投票。卡利克辛努斯的建议得到了热烈拥护,喝彩的声音让执行委员们感到十分害怕,不得不同意将将军们提交公民大会投票。哲学家苏格拉底碰巧是那天的执行委员之一,唯独苏格拉底有勇气坚持不肯向卡利克辛努斯的提议屈服,但苏格拉底的坚持并没有起到作用,他直接无视。审判程序继续进行。[62]
尽管公民大会如此群情激愤,但是游里普托勒穆斯仍然不惧威胁,再次站了出来,试图为阿吉努赛诸将辩护,提出了不同于五百人议事会所提的另一个动议:依据坎诺努斯法令(Cannonus)来审判阿吉努赛诸将。坎诺努斯法令要求,被控诉犯有“误导民众”罪行的辩护者们戴着镣铐站到公民大会的会场上来;如果这些人罪名成立,就把他们扔进深井里杀死,(-371,372-)没收其财产,什一缴归雅典娜。如果公民大会仍然不喜欢这个提议,游里普托勒穆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提供给公民大会:使用针对洗劫神庙罪或叛国罪的审判程序来审判阿吉努赛诸将。受到控诉的人在民众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就不得埋葬在亚狄珈境内,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什一缴归雅典娜。游里普托勒穆斯向公民大会提出的这两种审判程序都是重罪审判程序,但却能够保证阿吉努赛诸将得到逐一单独审判,并且有一整天的时间来进行自我辩护。[63]显然,游里普托勒穆斯确信,雅典公民大会上激愤的群情如骤风暴雨,只是因为伊翁胞族祭而被煽动起来的暂时性情绪。只要留出时间,让民众情绪平复,双方进行充分论辩,民众就不会给阿吉努赛诸将定罪。游里普托勒穆斯为阿吉努赛诸将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辩护洋洋洒洒,颇为动人;游里普托勒穆斯拒绝归罪于舰长们,尽管他清楚地指出,营救任务是舰长们的责任;游里普托勒穆斯警告雅典民众要注意程序正义;游里普托勒穆斯还提醒雅典民众,这些受到控诉的将军们,刚刚为雅典赢得了一场重大的海战胜利。游里普托勒穆斯的这番演说几乎动摇了当时正处于愤怒和激动之中的雅典民众。一开始,根据举手投票来看,游里普托勒穆斯建议使用坎诺努斯法令来审判阿吉努赛诸将的动议得到了公民大会通过。然而,一个名叫梅内克勒斯(Menecles)的人提出了技术性反对意见,而今天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技术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就游里普托勒穆斯动议进行第二次投票的时候,还是五百人议事会原先的审判程序预案占了上风。公民大会判决所有8名将军——包括已经逃走的两人,加上伊拉司尼德及其他5人——罪名成立,此时仍然留在雅典的6名将军就被处以死刑。[64]
狄奥多罗斯将这样的判决结果归咎于阵亡者遗属及朋友,还归咎于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65]尽管最终投票结果仰赖于超过半数人的支持,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这样的判决结果产生的过程中,是遗属亲朋和塞剌墨涅斯同党起了主要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人数众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在辩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组织情况。遗属亲朋的举动无需过多解释,但是对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党,我们就必须进行一番考察研究了。如前所述,如果我们确实已经摒弃了阿吉努赛问题上的党争论、不认为党派政治是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的主要行为动机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问问,为什么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同党如此坚持要给将军们入罪。现今,我们证据有限,只能略作推测一二。之前所做的种种分析都显示,阿吉努赛战役之后的一系列事件都并非出于哪个人或哪个小团体的精心谋划,(-372,373-)相反,这一系列事件造就了某种特别的情势,群情激愤之际,必须有人得到处分;剩下的唯一问题只是究竟处分谁。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塞剌墨涅斯很可能确信,因为将军们的第二波来信,他和其他舰长们真的已经面临绝境。塞剌墨涅斯一定觉得自己与其他舰长所受到的攻讦极为不公,他们自我抗辩并转头攻击将军们,仅仅只是一种自保举动。[66]一旦愤怒与反恐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军们与舰长们之间原本存在的妥协与相互制衡就已经不再可能实现,反之,恐惧和怒火开始主宰情绪。我们必须看到,在游里普托勒穆斯演说辞中,尽管他使用了一种和解的论调,将营救任务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风暴而非其他,但仍然出现了如下的话语:“因此,得到命令去追击敌军的人,应当就他们未能成功追击敌军来说明情况;同时,得到命令去执行营救任务的人,应当就他们没有执行将军们的命令接受审判,因为他们没能营救起战役中的幸存者。”[67]舰长们没法预见,将军们是不是会被宣告无罪,舰长们也无法预见,接下来,民众的怒火是不是会冲着他们自己而来。此外,如果将军们得到单独审判的机会,那么在长长一串审判中,将军们将不断为自己进行辩护,为了自保,将军们肯定会一次又一次提起营救任务是舰长们的任务,肯定会将营救任务的失败归咎于舰长们。在雅典城邦,至少在几个星期以内,伤痛难以平缓,愤怒难以止息,实在无法预测审判的结果,这样的过程简直教人心惊肉跳。最后,正如我们所见,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党大有可能对将军们在阿吉努赛战役之后的举动加以挑剔抱怨,说将军们在天色如此之晚的时候,才将如此艰难、危险、让人不快的工作任务交给舰长们,那么最终伤者没能得到营救、死者没能得到打捞,将军们也多少逃不了干系。也许,这就是使得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迫切要求对将军们进行集体审判并成功令他们入罪的情绪和想法。
雅典并无成文宪法,所以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对阿吉努赛诸将的审判和定罪是否违宪。[68]然而,雅典人很快就对审判感到后悔了。卡利克辛努斯和其他4人(-373,374-)被控欺骗民众并且罪名成立。[69]在战后如此对待将军们,自古代开始就有人不断谴责这种做法。狄奥多罗斯从中得出了道德教训,说最终的结果似乎表达了神祇的怒火,而在战后被强加到雅典人身上的三十僭主专制就是对这个错误的惩罚。[70]格罗特,雅典民主政体的热切拥护者,为雅典民众辩护,说将军们正如他们被判决的那样,是有罪的。但即便是格罗特这样的雅典民主拥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审判是不当的,说因为雅典人为溺水将士而感到的深切悲痛令这次审判成了“有罪的诉讼”。[71]民众和政府悲恸、紧张、盛怒,盛怒之下,僭越之举与违法行为往往屡见不鲜。在专制之下,僭越与违法举动很难被注意到,也常常轻易就被忘记,因为专断独行和恣意妄为就是专制者的日常行为模式。但是,在施行宪政的温和法制国家里,僭越违法之举会被死死揪住,会被认定是不可以忘却的凌辱和暴行,因为这些僭越违法之举与这个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是如此背道而驰。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带着耻辱永远铭记泰图斯·奥茨(Titus Oates)与其所捏造的天主教阴谋案(the Popish plot),铭记杰弗里斯(Judge Jeffries)的血腥巡回审判,以及铭记处死海军上将拜恩(Admiral Byng)这件事——“为了激励其他海军将领”,如伏尔泰(Voltaire)所说;而法国人呢,则永远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革命法庭所进行的司法屠杀而深感难堪;同理,美国人回忆起在麻省发生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Salem,Massachusetts)时也倍感痛苦,一如他们回忆起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非法囚禁。与这些人一样,雅典人对审判并处决阿吉努赛诸将感到后悔,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因为这一事件与雅典对法律、公平和程序正义的一贯尊重是如此南辕北辙,而这种尊重正是雅典民主政体的特征所在。
雅典人为这个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审判导致8名将军或者被处死,或者被流放,使得他们无法参与405/404年的战争,而这一年恰恰成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年。阿吉努赛事件所引发的憎意与疑惧也使得雅典失去了塞剌墨涅斯这样经验丰富的将领——尽管塞剌墨涅斯于405/404年被选举为将军,但他没有通过新官入职审查程序(dokimasia),因而也就不能出任将军并率部远征。[72]同样,色拉叙布卢斯也受到城邦内这种敌意的侵害,甚至没有能够被选举为将军。(-374,375-)而雅典城邦是多么需要所有这些能人,多么渴求他们的才干。此外,对雅典将军的这种处置方法对于405/404年选举出来的新将军委员会肯定也产生了恶劣影响。在这次审判之前,从来没有雅典将军被处死过。除去这些军事方面的考虑之外,审判和死刑将雅典民众撕裂,而且是在雅典最需要民众团结和相互信任的关键时刻。在危急关头,这些裂痕令政治领导再难沉着理智,也令政治家们易于放任激情盖过理性。
[1] 两份主要的古代文献来自于色诺芬(Xen.Hell.1.6.33—7.35)和狄奥多罗斯(Diod.13.100—103.2)。色诺芬与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在很多地方是不同的,两个版本的叙述之间最明显的分歧是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的行动。在色诺芬的叙述里,塞剌墨涅斯是这次事件中的恶人;在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中,应该谴责的是雅典暴民,而不是塞剌墨涅斯。布索特采纳了色诺芬叙述,认为狄奥多罗斯叙述在修辞学上来看是捏造的、不可靠的。布索特一贯持有这样的观点,与其同时代的大部分学者也一贯如此(关于布索特对狄奥多罗斯的典型苛评,参见《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6页,注释4,以及第1598页,注释1)。甚至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75—210页)也是倾向于在部分采纳狄奥多罗斯叙述的基础上采纳色诺芬叙述的——尽管他用精彩动人的叙述为塞剌墨涅斯脱罪,软化并解释了民众行为,并将主要责任归咎于雅典将军们。柯罗歇(P.Cloché)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为透彻、十分有用(《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第130卷,1919年,第5—68页),他以开放态度处理色诺芬叙述和狄奥多罗斯叙述,(-354,355-)择其适用者而采纳之。随着《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Hellenica Oxyrhynchia)的发现,同时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狄奥多罗斯多次使用了《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2—122页)提出,狄奥多罗斯在记叙将军审判事件时也使用了《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安德鲁斯提到,“不用犹豫,我们应当更多采用狄奥多罗斯的叙述,至少是在其史书第13卷第101节之前的部分,因为自此之后,狄奥多罗斯叙述甚为疏阔不详,以至于我们无法自其叙述中确定其材料的初始来源”(《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20页)。安德鲁斯的论述令人信服,我也认为,我们应当在理据充分之处采纳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同时,如果色诺芬的版本更佳,我们也应当采纳之。我自己对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这两个文献来源的看法和态度类同于柯罗歇的做法,尽管我的结论同柯罗歇是不同的。
[2] 狄奥多罗斯(Diod.13.100.1)告诉我们说,雅典人追出了很长一段距离: 。
。
[3] Xen.Hell.1.6.35,7.30;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6页,注释1。
[4] Diod.13.100.1. 我这样计算面积:假定向南追击的距离等于诸岛屿距列斯堡的距离,即两英里。两英里似乎是一个较低的估计值。幸存者的数目(1000人)同样是保守估计值。赫尔伯斯特(L.Herbst)(《阿吉努赛之战》[Die Schlacht bei den Arginusen],汉堡,1855年,第37页,注释51)估计幸存者数目为1200人,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6页)估计幸存者数目为2000人。值得注意的是,狄奥多罗斯在描述这次战役时始终只提到了尸体数目,而色诺芬则提到了幸存者。
[5] 色诺芬(Xen.Hell.1.6.33;7.29)清楚记载,雅典人回到了阿吉努赛诸岛上,开了个会,此前并不涉及任何营救举动。狄奥多罗斯(Diod.13.100.1—3)则记载,这次会议是在回到阿吉努赛岛上之前召开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色诺芬是对的。正如柯罗歇所指出的(《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流移四散的雅典舰队如何能够集中起来开会进行讨论呢,只有回到阿吉努赛岛才可以。
[6]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208—209页。
[7] 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12—13页。
[8] 参见本书,第243页(原书页码)。
[9] 参见本书第375页,注释①。
[10] 色诺芬的叙述完整呈现了游里普托勒穆斯(Euryptolemus)为阿吉努赛诸将所进行的辩护(Xen.Hell.1.7.31),也用自己的话为阿吉努赛诸将进行了一些辩护,尽管细节欠奉(Xen.Hell.1.6.35)。狄奥多罗斯(Diod.13.100.1)记载呈现的版本较为疏阔简略,没有提及名字,也遗漏了实际行动所采取的妥协方案。狄奥多罗斯还错误地认为,这次会议召开于诸将回到阿吉努赛诸岛之前。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并没有被赋予较其他普通舰长更高的职权(Xen.Hell.1.7.5—6)。
[11] 对阿吉努赛诸将的这个决策批评得最强烈的是格罗特,尽管他也提不出将军们的具体动机(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86页)。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Die Attische Politik seit Perikles],第87页)强调了政治动机。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08页,注释4)提及他们前往密提林的愿望。
[12] 参见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65页;以及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1页。
[13] 参见本书,第173页(原书页码)。
[14] 参见本书,第184—198页(原书页码)。
[15] 阿吉努赛诸在回到雅典后受审时的自行辩护中清楚提到了这一点(Xen.Hell.1.7.5—6)。
[16] 毫无疑问,阿吉努赛诸将确实离开了阿吉努赛岛去追击密提林敌军。将军们在面对公民大会进行自行辩护时说得非常明白(Xen.Hell.1.7.5),以及游里普托勒穆斯在迟些时候的大会上也重申了这一点(Xen.Hell.1.7.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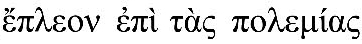 。这里所使用的过去时是意动用法(conative imperfect),这意味着舰队出发了,但是没有能够追上敌军。参见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21页,注释1。知道这件事的人有上千,将军们不大可能就这个问题胡说八道。
。这里所使用的过去时是意动用法(conative imperfect),这意味着舰队出发了,但是没有能够追上敌军。参见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21页,注释1。知道这件事的人有上千,将军们不大可能就这个问题胡说八道。
[17] Diod.13.100.2. 狄奥多罗斯将士兵们提出异见置于返回阿吉努赛岛之前,这是错误的。然而,我们不应该拒绝狄奥多罗斯叙述所提供的这个证据。狄奥多罗斯很可能弄错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他常常如此。我认为狄奥多罗斯叙述的这件事情确有其事,但他自以为合适的这个语境是错误的。
[18]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89页。
[19] Xen.Hell.1.6.37: .
.
[20] Xen.Hell.1.6.28,35,37—38.
[21] Diod.13.97.4;100.2—4.
[22] Xen.Hell.1.6.38.
[23] Diod.13.100.6.
[24] Xen.Hell.1.7.17—18. 我们之所以知道有这种倾向,是因为游里普托勒穆斯在为将军们辩护时的演说里提到了这一点,而不是某段连续的叙述文本里提到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在叙述文本中寻找信息。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2—122页)让读者注意色诺芬叙述中战斗结束和将军召回之间的这道鸿沟,读者难以明白作者在此处的心思。这道文本鸿沟使得雅典民众的行动显得极为愚蠢。这道鸿沟可以使用狄奥多罗斯提供的证据来进行修补,也可以使用色诺芬在其他部分的叙述来进行修补。尽管游里普托勒穆斯的讲述带有偏见,是为了支持将军们、反对塞剌墨涅斯而作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质疑游里普托勒穆斯,质疑他所讲述的将军们的讨论过程是有问题的。将军来信的内容正是因为塞剌墨涅斯向公民大会念出而得到证实的(Xen.Hell.1.7.4—5)。
[25] Xen.Hell.1.7.17—18.
[26] Diod.13.101.3.
[27] Diod.13.101.1.
[28] Diod.13.101.2.
[29] 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37—39页)清楚揭示了第一次意见不合的情况,而维持统一意见、隐藏舰长职责确乎是由将军提出来的。
[30] Diod.13.101.2.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87页)和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8页)说,将军们往家里写了私函,控诉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但古代作家们没有这么记载。同时,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6页)强调了这些通信的正式性和官方性,这是对的。
[31] Diod.13.101.3.
[32]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85页,注释2)认为塞剌墨涅斯等人不承认风暴的作用,但是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22—23页)则揭示了塞剌墨涅斯等人承认,风暴确乎存在,强度很大,且与事件的发生相关。柯罗歇的解释令人信服。
[33] Diod.13.101.4—5.
[34] Xen.Hell.1.7.1;Diod.13.101.5. 罢免阿吉努赛八将所使用的程序很可能是举手表决弹劾程序 。通过该程序罢黜的公职人员并未被定罪,但是业经遭到控诉,必须在相关机构面前进行自我辩护。参见罗伯茨(J.T.Roberts),《雅典政府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in Athenian Government),威斯康辛州麦迪逊,1982年,第15页。在整个阿吉努赛事件中,刻农一直在密提林,因而是无罪的,所以他受命指挥整支舰队,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和菲洛克勒斯(Philocles)则被派去协助刻农指挥雅典舰队。
。通过该程序罢黜的公职人员并未被定罪,但是业经遭到控诉,必须在相关机构面前进行自我辩护。参见罗伯茨(J.T.Roberts),《雅典政府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in Athenian Government),威斯康辛州麦迪逊,1982年,第15页。在整个阿吉努赛事件中,刻农一直在密提林,因而是无罪的,所以他受命指挥整支舰队,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和菲洛克勒斯(Philocles)则被派去协助刻农指挥雅典舰队。
[35] Xen.Hell.1.7.1. 所引述的语句来自于Diod.13.101.5。
[36] 关于离任审查程序,参见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203—205页;麦克道威尔(D.M.MacDowell),《古典时代雅典法律》(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纽约州绮色佳及伦敦,1978年,第170—172页;以及罗伯茨,《雅典政府的责任制》,第17—18页。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都没有直接说明此处使用的遣返程序就是离任审查程序,但是就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料看来,认为雅典当时采取了该程序是说得通的。这是因为,之后我们就将看到,伊拉司尼德第一个被起诉,罪名是滥用公款和指挥失误,而这两个罪名正好对应了离任审查程序所要审查的两个方面。然后,伊拉司尼德被带到民众法庭(Xen.Hell.1.7.2),这正是离任审查程序的下一步做法。其他5名将军先是在议事会(boule)作自辩申明,而离任审查程序两个调查部分各自的负责人审计员(logistai)和调查员(euthynai),则正巧都是从议事会中遴选产生的(Arist.Ath.Pol.48.4—5)。
[37] Xen.Hell.1.7.2.
[38] 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41页。
[39] 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41页,注释12。
[40] Xen.Hell.1.7.3.
[41] Xen.Hell.1.7.3.
[42] Xen.Hell.1.7.4.
[43] 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85—89页;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39—40页。
[44] Diod.13.101.6;Xen.Hell.1.7.5.
[45] Xen.Hell.1.7.6.
[46] 色诺芬(Xen.Hell.1.7.7)说:“将军们说了这些话,眼看就要说服民众了”,原文为 是过去时(imperfect),意味着劝服民众的举动仍然在进行之中,并未完成。
是过去时(imperfect),意味着劝服民众的举动仍然在进行之中,并未完成。
[47] Xen.Hell.1.7.7. 色诺芬说得很清楚,当时确实天色已晚,并非借口。因此,我们不应当将程序延误归咎于诸将政敌的阴谋诡计。参见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46—47页。
[48] Xen.Hell.1.7.8.关于具体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03页。
[49] 帕尔克(H.W.Parke),《雅典人的节庆》(Festivals of the Athenians),纽约州绮色佳市及伦敦,1977年,第88—92页。
[50] Diod.13.101.6.
[51] Xen.Hell.1.7.8.
[52] 例如,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03页。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48—49页)并未径直断定塞剌墨涅斯就此有欺诈和贿赂行为,他的看法是,在遗属闹事这件事情上,塞剌墨涅斯只是敦促丧亲之人前来公民大会进行抗议。
[53] 特别是Lys.12.62—78,但同时参见Lys.12.36。
[54] Xen.Hell.1.7.35;Lys.13.10.
[55] 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8页。
[56]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93—194页。
[57] Xen.Hell.1.7.9—10. 色诺芬宣称,塞剌墨涅斯贿赂了卡利克辛努斯,让卡利克辛努斯在五百人议事会上提出那样对阿吉努赛诸将不利的审判程序来,但是色诺芬对塞剌墨涅斯的这项控罪既不真实,也无必要,就像是色诺芬之前说塞剌墨涅斯找人假扮遗属的事情一样不真实。如果无法在五百人议事会取得简单多数投票,卡利克辛努斯的动议就无法发挥作用。如果五百人议事会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青睐卡利克辛努斯的方案,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去贿赂什么人来推进这个动议呢?
[58] Xen.Hell.1.7.11.
[59] Xen.Hell.1.3.12—13;4.19.
[60] 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86页;亨德松(B.W.Henderson),《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大战》(The Great War between Athens and Sparta),伦敦,1927年,第472页;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7卷,1974年,第116页;麦柯伊(W.J.McCoy),《美国语文学刊》(AJP),第98期,1977年,第282—289页;罗伯茨,《雅典政府的责任制》,第66页。
[61] 麦克道威尔,《古典时代雅典法律》,第188页。
[62] Xen.Hell.1.7.11—16.
[63] Xen.Hell.1.7.16—23.
[64] Xen.Hell.1.7.24—34.
[65] Diod.13.101.6—7.
[66]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在三十僭主统治之下,塞剌墨涅斯遭到克里提亚斯(Critias)控诉的时候,在自我辩护时所说的确乎就是这样一句话(Xen.Hell.2.3.35)。
[67] Xen.Hell.1.7.31.
[68] 麦克道威尔,《古典时代雅典法律》,第189页。
[69] Xen.Hell.1.7.35;Diod.13.103.1—2. 雅典人改变心意的日期我们并不清楚,但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21页)说,“从本质上来说,最有可能的情况应当是雅典民众的态度立马就有了转变”,他很可能是对的。
[70] Diod.13.103.1—2.
[71]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209页。
[72] Lys. 13.1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