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據有關文獻記載,漢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為我國向所公認佛教傳入之始。佛教傳入中國後,隨即得到了迅速的傳播。多災多難、戰亂不息的社會,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佛教的諸行無常、人世苦空、因果報應、三世輪回及彼岸説,正契合了當時彷徨無望的中、下層人士及走投無路的平民百姓的悲觀怨世情緒,並為他們展示了一條求得精神上暫時解脱的道路,同時,也契合了一些統治者希望通過佛教感化,百姓修己向善,從而坐致太平的心理。這就是為何佛教一經傳入,立即受到朝野上下熱烈追捧的原因。
佛教的傳入,首先涉及的是傳教的場所、傳教的内容以及信衆,因此隨之出現的是“寺塔之興”、“譯經之興”與“僧尼之興”。特别是到了南北朝時期,更是蔚為大觀。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蕭衍更是篤信三寶、廣修佛寺,親自講經説法,舉行齋會,甚至四度脱下皇袍,披起袈裟,“捨身為奴”,虔誠地在寺廟裏服役。僅有梁一朝,各處寺廟2 846座,僧尼82 700餘人。僅建康(今江蘇南京)一地,就有大寺700餘所,僧尼信衆常有萬人。
與南朝相比,北朝的氣勢似乎更大,雖説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期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體而言,歷代帝王都大力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為紀念母后開始營造龍門石窟。據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記載,到北魏末年(公元534年),境内佛寺多達30 000餘座,僧尼200餘萬人。僅都城洛陽一地,“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至北齊時,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餘萬人,寺廟4萬餘座。
而這一時期(自東漢至隋),譯成的漢文佛典約達960部,2 990卷,2 400萬字之巨。
二
如此洶湧的外來宗教,一旦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落地生根,對中國人的生命觀念和生活態度,必然産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時潛在地表現在人們為人處世的心態裏,有時又直接表露在個人的社會符號名字中。名字並不僅僅是區别人在社會上的符號而已,更代表着一種觀念,一種信仰。因此,南北朝時期,許多人的名字就直接取材於佛教經典或佛教教義。
對於這一問題,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與佛教》[1]一文中已作了詳細的闡述,文中論及,時人以瞿曇、悉達、菩提、菩薩、羅漢、彌陀等佛教人名或術語直接用於人名的就達36種之多,而用與佛教有關的一個字如“佛”、“僧”、“曇”、“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更是多如牛毛。
不過,也有一些人“名”比較特殊,而吕先生未及列舉者,茲補充數例:
樊梵,字文高(《東觀漢紀》卷一一)。佛家經典均用梵文寫成,謂佛家經典文意高妙。
吕七寶(《魏書》51—1140)。七寶:梵語sapta ratna^ni。即七種珍寶。又稱七珍。指世間七種珍貴之寶玉。諸經説法不一,《大智度論》卷一〇謂七寶即:金、銀、琉璃、頗梨、車渠、赤珠、碼瑙。《法華經》卷四則以金、銀、琉璃、硨磲、碼瑙、真珠、玫瑰為七寶。這是以佛教名物命名。
蕭衍,字叔達(《梁書》1—1)。即梁武帝,“衍”乃“摩訶衍”之省,即所謂“乘”,意為能使衆生到達西方極樂世界的種種教法。意為乘如來五衍之車,即可到達佛國彼岸。
徐普濟(《梁書》47—648)。普濟寺,位於江蘇鎮江東五公里大江中,為焦山名刹。焦山,又稱樵山、譙山、浮玉山。傳説後漢處士焦光隱居于此,現有焦仙嶺,故一般皆稱焦山。山中巉巖叢樹,峭枝鬱結,風景之佳,為江上之冠。此寺建於後漢興平年間,初稱普濟寺,宋代重建,改稱焦山寺,清康熙二十五年,賜名“定慧寺”。此乃以後漢寺名為名者。
裴子烈,字大士(《陳書》5—11)。烈士應“大士”,南朝崇佛,因佛家菩薩通稱為“大士”。
另外,吕先生所舉還大多限於當時人名,而我國古代男子除了有“名”,成年舉行冠禮之後,尚須命“字”(且名、字一般多有所關聯),有人則“大名”之外,還加“小名”。因此,佛教文化影響命“字”、取“小名”者,更不可枚舉。
下面,選擇一些歷史上命“字”、取“小名”與佛教有關的例子列舉如下(所有材料均引自正史),作為吕文的補充:
蕭寶卷,字智藏(《南齊書》7—97)。即齊廢帝東昏侯。智藏,佛教語,謂智慧廣大,包含諸法故曰智藏。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無量無邊,如來智藏,光明清淨,普照十方。”(9—483)
蕭晃,字宣明。小字白象(《南齊書》)35—623)。白象:佛教語,指全身純白之象。以象有大威力而性情柔順,故菩薩入母胎時,或乘六牙白象,或作白象形,表示菩薩性善柔和而有大勢;且白象之六牙表示六度,四足表示四如意。普賢菩薩乘白象,即比喻其大慈力。
蕭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梁書》4—103)。六通:即“六神通”,佛教術語。為佛菩薩依定慧力所示現之六種無礙自在之妙用。具體指: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3—79)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云何六證法?謂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證,二者天耳通證,三者知他心通證,四者宿命通證,五者天眼通證,六者漏盡通證。”(1—54)
蕭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梁書》6—143)。即梁敬帝。相:佛教術語,表現於外而能想像於心的各種事物的相狀。佛教中有“慧相”,劉宋求那跋跎羅譯《雜阿含經》:“云何不知相?事業是過相,事業是慧相。”(2—342)亦稱“智慧相”,西晉竺法護譯《佛説阿惟越致遮經》:“曉了智慧相,明空法亦爾。”(9—219)故名“智”,字“慧相”,名、字義相應。另,歷代僧人中名“法真”者有數人。
蕭方等,字實相(《梁書》44—618)。梁元帝長子。佛家認為:“方”是“廣”之義,“等”是“均”之義。佛於第三時,廣説藏通别圓四教,均益利鈍之機,故名“方等”。又名佛性、法性、真如、法身、真諦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惟此獨實,不變不壞,故名“實相”。故名“方等”,字“實相”,名、字義相應。
蕭方諸,字智相(《梁書》44—620)。梁元帝次子。智相:智慧之相,即指佛之光明。佛之光明,乃佛智顯現於外之相貌,以智慧為其體。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云何比丘知相?於是,比丘知愚相,知智相,如實而知之,如是比丘知相。”(2—794)“方諸”當為“十方諸佛”之省,“十方諸佛”有“智相”,故名、字義相應。
胡僧祐,字願果(《梁書》46—639)。佛家認為“願”乃心中欲成就所期目的之決意,特指内心之願望,如心願、志願、意願、念願等。“果”乃一切之有為法,前後相續,故對於前因而謂後生之法為果。“願果”即大願果成。後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常作如是難舍之施,本作誓願,欲成願果。”(4—338)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贊》:“菩薩久修習,清淨智慧業。廣植諸德本,願果華於今。”(4—192)這正與“僧祐”(菩薩保佑)相應。
沈僧昭,一名法朗(《南史》37—970)。《説文·日部》:“昭,日明也。”徐鍇《説文繫傳·月部》:“月之明為朗。”因此“僧昭”與“法朗”意義相應。另外,晉代有名僧康法朗,其弟子名“令昭”,見梁慧皎《高僧傳》卷四“晉中山康法朗”。
拓跋燾,小名佛狸(《魏書》4—69)。即魏太武帝。千百年來,小名不避從賤,豬、貓、狗、魚均可為小名。乃父母憐惜太甚,故顯卑賤,希望能够養大成人,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樸素的辯證思想。如孔丘之子小名“鯉”,陶淵明小名“溪狗”,王安石小名“獾郎”等。拓跋燾,小名“佛狸”,“狸”乃山貓,加上一個“佛”字,盡顯宗教色彩。
元琛,字曇寶(《魏書》7—78)。琛:珍寶。曇:“瞿曇”之省稱,釋迦牟尼姓瞿曇,故以瞿曇為僧、佛之代稱。曇寶猶言“佛寶”、“僧寶”。
楊範,字法僧(魏書9—2029)。《爾雅·釋詁上》:“範,法也。”故“法僧”與“範”義相應。
元鷙,字孔雀(《魏書》14—350)。鷙:猛禽。孔雀本非猛禽,然佛教中有菩薩孔雀明王,一頭四臂,控馭孔雀,性情威猛,故以“孔雀”應“鷙”。
慕容昇,字僧度(《魏書》50—1123)。佛家之“度”乃渡過之意。謂從此處渡經生死迷惑之大海,而到達覺悟之彼岸。出家為覺悟之昇華,故稱出家為“得度”。字“僧度”與名“昇”相應。
婁昭,字菩薩(《北齊書》15—196)。菩薩,菩提薩埵之略稱。梵語作bodhi-sattva,意譯為“覺有情”(菩提:覺悟;薩埵:舊譯為“衆生”,今譯為“有情”),就是覺悟的衆生,即指上求佛道和下化衆生的大聖人,是佛教中僅次於“佛”的得道者。而“昭”有“明”義,與“菩薩”義相應。
李湣,字魔憐(《北齊書》22—317)。《廣韻·軫韻》:“湣,憐也。”“魔”即“魔羅”、梵語ma^ra之音譯略稱。意譯為殺者、奪命、能奪、能奪命者、障礙。即佛典中能害人性命和障礙擾亂人們修道的餓鬼,欲界第六天之天主即是魔王。以“魔憐”為字者,即祈獲魔鬼之憐憫,不受其傷害。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北齊書》37—483)。“佛助”即祈佛陀之助也。
婁叡,字佛仁(《北齊書》48—666)。《玉篇》:“叡,智也。”“智”與“仁”意義相應,加一“佛”字,以顯宗教色彩。
宇文覺,字陀羅尼(《周書》3—45)。即周孝閔帝。“陀羅尼”,梵語dha^ran!i^之音譯。意譯為總持、能持、能遮。即能總攝憶持無量佛法而不忘失之念慧力。據《佛地經論》卷五所述,可知陀羅尼是一種記憶法,即於一法之中,持一切法;於一文之中,持一切文;於一義之中,持一切義;依記憶此一法、一文、一義,總持無量佛法。故字“陀羅尼”與名“覺(覺悟)”相應。
宇文導,字菩薩(《周書》10—154)。“菩薩”見前釋,菩薩是覺者,是引導衆生得道者,故與“導”相應。
宇文護,字薩保(《周書》11—165)。《漢書·張湯傳》“調護之尤厚”,顔師古注:“護,保佑也。”所謂“薩保”即“菩薩保佑”之義,故與“護”相應。
若干鳳,字達摩(《周書》17—282)。“達摩”即“菩提達摩”,梵語Bodhidharma之音譯略稱。是中國禪宗的始祖。他生於南印度,梁普通年中(公元520—526年)至南朝都城建業會梁武帝,面談不契,遂一葦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陽,後卓錫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傳衣缽於慧可,故中國的禪宗又稱達摩宗,達摩被尊稱為“東土第一代祖師”。達摩祖師與寶志禪師、傅大士合稱梁代三大士。“達摩”為人中之鳳,故與“鳳”相應。
尉遲綱,字婆羅(《周書》20—339)。“婆羅”,即“婆羅門”,又作婆囉賀磨拏、婆羅欱末拏、没囉憾摩,梵語bra^hman!a之音譯略稱。意譯為淨行、梵行、梵志、承習。乃印度四大種姓中最上位之僧侶、學者階級,為古印度一切知識之壟斷者,自認為乃印度社會之最勝種姓。故與“綱(統領)”義相應。
鄭偉,字子直,小名闍提(《周書》36—633)。“闍提”即“闍提首那”,梵名Jatisena之音譯略稱,意譯為愿勇。《涅槃經》所説十仙之一。據北本《涅槃經》卷三九載,闍提首那原為婆羅門,執著涅槃無常,一日與阿闍世王共詣佛所請益,佛陀就其所執為説四真諦法,闍提首那即得正見而皈依佛法,由憍陳如為之剃髮,下手時鬚髮與煩惱俱落,於是得阿羅漢果。
王軌,小名沙門(《周書》40—711)。“沙門”,梵語s/raman!a之音譯,又譯為沙門那、娑門、桑門、喪門。意譯為勤勞、功勞、劬勞、勤懇、静志、淨志、修道、貧道等,為出家者之總稱。
蕭藻,字靖藝,小名迦葉(《南史》51—1267)。“迦葉”,即摩訶迦葉,梵名Maha^-ka^s/yapa,音譯之略稱。為佛十大弟子之一,以頭陀第一著稱。身有金光,映蔽餘光使不現,故意譯為飲光。在靈山會上,受佛正法眼藏,傳佛心印,為禪宗初祖。
楊異,字文殊(《隋書》46—1258)。“異”與“殊”詞義相應。又“文殊”,菩薩名,即文殊師利或曼殊室利,梵文Mañjus  rī的音譯的略稱,意譯為“妙吉祥”。佛教四大菩薩之一,與普賢菩薩常侍於釋迦如來的左右,代表聰明智慧。因德才超群,居菩薩之首,故稱法王子。三國吴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佛遣文殊師利,往度脱之。”(4—520)
rī的音譯的略稱,意譯為“妙吉祥”。佛教四大菩薩之一,與普賢菩薩常侍於釋迦如來的左右,代表聰明智慧。因德才超群,居菩薩之首,故稱法王子。三國吴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佛遣文殊師利,往度脱之。”(4—520)
李雄,字毗盧(《隋書》46—1260)。“毗盧”,佛名。即毗盧舍那、毘盧遮那,梵文Vairocana音譯之略稱。乃密教之大日如來。一説乃佛真身之尊稱。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歸命大智海毗盧遮那佛。”(3—655)
宇文皛,字婆羅門(《隋書》50—1315)。“婆羅門”詳“尉遲綱,字婆羅”條。《説文·白部》:“皛,顯也。”與“婆羅門”之地位正相應。
盧思道,字子行,小名釋奴(《隋書》57—1397)。
崔弘度,字摩訶衍(《隋書》74—1698)。“摩訶衍”,即摩訶衍那,梵語maha^-ya^na之音譯略稱。意譯為“大乘”。“大乘”本義指大的交通工具。不以個人之覺悟(如小乘行者)為滿足,而以救度衆生為目的,一如巨大之交通工具可載乘衆人,故稱為大乘。以此為宗旨之佛教,即是大乘佛教。《爾雅·釋詁上》:“弘,大也。”“弘度”即普度衆生,與“摩訶衍(大乘)”相應。
至如以“僧”、“佛”、“法”、“敬”、“道”、“善”等與佛教相關的詞語命“字”者,更如吕先生所云“多如牛毛”。如:司馬消難,字道融(《周書》21—354)。趙剛,字僧慶(《周書》33—573);趙善,字僧慶(《周書》34—587),兩人字相同。王僧孺,字僧孺(《南史》49—1459);冀儁,字僧儁(《周書》,47—837),此兩人各自名、字相同。魏玄,字僧智(《周書》43—779)。薛慎,字佛護(周書,35—624)。姚僧垣,字法衛(《周書》47—839)。蔡大寶,字敬位(《周書》48—868)。蔡大業,字敬道(《周書》48—869)。杜正藏,字為善(《隋書》76—1748)等,因限於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又:有人認為:“唐宋之際,佛教為儒學所同化兼併,雖鮮有詩人王維字摩詰之類的佛門殘羹,但釋宗的不出家修行,自性成佛的教義,因符合漢文化的傳統,卻為人所尚。唐朝時大多的文人墨客都以居士自居,如李白——青蓮居士,白居易——香山居士,歐陽修——六一居士,李清照——易安居士,蘇軾——東坡居士,等等。”[2]
其實,也並非完全如此。唐宋之際,受佛教影響而取“名”命“字”的風氣仍盛,不過,隨着佛教的普世化,這一風氣逐漸深入了民間。社會上層的人士取名命字直白地取材於佛教經典或佛教教義的情況日漸式微,即使信佛的文人也只以居士作為自己的雅號而已。而南北朝時期的那種直接取材於佛教經典或佛教教義的取名方式,卻廣泛運用於下層吏民。只要我們打開敦煌文書,僅西北地方,命名與佛教有關者即不可勝數(因下層吏民,一般僅有名而無字),而且除男性以外,有更多的女性受此影響,名字也帶上了濃烈的佛教色彩。如:名字中帶“佛”字者有安佛奴(S2228)[3]、董佛奴(P3418背)、曹佛奴(P2877)、張佛奴(P3250)、令狐佛奴(京都有鄰館51)、石佛得(P3249)、羅佛利子(P3391)、馬仏住(S4472)、陽大佛(S3005)等;帶“僧”字者有杜僧奴(P3018)、泛胡僧(S5632)、吴僧子(S1845)等;帶“法”字者有杜法子(女)(P3877)、宋法光(ДX1282)等;帶“像”(佛教所謂“像寶”)字者有康像奴(羅振玉藏頭名簿)、宋像通(羅振玉藏頭名簿)、麴像子(S2894)等;以佛、菩薩名命名者有安羅漢(P3559)、賀羅漢(P3559)、王金剛(P5016)、趙金剛(ДX1282)、張金剛(P4635)、張觀音(S2669)、唐觀音(S2669)、馬曼殊(S2669)(按:即文殊,菩薩名)、程妙音(女)(P3877。按:妙音,菩薩名,為印度佛教説一切有部四大論師之一)等。另外涉及佛教名物、教義者更是不可枚舉,如:趙曼陀(S2669。按:即曼陀羅,佛經中天花名)、王妙智(女)(P3877。按:妙智謂佛智之不可思議也)、程妙果(女)(P3877。按:妙果:佛經中即指菩提涅槃)、程十住(P3877。按:菩薩五十二位修行中,第二個十位名十住)、劉再住(羅振玉藏頭名簿)、鄭永住(P3559)、張安住(P5038)、程祐住(P3145)、趙慈觀(女)(P3877)、鄭因果(女)(P3877)、史神力(P3559)、郝行滿(P3559)、羅皈歸(P3071)、劉皈漢(S0327)、陰留德(S0327)、程沙門(女)(P3877)、泛沙門(P3559)等。唐宋以後,仍不絶如縷,只是已到强弩之末。如:
宋人陳天麟(1116—1177),字季陵,安徽宣城人,宋高宗紹興十八年進士。據《陳書·徐陵傳》記載:南朝陳徐陵,幼聰穎,家人攜之見高僧寶誌,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陳天麟,字季陵,就是用了這一佛教典故。
清人王詰,字摩也,江蘇太倉人,家居浙江吴興。清代著名畫家,工山水。王詰字摩也,取義與唐人王維字摩詰同。維摩詰,又稱“維摩”,菩薩名。即維摩羅詰、毗摩羅詰,梵名Vimalakirti音譯之略稱。意譯“淨名”,淨者清淨無垢之謂,名者名聲遠布之謂。維摩詰為釋家之大乘居士,曾以問病為由,向釋迦牟尼派來問疾的弟子文殊師利宣揚大乘佛教。
清人歐陽厚均(公元1766—1846年),字福田,清嘉慶四年進士,著名經學家。《漢書·王嘉傳》:“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佛家稱佈施行善以獲來生之報為“福田”。此中以佛教之“福田”與“均田”對應。
清人陳貞慧(公元1604—1656年),字定生,江蘇宜興人,明末清初散文家。《唯識決論》九:“云何為慧?由慧推求,得決定故。”此拆用佛經經文為名、字例。而“生”為男子美稱。
三
當然,關於佛教文化對於中土人取名命字的影響,我們也不能牽强附會,一概而論,必須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如關於“華佗,字元化,一名旉”(《後漢書》82—2736;《三國志》29—799),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一文認為:“檢天竺語‘agada’乃藥之意。舊譯為‘阿伽陀’或‘阿羯陀’,為内典中所習見之語。‘華’字古音,據瑞典人高本漢字典為rwa,日本漢音亦讀‘華’為‘か’。則華佗二字古音與‘gada’適相應,其渻去‘阿’字者,猶‘阿羅漢’僅稱‘羅漢’之比。蓋元化固華氏子,其本名為尃而非佗,當時民間比附印度神話故事,因稱為‘華佗’,實以‘藥神’目之。此《魏志》、《後漢書》所記元化之字,所以與其一名之‘旉’相應合之故也。”[4]
陳寅恪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文史大家,但對陳先生的這一説法,本人有些不同的意見。
(一)首先,從語音上看“華佗”兩字的古音:“華”有兩音:(1)華草之“華”(花之本字)。《廣韻》:“呼瓜切”,乃“曉”母“麻”韻合口二等平聲字;上古音為“曉”紐“魚”部,擬音為[ ]。(2)光華之“華”。《廣韻》:“户花切”,乃“匣”母“麻”韻合口二等平聲字;上古音為“匣”紐“魚”部,擬音為[
]。(2)光華之“華”。《廣韻》:“户花切”,乃“匣”母“麻”韻合口二等平聲字;上古音為“匣”紐“魚”部,擬音為[ ]。佗,《廣韻》:“徒河切”,乃“定”母“歌”韻開口一等平聲字,上古音為“定”紐“歌”部,擬音為[da]。俞敏先生在《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中通過對當時譯經的窮盡性調查告訴我們:梵文中的“g”類音節,後漢三國譯經中分别對應的漢字是“伽”、“迦”、“竭”、“揭”、“犍”、“乾”、“揵”、“劫”、“橋”、“
]。佗,《廣韻》:“徒河切”,乃“定”母“歌”韻開口一等平聲字,上古音為“定”紐“歌”部,擬音為[da]。俞敏先生在《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中通過對當時譯經的窮盡性調查告訴我們:梵文中的“g”類音節,後漢三國譯經中分别對應的漢字是“伽”、“迦”、“竭”、“揭”、“犍”、“乾”、“揵”、“劫”、“橋”、“ ”、“耆”、“俱”、“瞿”、“群”、“掘”、“祇”、“懼”、“拘”、“求”、“裘”、“健”、“曷”、“含”、“恒”、“合”。梵文“ga”音節,對應的漢字是“伽”、“迦”;梵文“gad”音節對應的漢字是“竭”。而“伽”、“竭”為“群”紐字;“迦”為“見”紐字,没有以“曉”、“匣”紐之漢字“華”對譯者。雖然,在漢譯佛經中,梵文中少數的[g]後來也有變為擦音[
”、“耆”、“俱”、“瞿”、“群”、“掘”、“祇”、“懼”、“拘”、“求”、“裘”、“健”、“曷”、“含”、“恒”、“合”。梵文“ga”音節,對應的漢字是“伽”、“迦”;梵文“gad”音節對應的漢字是“竭”。而“伽”、“竭”為“群”紐字;“迦”為“見”紐字,没有以“曉”、“匣”紐之漢字“華”對譯者。雖然,在漢譯佛經中,梵文中少數的[g]後來也有變為擦音[ ]的,如以“曷”、“含”、“恒”、“合”對譯者,俞敏先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他説:“‘匣’和‘群’並没有互補關係,在漢語裏,‘匣’與‘于’互補,《切韻指掌圖》的歌訣裏已經提過,雖然不大準,可也不是常識以外的東西,不詳細説了。這種‘匣’在譯咒法師嘴裏反映兩個母音中間g後來變擦,好像有些德國人把Tage念成[
]的,如以“曷”、“含”、“恒”、“合”對譯者,俞敏先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他説:“‘匣’和‘群’並没有互補關係,在漢語裏,‘匣’與‘于’互補,《切韻指掌圖》的歌訣裏已經提過,雖然不大準,可也不是常識以外的東西,不詳細説了。這種‘匣’在譯咒法師嘴裏反映兩個母音中間g後來變擦,好像有些德國人把Tage念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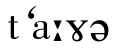 ]。漢語裏的這種‘匣’也是這麼來的麼?暫時没法兒斷定。”[5]後來俞敏先生的高足施向東教授經過對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研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説:“《切韻》音系的群紐何以没有一等字,只有三等字。與所有各組塞音相比,唯獨這一組塞音没有一等濁音,十分奇特。黄侃主張古無群紐,後來從溪紐分化出三等的群紐。其實不然。上古音本有群紐。後漢譯音以‘含恒合’對g,這些字當時正是群紐一等字。後來,由於一等字後母音的影響,輔音發音位置後移,k、kh變成q、qh,而g後移之後漸漸保持不了塞音的音色,變成了發音部位較後的摩擦音,所以這些字在《切韻》系統中跑到匣紐中去了。”他通過對玄奘譯著中梵漢對音的研究,結論是:“輔音g,對譯用字:伽祇窶瞿耆具懼郡健乾揵喬殑毱局姞掘崛揭笈拘,這些都是群母字。例外字:恒(匣紐),例外字出現率1/158,小於0.6%。”[6]從俞敏、施向東先生深入細緻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梵漢對譯中,對譯梵文g音節的,一般都是“群”紐漢字,而以“匣”紐字對譯者,所占比例極小。從後漢三國到唐代玄奘的譯經中,也僅“曷”、“含”、“恒”、“合”四字而已,而且此四字皆為一等字。而“華”乃合口二等字,所以將“agada”譯為“阿伽陀”或“阿羯陀”是符合後漢三國時的梵漢對譯規律的,而譯成“阿華佗”,用“華”對譯梵文g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漢語裏的這種‘匣’也是這麼來的麼?暫時没法兒斷定。”[5]後來俞敏先生的高足施向東教授經過對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研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説:“《切韻》音系的群紐何以没有一等字,只有三等字。與所有各組塞音相比,唯獨這一組塞音没有一等濁音,十分奇特。黄侃主張古無群紐,後來從溪紐分化出三等的群紐。其實不然。上古音本有群紐。後漢譯音以‘含恒合’對g,這些字當時正是群紐一等字。後來,由於一等字後母音的影響,輔音發音位置後移,k、kh變成q、qh,而g後移之後漸漸保持不了塞音的音色,變成了發音部位較後的摩擦音,所以這些字在《切韻》系統中跑到匣紐中去了。”他通過對玄奘譯著中梵漢對音的研究,結論是:“輔音g,對譯用字:伽祇窶瞿耆具懼郡健乾揵喬殑毱局姞掘崛揭笈拘,這些都是群母字。例外字:恒(匣紐),例外字出現率1/158,小於0.6%。”[6]從俞敏、施向東先生深入細緻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梵漢對譯中,對譯梵文g音節的,一般都是“群”紐漢字,而以“匣”紐字對譯者,所占比例極小。從後漢三國到唐代玄奘的譯經中,也僅“曷”、“含”、“恒”、“合”四字而已,而且此四字皆為一等字。而“華”乃合口二等字,所以將“agada”譯為“阿伽陀”或“阿羯陀”是符合後漢三國時的梵漢對譯規律的,而譯成“阿華佗”,用“華”對譯梵文g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二)據《佛教大辭典》:“阿伽陀:梵語agada的音譯。[7]gada是病,a是否定;agada即是病之否定,故是無病、健康,亦有不死的意思。②指一般的藥,特别是解毒劑,服後除病。亦可作不死藥解。③從語源學來説,梵語agada可以解為āgata,意譯為普去;即是説,這種藥用了普遍地使衆生去除病苦。另外,gada可解為價(值),agada即是無價(值),該藥有無量價值也。故又稱阿竭陁藥。”①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梵語agada中,a表否定,agada與gada意思截然相反,所以梵語中的“agada”決不能省作“gada”。因此陳先生認為華佗的名字是梵語“agada”音譯之省略,似為牽强。更為甚者,1980年,日本弘前大學醫學部麻醉科教研室松木明知先生在日本出版的《麻醉》第9期,發表了題為“麻醉科學史最近的知見——漢之名醫華佗實為波斯人”的文章。松木明知認為:華佗是波斯文xwadag的諧音,其含義為主或神。所以華佗不是人名,而是主君、閣下、先生的意思,引申到華佗個人的職業應是“精於醫術的先生”之意。以此“華佗”似乎又成了波斯人。其實這類僅靠聲音接近而强作比附的作法是很危險的。
(三)再説,古人名“佗”,並非鮮見,且在華佗之前,早有諸多名“佗”者,比如春秋時期:王子朝和周敬王争位,周敬王的支持者名劉佗(《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晉國有賈佗(《左傳·文公六年》)、涉佗(《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宋國有仲佗(《左傳·定公十年》),衛國有尹公佗(《左傳·襄公十四年》)、北宫佗(《左傳·襄公三十年》),陳國有陳佗(《左傳·桓公六年》),莒國有季佗(《左傳·文公十八年》)。西漢時南越國王名趙佗(《史記·南越王尉佗列傳》),東漢時有孟佗(《後漢書·張讓傳》)、楊佗(《後漢書·孫程傳》)。三國時有徐佗(《三國志文類》卷五〇“裴松之評魏氏”條),等等。而且我國的人名一般是與字相應的。華佗字元化,一名旉。佗,古有“施加、施及”義。《詩·小雅·小弁》:“舍彼有罪,予之佗矣。”毛傳:“佗,加也。”鄭玄箋:“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大子。”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長沙方言續考》:“佗:今長沙人謂不自承其過而移加於人曰‘佗’。”[8]《廣雅·釋詁二》:“拸,加也。”王念孫疏證:“拸之言移也。移,加之也。《趙策》云:‘智伯來請地,不與,必加兵于韓矣。’韓子《十過篇》‘加’作‘移’,是‘移’與‘拸’同義。《玉篇》‘拸’音‘與紙’、‘與支’二切。《集韻》又‘他可切’。《小雅·小弁》篇‘舍彼有罪,予之佗矣’,毛傳云:‘佗,加也’。‘佗’與‘拸’亦聲近義同。”[9]故“佗”有“施加”義。華佗,字元化,“化”為教化,教化乃施加於人者,故名、字相應,謂施加教化也。同時,華佗一名“旉”。旉,古敷字,《説文·寸部》:“旉,布也。”徐鍇《繫傳》:“旉,布以法度也。”《玉篇·寸部》:“旉,徧(遍)也”,《説文·攴部》:“敷,(按:即‘施’之古字)也。《周書》曰:‘用敷後人。’”[10]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九“敷析”注引孔注:“敷,施也。”因此這“旉”字不僅與字“元化”義相應(施加教化),而且與本名“佗”均表“施加”,為同義。再者,《爾雅·釋草》:“華,荂也。”郭云:“江東呼華為荂,音敷。”如此,“旉”不僅與華佗之“佗”同義,還與“荂”同音,而“江東呼華為荂”,則與“華佗”之“華”亦相應。由此看來“華佗,字元化,一名旉”,三者互相關聯,乃一有機整體,絶非陳先生所云“《魏志》、《後漢書》所記元化之字,所以與其一名之‘旉’相應合之故也”。更為有力的佐證是:北魏時期有一裴陀,字元化(《魏書·良吏列傳》)。此人為河東聞喜(今山西)人,曾任中書博士、趙郡太守、東荆州刺史。其名為“陀”,其字亦為“元化”,説明這一名、字意義相應,是當時人都懂得的。
(四)華佗並非上古神話人物,他乃漢末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11]。據考證,他約生於東漢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卒於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張仲景(張機)、華佗與董奉,史上並稱為“建安三神醫”,何況張仲景之名聲不在華佗之下,何以張仲景、董奉均為真名,獨華佗要用梵語來稱呼呢?且《後漢書》卷一一二、《三國志·魏志》卷二九均有華佗的專傳。《三國志》是西晉陳壽(公元233—297年)編寫的一部紀傳體國别史,詳細記載了從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六十年的歷史,受到後人推崇。《後漢書》則是劉宋時范曄(公元398—445年)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後漢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後來居上的紀傳體斷代史。所以《後漢書》、《三國志》均為嚴謹的正史,列入前四史之中。陳壽距華佗不足百年,范曄距華佗亦不過二百餘年,雖然在記述華佗的年齡與其醫術時,有可能受到民間流傳的誇大之辭的影響,比如“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比如也可能隨着佛教傳入的印度醫學的一些案例攬入其中,但不至於連姓名都是虚構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自東漢才傳入中土,因此受佛教文化影響而取名命字的現象是在佛教非常普及以後,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西晉以前很少見到,到南北朝時才興盛起來。所以吕先生也只談了“南北朝人名與佛教”,從本人所收集的材料看,也没有早於西晉的。而華佗乃漢末人,似當時還無此風氣。
引用書目
史書皆採用中華書局二十四史版,書名後所附數字,前一數字為卷數,後一數字為頁碼。
佛經採用大正新修大藏經,引文後括弧中,前一數字為册數,後一數字為頁碼。
敦煌人名來源於敦煌社會經濟文書,每個人名後括弧中注明了卷子的出處,材料引自《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録》(1—5輯),唐耕耦、陸宏基編,書目文獻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86—1990年。
【注释】
[1]吕叔湘《南北朝人名與佛教》,《中國語文》1988年第4期。
[2]佚名《關於姓名文化的宗教審視》,佛緣網2009 10 12,http://www.foyuan.net/。
[3]括號中爲敦煌冩卷卷號。下同。
[4]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原載《清華學報》1930年第6卷第1期,後收入《寒柳堂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社2001年版。
[5]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見《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6]施向東《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研究》,部分内容原以“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為題發表於《語言研究》1983年第1期,全文見《音史尋幽——施向東自選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7]吴汝均編著《佛教大辭典》,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2年7月臺灣第1版,1995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本。
[8]楊樹達著《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9]王念孫《廣雅疏證》,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0]《説文·攴部》:“,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段玉裁注:“今字作施,施行而廢矣。”《玉篇·攴部》:“,亦施也。”
[11]據前亳州博物館館長、知名的亳州地方專家李燦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華佗是“譙人”,這在最原始、也是最權威的文獻《後漢書》、《三國志》及《博物志》中都有記載。華佗是亳州人,這是無可置疑的。除了文獻記載,亳州還有大量有關華佗的遺跡和傳説。李燦先生説,在1957年和1981年的兩次地名大普查中,他發現漢朝直到華佗時,華氏後裔主要分佈在亳州的雙溝鄉和泥臺鄉,尤以雙溝鄉為主。雙溝和泥臺都是漢朝的大鎮,其中雙溝鄉東北的華莊堌,是當前發現的惟一一處漢代的、面積最大的華氏族居遺址。李燦先生還透露,在亳州至少還有以下十個地方與華佗有關:一是泥臺鄉西部老楊河邊,有個華祖廟村,村中約有20户華姓人家;二是雙溝鄉西北的華寺村,有50多户華姓人家;三是華寺村北1里左右的華寺廟,住有1户華姓人家;四是城父鎮東北有華佗廟,當時已經荒廢;五是現在亳州城内的華祖庵;六是雙溝鄉東4里有華嚴寺,有華姓居住;七是華莊堌東面有華雲寺,也有華姓居住;八是雙溝鄉東部5里有個華姓大村,叫華莊,有88户華姓人家;九是雙溝鄉東部和西南部各有一個“小華莊”,都有華姓人家居住;十是亳州市北10里左右,有個小華莊,當時有60餘户華姓人家。(《新安晚報》2010年2月23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