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出版产业研究的重要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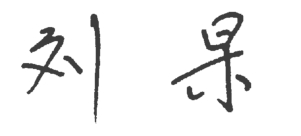
我和陈昕同志有点文字因缘。1996年11月,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了《中青年编辑论丛》,收了9位中青年编辑同志的自选文集,其中就有陈昕同志的《编匠心集》。中国编辑学会积极支持这件事。学会的同志分工审稿,分给我审稿的正好是陈昕同志的《编匠心集》。丛书出版后,我以《读枙编匠心集枛》为题,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我对书稿的肯定意见。此前在丛书的总序中我是这样写的:“10多年前,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批批青年同志陆续进入出版界,踏上编辑工作岗位。他们是新时期出版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参与者,是伴随着这段历史逐渐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伟大的时代孕育和造就了出版界新的一代。……我们以十分喜悦的心情,欢迎出版界新的一代。”又过了10年。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新时期出版界的新一代,已经成为出版界的栋梁。在他们中间,陈昕同志无疑是佼佼者之一。
陈昕同志的《中国出版产业论稿》(以下简称《论稿》)也是文集,不是专著,但是它比较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了出版产业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可以说,《论稿》是当今出版产业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10年前我在《读枙编匠心集枛》中写过:“这些年来,我深感需要加强对出版业的经济学的研究。出版业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门,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对这一点现在没有争议了。因此需要研究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经济学的依据,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条件。问题是目前能做这种研究的人不多。像陈昕同志这样既熟悉出版、又具有经济学素养、还是热心人,十分难得。”过了10年,《论稿》的内容表明,陈昕同志再接再厉取得了新的成果,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我之所以特别看重陈昕同志对出版产业的经济学研究,是因为要做好出版产业必须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是理性的科学的态度,是成功之路。加强对出版产业的经济学研究,是在出版产业的发展中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前提。现在全国轰轰烈烈发展出版产业,可是如何从经济学上加深对出版产业的理解、进而自觉坚持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少同志的准备明显不足。认识上有误区、实践上有盲目性,自然都不利于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
对出版产业的经济学研究,首先是研究普遍性。这非常重要。因为出版产业也是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相同的共性。普遍经济规律,对所有产业是适用的,对出版产业也是适用的。比如,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其次是研究特殊性。这尤其重要。其中研究出版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殊性,难度最大。《论稿》上篇《中国出版产业发展阶段研究(1978—2005)》,是本书重要的长篇论文。这篇论文第二章“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经济学分析”,是论文主要部分“展开叙述的基础”。在这章的“图书商品性质的经济学分析”一节中,给出了若干命题:“图书是一种文化商品”、“图书商品有显著的差异化”(“图书商品的差异化根源于图书的文化属性”、“图书商品的差异化为图书种类的增加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图书属于较弱的超必需品”(超必需品“反映的是人类较高层次的需求”)、“图书商品具有正的外部性”(“外部性为正,意味着他人或社会的福利有了增加,但行为人或厂商却没有得到补偿,比如发明、公共绿地、教育,等等”)。在“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特性的经济学分析”一节中,也给出了若干命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对图书市场需求的影响”、“收入结构及人口结构对图书市场需求的影响”、“图书出版产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性”、“图书出版产业有较高的集中度”、“图书出版产业的数字化发展趋势”。这篇论文第三章“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阶段性分析”开头就说:“本章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作实证考察,并以第二章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为分析工具,对不同阶段的内在成因作经济学分析。”陈昕同志特别重视对出版产业的经济学分析。不仅这篇重要论文如此,《论稿》全书都是如此。这是《论稿》的特点和优点。陈昕同志的结论是不是都正确大家还可以讨论,但是他重视经济学分析的科学态度毫无疑问是值得提倡的。
《论稿》不是坐在书斋里从书本到书本,而是以饱满的热情和勇气面对出版产业的现实。正因为这样,《论稿》有多处闪光的亮点,在初次发表时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比如,关于“中国图书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论述。这对于认识和把握市场竞争态势的变化、从而积极地理性地投入市场竞争、推动市场走向成熟,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关于组建出版集团的论述。明确提出“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出版集团的组建问题”,进而提出“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原则性意见,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关于建立强有力图书发行中盘的论述。“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图书发行中盘”,是关系图书流通产业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比如,关于抓紧建设中国出版业的现代物流体系的论述。这个对全国来说具有很大前瞻性的论述,“是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目前的实践为蓝本展开的”。比如,关于出版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的论述。加强数字化建设,开发数字化产品,跟上数字融合步伐,是出版产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些只是举例。《论稿》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有陈昕同志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因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要说《论稿》闪光的亮点,不能不特别提到关于出版应当勇敢承担文化建设重任的论述。陈昕同志熟悉经济、关注经济、会办经济。他却大声疾呼出版要“勇敢承担文化建设重任”。他不是离开经济谈文化,而是结合经济谈文化,结合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谈出版产业承担的文化建设的职责。这是很可宝贵的。
1994年他写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出版一些高质量的、代表国家水准的大型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的出版家们,让我们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新体制的过程中,逆市场的‘短视’而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出版好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以迎接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这番议论很有远见。
2002年他写道:“如果我们依然顺从于市场‘短视’的本性,不从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花大力气来培养整个民族文化创新的能力,那么就不仅是文化产业长期发展乏力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也可能因此而无法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如何通行于世界各地?”“我们强调培养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也不意味着要把文化创新的成果仅仅置之于书斋;恰恰相反,当我们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时,当我们把原创文化的成果纳入产业发展的轨道时,那么涌现出的将是何等壮观的生产力啊。”这番议论很有气派。
2005年他写道:“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般说来企业的目标可以表述为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出版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它的目标是二元的;出版企业当然也要创造利润,但更重要的是要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图书,出版企业的利润追求应该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图书产品来真正加以实现。”“在出版改革过程中,我们往往容易出现两类偏差,一是片面追逐利润而出版了一些格调低下或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图书,忘记了出版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它所承担的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责任。二是片面追逐利润,离开了内容提供和生产的业务领域,热衷于进入股市、楼市、旅游等其他非文化出版产业,忘记了出版企业承担的文化建设的重任。因此,出版单位在由事业转制为企业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出版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是一项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番议论切中时弊。
在《论稿》之外还有陈昕同志的答记者问可以参照。2006年2月,他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一直在讲一种世纪出版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脊梁。现在我不能说已经成为文化脊梁,但我们正在努力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脊梁。”此前他在接受《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出版单位承担着传播先进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的职责,世纪集团把自己的使命定为:通过我们的选择,提供能够创造或增加价值的内容和阅读体验;通过我们的整理,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我们的服务,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可见文化建设这个主题,在陈昕同志的出版理念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他的这个观点,前后一贯,旗帜鲜明。现在的出版界,有力争成为“文化脊梁”的有志之士,也有小平同志批评的那种“混迹于”出版界的“唯利是图的商人”。大家都面临着是与非、荣与辱的重大抉择。
《论稿》的问世触动了我。我想借此机会重复我的多次呼吁:高度重视出版产业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出版学和出版经济学的研究。这是出版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只有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才有可能使出版产业的发展上升到自觉的层面。出版学和出版经济学的走向成熟,是出版产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和重要标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