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出版人论出版的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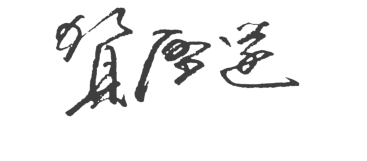
陈昕同志历年所著有关出版研究的文章约有百万字之钜,他从中选出一部分编为《中国出版产业论稿》,交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并嘱我为之写一篇序。其实此书已有出版界前辈刘杲同志的序,以年辈与身份而言他的确是一位合适的作序人;我则不然,从哪一方面说都不合惯例。而之所以“知难而进”,因为有两条可说的理由:往年陈昕同志曾有邀我加入世纪出版集团的动议,事虽不果,心意可感,这是私谊;复旦出版社打算从本书开头,组织出版一系列本行业人士研究讨论出版事业的著作,我忝为主事人,有些想法可以借此机会略加表白,这是公义。至于浅陋之言少说为妙,却又顾不到那么周全了。
在一个社会的总体结构中,出版业具有某种特殊性。它既是一种产业,又是一项文化事业;它以产业的经济活力,支撑起自身所承担的文化功能。一个出版从业人如果仅仅以利润最大化为止足,则无论怎样成功,也绝不可能在本行业中受到广泛的尊重。因为出版的内容始终关乎文化的建设与文明的传承,发现、收集、整理、引入、传播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于当代及后世有益的信息,始终是优秀的出版人投入这一事业的根本动机。而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够从商品特征上理解图书,循依产业的规则组织出版,则基本的运作都难以维持,一切宏大的计划徒然束之高阁,文化功能的实现也就成了空话。所以,一个优秀的出版从业人,总是在文化承担与经济运营这两方面都具备足够的能力。
出版业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尤其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面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在艰难的环境里、巨大的压力下,国人努力“走出中世纪”、“走向世界”(这里借用两种书名)。而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出版业从其诞生开始,就成为催化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译介西方著作引入先进思想,编印新式课本昌明现代教育,到汇辑古典名著清理传统文化,正如王建辉同志在《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近代出版在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如社会参与、价值表达、思想传播、知识扩散、文化阐发等诸多方面,都成为近代文明的重要载体”。而优秀的出版人如商务印书馆的早期主持者张元济,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都是以成功的产业经营,使出版机构成为沟通学术界、思想界与社会大众的枢纽,成为文化的集散中心。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大变革时期,它的历史意义恐怕怎样评价都不算高。在这一进程中,出版界同样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历史的运行,对于新的中国蓝图的不断展开,甚至常常是起着先导的作用。而一代新的出版工作者也就在这特殊的时代中获得展示他们的意志和智慧的机会。刘杲同志说陈昕乃是今日出版界的栋梁之材中的“佼佼者”,我想同行中对此大多是愿意认可的。
如果用军队中培育将帅的情形作比喻,陈昕同志的一个突出之处是在出版行业中具有完整的履历:他从普通编辑、编辑室主任做起,而后在上海和香港的几家著名出版机构展转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领导职务,做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并于1999年负责组建了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他熟悉中国出版界的所有层面,深切了解这一行业的快乐与艰辛,弊端与希望。在这一方面,同行中确实是罕有其配。
陈昕同志对出版事业的热情和超常的工作精力,恐怕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至少我自己是如此。领导着规模宏大的出版机构,他的眼光总是盯着发达国家,把了解这个行业最前沿的情况和发展大趋势作为自己的必修课,因此出国调研、考查是经常有的事情。但和一般人出国考查总要顺带观光不同,陈昕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人民日报》曾有一篇报导,引用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李远涛跟随陈昕去美国后的感想,说是“每天两个出版机构,再加上要准备大量材料,喘不过气”;“满脑子都是访问、会谈和一堆堆数字,对美国的感觉却模模糊糊”。我还听说过一桩趣闻:陈昕率团访美,回国那天一盘算,离上飞机还有个把小时的多余时间,于是领着众人又参观了一家就近的书店。当然不仅是出国考查,差不多在任何情况下,陈昕都喜欢以紧张的节奏来工作,“消闲”二字与他全然无干。我想他也不是准备当劳模的,这就是他的风格乃至生活习惯——与人之常情有违,怕也难免。
出版界有以从事实务为主的,也有偏重于理论研究的。前一种类型的人往往不太重视理论,眼光不能放得很远;后一种类型的人往往对实际操作知之不深不细,所论或有迂曲。以我自己的经验,觉得在出版业中负一点责任的人,应该将两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才好。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陈昕尤为佩服。他既是一个实践经验丰富的出版家,又是一位学者。早在1978年,陈昕就写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这篇内容超前的论文,投到当时的《社会科学》杂志。此后在从事出版业的二十余年中,他撰写了100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着重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出版,因此获得一个“出版经济学家”的雅号,这在中国出版界是很少见的。陈昕的主要论文已经收录在本书中,它的学术价值,刘杲同志在他为本书所作的序中也有较全面的评价,我就不必多说了。我只是想强调一点:陈昕同志的研究,一方面是理论性很强,视野很广阔,从图书的商品性质、出版业的产业特点、到中国图书市场的变化与前景、中外图书出版的比较,都有堪称系统的分析;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学院派”的书斋里的学问,它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始终扣紧当下出版业运作和发展的实际问题,宏大的设想总是和十分具体的操作设计相联系。作为同行,读起来尤其觉得亲切。
要我另外再谈一点读后感的话,那就是常常会想起《老子》所说的“强行者有志”。
出版一向被认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行当;出版人自己写书,特别是关于出版的书,颇为少见。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版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版社不再是简单地按照现行政策或领导意图编印图书的机构,它正努力成为文化创新活动的主导者和组织者,成为在市场的基础上以长远眼光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有待总结,有不少问题需要探究。因此,出版一批有价值的“出版人谈出版”的著作,恐怕是有必要的。这不仅有益于同行间彼此沟通、取长补短,说到底出版乃是全社会的重要事业,它也是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在计划编这套书时,想到陈昕同志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领头的,这一次仍请他领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