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烽火中的呐喊——以《呐喊(烽火)》周刊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在令人沮丧的1930年代,当国民党实施的“白色恐怖”因日本入侵华北而更为加剧时,知识分子们试图复兴“五四运动”的思想。即使被攻击为有害于全国一致的抗日斗争,他们仍然坚决号召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他们相信,没有启蒙就不能救国。
——舒衡哲
战争让文明显得更加文明。
——汤因比
《呐喊》周刊是茅盾、巴金于1938年在上海创立的文学期刊,这份刊物出刊2期后旋即更名为《烽火》,第十三期改由广州出刊。作为新文学的两大巨擘的茅盾与巴金,在抗日军兴的上海创办这样一份抗战杂志,理应受到文学界、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可笔者认为,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这份刊物却是这样一种状况:提到的多,研究的少;既不批评,赞誉也少。
“提到的多,研究的少”是因为这份杂志的主办者茅盾、巴金两人在1949年之后先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长达50余年,关于茅盾、巴金的学术论文、人物传记汗牛充栋、蔚为壮观,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道独特景象。既然做他们的专门研究,就不能不论及他们在抗战时的文学贡献,于是这样就提到了这份杂志,但是笔者始终未曾看到过关于这份杂志的专门研究与论述,论述篇幅较多的唯一一篇论文亦是将其与胡风的《七月》杂志联合研究的,而且论文作者吴永平还这样说:“要想如实地评价《七月》周刊或《呐喊》(《烽火》)[1]周刊的历史功绩,非进行比较式的综合研究不可”。
“既不批评,赞誉也少”则是拜《七月》主编、作家胡风的言论所赐,他曾这样说:
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件,抗战开始了,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当时上海原有的一些刊物的主办人都认为现在打仗了,大家没有心思看书,用不着文艺刊物了,所以都纷纷停刊。只剩下一个缩小的刊物《呐喊》(后改名《烽火》),却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境地,内容比较空洞。我认为这很不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时候应该有文艺作品来反映生活、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2]
这段话后来被收入了《胡风文集》,这是胡风在1982年接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柯丝琪访谈时的发言。[3]这一年恰恰是茅盾去世后的第二年,一批在上海参加过“文化抗敌”的老作家、老学者与老出版人都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相继病故,而作为饱受政治迫害“幸存者”与“孤岛文学”见证者之一的胡风,其发言自然就有了一定的权威性与真实性。自此之后,大多的文学史学者在提及《呐喊(烽火)》周刊时,多半就从胡风的这段话出发阐释。
但是,这份杂志的主办者茅盾与巴金乃是并不等同于邵洵美、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而是继鲁迅之后在“十七年时期”与“新时期”中国文坛的旗手与统帅,除了胡风这一特殊个例之外,谁也不敢轻易否定他们俩的文学成果。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于该刊物,索性采取既不批评也不赞誉,匆匆一提并不带深入研究的态度。时至日久,这份刊物落入“提到的多,研究的少;既不批评,赞誉也少”的冷门境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的主旨在于,借胡风对于《呐喊(烽火)》杂志的界定,从客观、具体的史料出发,以《呐喊(烽火)》杂志为支点,试图审理其在“抗战文学”中的独特价值与文化贡献,澄清现当代文学界对于这一刊物的偏见与误解,从而进一步审理“左翼”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或曰“抵抗文学”)的具体关系所在。
一、是“剩下一个缩小的刊物”还是“烽火中的呐喊”?
《呐喊(烽火)》周刊创刊于1937年8月25日的上海。
在这份杂志创刊前的12天,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宝山并截断淞沪铁路,发动震惊世界的“八一三”事变,淞沪战争遂爆发。炮火喧天的战争持续了3个多月,而8月23日清晨的“吴淞登陆战”(又称“上海保卫战”)则是整个淞沪战争最惨烈的一仗。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十一师团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于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由于中国守军人少装备差,使得日军强行进入上海境内,“孤岛上海”失守。为挽救危局,次日由陈诚、罗卓英、薛岳、关麟征、何柱国与李仙洲等组成前敌总指挥部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先后分批赶至上海,向登陆入城之敌发起猛烈反击。由于上海是由街道、弄堂组成的城市,两军无法进行炮战与空战,只有进行巷战与白刃战,战争持续竟达半月,双方均伤亡惨重。整个淞沪保卫战堪称抗日正面战场上牺牲最为壮烈的战役之一——正是在“吴淞登陆战”之后的第三天,《呐喊(烽火)》杂志创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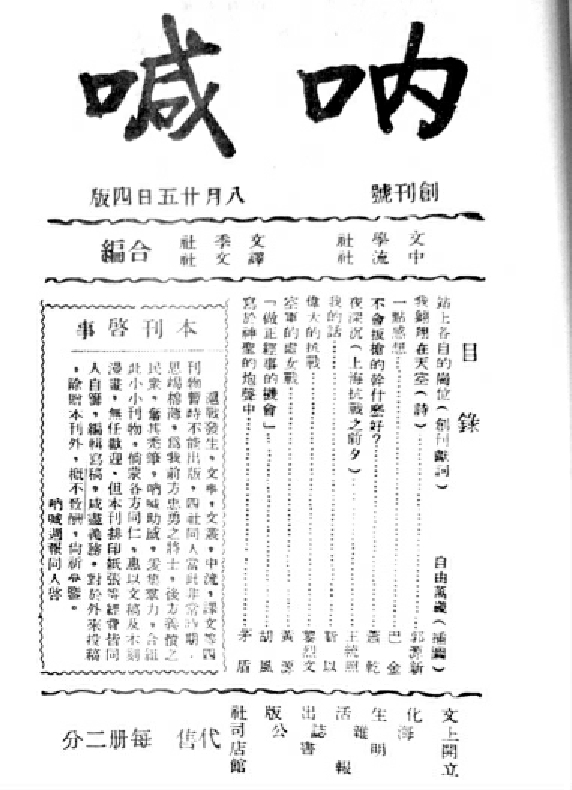
《呐喊》创刊号封面
在1938年之前的上海,各类文学刊物可谓是蔚为大观,随着日军的进犯,一批不愿意投敌从事“和平运动”的作家与出版人遂开始从事“抵抗文学”,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一批文学杂志的被迫停刊甚至遭遇恐怖迫害。在创作上,“绝大多数杂文作家完全停止了写作”。在刊物上,一系列刊物相继停刊、终刊,如黄源主编的《译文》月刊(1937年6月停刊)、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1937年6月停刊)、卞之琳等主编的《新诗》(1937年7月10日停刊)、钱瘦铁等主编的《美术生活》(1937年8月1日停刊)、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37年8月1日停刊)、黎烈文主编的《中流》(1937年8月5日停刊)、洪深与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1937年8月10日停刊)、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月刊(1937年11月10日停刊)以及在1939年日本特务对于《大美晚报》文艺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的暗杀,将军事殖民统治对抵抗文学的迫害推向了高潮。
在这样的语境下,《呐喊》杂志的创刊显然有着非同于一般的意义。抛开内容不谈,其刊名亦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指向,甚至可以说是因为战争而成立的一个定向刊物。出刊的目的就是宣传抵抗,而且就在日军进犯之下的上海出刊。
在创刊号的发刊词里,“《呐喊》周报同人”这样说:
沪战发生,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等四刊物暂时不能出版,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棉(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爰集群力,合组此小小刊物,倘蒙各方同仁,惠以文稿及木刻漫画,无任欢迎,但本刊排印纸张等经费皆同人自筹,编辑写稿,咸尽义务。对于外来投稿除赠本刊外,概不致酬,尚祈共鉴。
而在郑振铎(署名“郭源新”)执笔的《站在各自的岗位》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一向从事与文化工作,在民族总动员的今日,我们应做的事,也还是离不了文化——不过,和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战争紧紧地配合起来的文化工作;我们的武器是一支笔,我们用我们的笔,曾经描下汉奸们的丑脸谱,也曾经喊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同胞的愤怒,也曾经申诉着四万万同胞保卫祖国的决心和急不可待的热诚……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够做得好,但我们相信我们工作的方向没有错误!
由是可知,《呐喊(烽火)》绝非是“剩下来”的刊物。从史料而论,茅盾始终是抗战期间“抵抗文学”的主要办刊者,无论是重庆的《文艺阵地》,还是上海的《呐喊(烽火)》,以及后来香港的《笔谈》,若无茅盾,这些刊物断然不可能出现。尤其在鲁迅逝世之后,茅盾在当时左翼文学界的影响力,除了郭沫若之外,几乎无人可堪匹敌。
《呐喊(烽火)》之所以能够出刊,并非是“剩下来”的缘故,也不是“缩小的刊物”——此刊乃是由巴金和靳以主持的“文季社”、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黄源主持的“译文社”与郑振铎主持的“文学社”“四社合并”办刊的结果。这四个文学社在当时的“孤岛文坛”都有着自己独立发行数年的刊物与固定的读者群体,已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学机构。而且巴金、郑振铎等人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力,亦非一般作家所能匹敌,而茅盾作为“总盟主”形成的“四刊合一”的期刊出版业“康拜恩”,乃是实至名归的强强联合。
在发刊词中,刊物的立意说得很明确。为“忠勇之将士”与“义愤之民众”“呐喊助威”,这乃是《呐喊(烽火)》创刊的缘由所在,而且“四社合并”乃是人力资源合并,在当时经济崩溃的上海,根本无法有多余的资金为作者发放稿酬,这在发刊词中也说得很明了。
作为“抵抗文学”的杂志代表,《呐喊(烽火)》周刊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在大批刊物停刊的环境下,它创刊了,而且是吴淞登陆战期间上海唯一的一份抗日期刊。值得一提的是,胡风的《七月》杂志创刊于同年的9月11日,其时不但晚于《呐喊》,甚至比《烽火》还要晚6天。此时吴淞登陆战已经基本结束,国民政府国防部已向上海大量增兵,蒋介石亲自担任负责沪杭地区的第三战区总司令,并将顾祝同、朱绍良、张发奎与刘建绪等悉数调往上海,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上海本地的局势也有所稳定。
二、是“很不够”,还是“群贤毕至,少长云集”?
正如上文所述,《呐喊(烽火)》乃是真正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日里创办的一份抗日期刊,这是其他刊物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呐喊》杂志体现出了极强的时效性与影响力。
首先是作者群的“名家云集”以及对青年作家的培养,起到了健全中国新文学创作者梯队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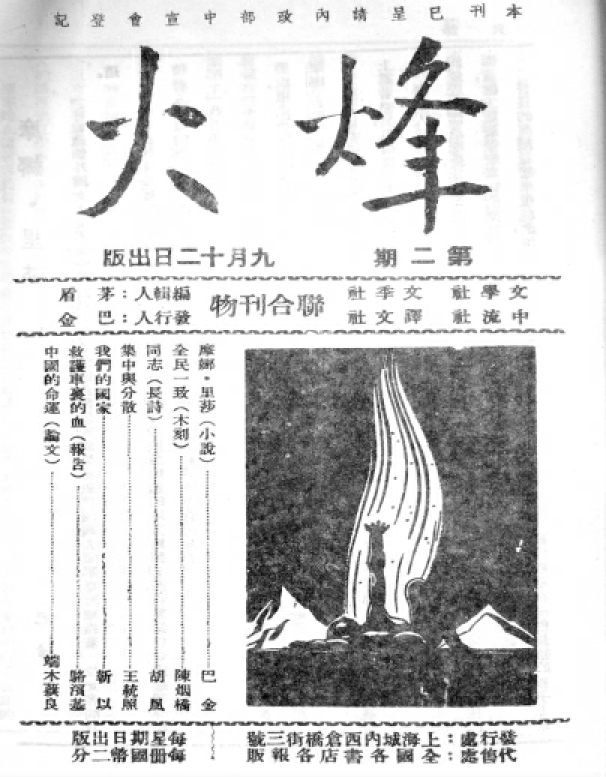
《烽火》封面
虽然每期文章不多,看似薄薄一册——《呐喊》创刊号仅为小三十二开本,15页,且均不给付稿费,但其中每一个作者都是在当时中国文坛具备极高知名度的人物。如第一期的文章由郑振铎、巴金、萧乾、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胡风与茅盾所写。其中,黄源是当时翻译屠格涅夫的著名翻译家,亦是新中国作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而黎烈文则是《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其余的作者,其知名度更是不用赘述。
这样由名家主办且由其他名家一起撰稿的刊物,在当时非常鲜见。而且撰稿作家群相对固定,在第二期中,亦还是这样一批作者(除胡风之外,其中巴金用笔名“余一”)。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只有茅盾才有这样的影响力,且仅在抗日救亡这样的战争语境下,大多数作家才可以这样团结起来,包括已经和茅盾有了不愉快回忆的胡风。
在其后的《烽火》杂志中,文学名家、大家们更是层出不穷、竞相来稿——许广平、郁达夫、郭沫若、丰子恺(漫画稿)、叶圣陶、端木蕻良、刘白羽、卢焚、骆宾基、田间、陆蠡、蔡若虹、艾芜、鲁彦、赵家璧、碧野、唐弢、阿垅(署名“SM”)、蹇先艾、杨朔、邹荻帆与《呐喊(烽火)》的发起人茅盾、萧乾、靳以、巴金及王统照等人一同构成了“《呐喊(烽火)》作者群”,如此庞大、如此豪华的阵容,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杂志中当是独一无二,绝非胡风所称的“缩小的刊物”。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处于战争中,但《呐喊(烽火)》杂志并未放弃对于文学创作多元化的重视与青年作家的培养,其中有丰子恺、郭沫若、茅盾、巴金与叶圣陶这样早已成就斐然的作家,亦有鲁彦、骆宾基、王统照与蹇先艾这样的“文坛边缘人”,其中更重要的是,像碧野、刘白羽、杨朔与邹荻帆这样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作家,亦在《烽火》杂志上获得了发稿的机会——在战争动荡的30年代末,伴随着大量文学杂志的停刊,“和平主义”杂志的盛行,一批热血文学青年亟待获得培养与平台——《烽火》为碧野、刘白羽等人提供了一个走上文坛与名家同台的机会。正因此,刘白羽的小说、碧野的诗歌与杨朔的散文,恰恰成为了1949年之后中国新文学在主流创作题材上的典范。[4]
其次是这份杂志本身的发展与影响,见证了“抵抗文学”在“孤岛”以及全民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抗争与努力。
《呐喊》创刊号虽然名家云集,但从装帧上看仅仅15页,8张纸。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开明书店与立报馆四家书店代售,定价每册2分。无怪乎胡风要说这是一份“缩小”的杂志。但到了第二期,由卜五洲主持的“五洲书报社”与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也参与到“代售”即发行的书店当中;及至更名《烽火》后,“发行”与“代售”均独立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发行部门”——这是一份报刊从“同人”走向“市场”的显著标志。其发行处为“上海城内西仓桥街三号”(今上海市黄浦区西仓桥街近河南南路与复兴东路交界处),这是上海一直以来的闹市区,可见其办刊规模已经扩大。且“代售处”也不是之前的区区6家,而是“全国各书店各报贩”;到了《烽火》第四期,已经有了“杭州总经售东南图书公司”与“重庆总经售文化生活社重庆分社”,这种蒸蒸日上的趋势一直持续到南迁广州的第十三期。
该刊于1938年5月1日南迁广州之后,改为旬刊,但其影响力有增无减,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售”,且在“上海、汉口、广州、重庆”均有分售,而且在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与上海杂志公司可以“代售”,定价也由2分涨到了5分。
在南迁广州之前,该刊没有稿费制度,采取的是“欢迎投稿,暂以本刊为酬”的方式,但是南迁广州之后,在“本刊启事”中,有这样两条:
一,本刊自第十三期起移在广州发行……又本刊并未委托外埠书店翻印,倘有此类情事发生,当提出严重交涉,希各地书业注意。
二,本刊为文学社、文季社、译文社、中流社联合刊物,经费亦由同人自筹……外稿一经刊载,当略付薄酬……
这个启事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是南迁广州的第一份刊物,但是已经提出了对于盗版者的抨击。这说明在上海办刊时,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已然出现了盗版,这足以说明其销量与影响力是相当大的。第二,《烽火》开始实行稿费制度,这说明该刊的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不再是之前那份在资金上捉襟见肘的刊物了。
《烽火》第十三期的《复刊献词》这样写道:
……国军退出淞沪,大上海完全沦陷以后,我们还竭力使我们的“烽火”燃烧在敌人的阵地,但我们的发行处却已经成为灰烬了。接下来的禁止和封锁断绝了我们和许多作者读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在中立区域里自由地扬起我们的呼声,但我们也不愿让敌人永远窒息了他。现在经了一些时日努力的结果,我们又在自己的土地上重燃起我们的“烽火”……

巴金发表于《烽火》上的《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复刊献词》所表现的是,虽然办刊地点变了,但是其主旨、核心没变,还是之前的那个《烽火》。甚至在这篇《复刊献词》的后面,还加上了当时郑振铎所写的《呐喊》发刊词《站在各自的岗位》,以表现两种刊物的一脉相承性。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此时的《烽火》,虽不说是“财大气粗”,但至少日子也好过许多,25页的页码,加上从未有过的书刊广告,这份刊物随着其南迁广州,顺利地完成了从“同人杂志”向“商业杂志”的基本转型,其影响力的扩大,亦不言而喻。
这充分说明,该刊的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吸引更多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二线作家与社会评论家的积极响应,由之前“群贤毕至”的“群英会”,变成了“少长云集”的“百花园”。而且越到后面几期,广告越多,若是没有足够的发行量,是决然不会腾出版面刊载广告,也不会有商家愿意在上面投放广告的。
一份刊物,从战争正严峻的时刻创刊,到最后移师广州,成为一份日益壮大、影响深远的文学期刊,它在国难当头之际,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与郁达夫等,说它是“剩下一个”、“日益缩小”的刊物,这是有违史实的。正因此,对于《呐喊(烽火)》的重新挖掘与研究,不但有了“辨章学术”的史学价值,更亦有着“考镜源流”的翻案意义。

因战乱《烽火》无法按时出刊,图为“向读者道歉”
三、是“观念性的境地”,还是“战争叙事”的必然?
《呐喊》创刊伊始,确实看似内容片面,几乎每篇文章以抗战宣传为主,但这不是“陷入”了某种境地,而是主编有意而为之。
期刊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性媒介的文本载体,其本身有着除了文学之外的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语境。尤其是在都市文化勃兴的上海,这一点尤为明显。当“八一三”事变爆发以后,日军对于上海的报馆、杂志社所采取的办法是“收买”加“封杀”,利用杂志尤其是文学杂志成为鼓吹“大东亚共存共荣”谎言的工具,并命名为“和平文学”运动(在华北沦陷区则命名为“新民文艺”运动)。伪政权配合日本占领军在沦陷区范围内发行的一系列杂志如上海的《新世纪》、《中国与东亚》、《众论》、《新申报》、《远东月刊》、《国民新闻》,北京的《中国文艺》、《朔风》以及南京的《同声》等,在当时均颇具影响。
在抗日与亲日二元对立的政治语境下,此时的文学刊物必然不可能超然二者而存在。看一份刊物究竟是否片面,除了观察其内容之外,更要审理其办刊人、办刊宗旨与主要作者究竟为何。作为之前有过丰富办刊经验的茅盾与巴金,决然不是政治吹鼓手,也不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之所以在《呐喊(烽火)》中,茅盾和巴金将“抗日”当做主旋律来对待,甚至招致“片面性”的置喙,笔者认为,从史料出发,可资分析的原因有二。
首先,“左”而不偏,是《呐喊(烽火)》杂志的办刊精神。
1930年4月,茅盾曾当选为“左联”执行书记,作为“左联”乃至中共的早期主要成员,茅盾一直没有卷入党内的派系纷争。1936年“左联”自动解散,两年后茅盾就主编《呐喊》杂志,可他并未向当时的“左联”核心作家约稿。所以,在整个《呐喊》以至于后期的《烽火》中,始终未曾见到周扬、冯雪峰、田汉、陶晶孙、徐懋庸、楼适夷、阳翰笙、王任叔(巴人)与阿英等人的名字。
这些早在30年代初就已经扬名国内文坛的“左翼文学猛将”,并未在名家云集、新人辈出的《呐喊(烽火)》杂志上露脸。按道理茅盾不会不认识他们,而且作为一份抗日刊物,没有这些激进的“左联文学家”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事实上,整份杂志虽然充满了抗战的激昂,主要作者却都是以巴金为代表的“左联”的“外围作家”。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是《呐喊》的另一位主编、“无政府主义作家”巴金的缘故,因为巴金始终没有进入到“左联”体系的内部。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一次全民甚至全人类的战争,既是救亡图存的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其并不以某种意识形态、党派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亦是《呐喊(烽火)》创刊的缘由。同样,我们还可以进而认为,因为他们所处的是上海,而上海是国民革命军的正面战场,在他们的观念里,本身就是国民政府作为抗战的主导力量。
但无论怎么说,事实却在《呐喊》创刊献词里被郑振铎写得明明白白:
向前看!这里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只有采取独立自由的中国,就能保障东亚的乃至世界的和平!同胞们,坚决地负起你们自己解放的任务!被压迫的日本劳苦大众和被驱遣到战场上来的中国士兵们,也请认清了你们的地位,坚决地负起你们自己解放的任务。
这段话的立场,在抗战军兴的“抵抗文学”中,非常罕见。其民族主义[5]精神,昭然于纸上,反政府不反民族,呼吁“被压迫的日本劳苦大众”甚至“被驱遣到战场上来的中国士兵们”一起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斗当中,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主张。但是,《呐喊》又始终未向梁实秋、邵洵美、陈西滢、凌叔华与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们约稿。可以这样说,在政治立场上他们是中立的,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抗日主旋律”恰恰又是民族主义的立场,而非如之前的“左翼文学”那般片面、偏激。
其次,《呐喊》体裁全面,既考虑到了战争叙事的需要,亦照顾到了其办刊的文学追求。
《呐喊》创刊,本是应战争之景,属于“定向出刊”,这一点无可厚非。若是批评其“内容比较空洞”,比起一些政论刊物、生活杂志来,《呐喊》已然是纯文学的路径,尤其其后出版的《烽火》,不但作家梯队层级分明,而且体裁丰富,文体全面,且不说胜于抗战期间口号性、时政类刊物,纵然是“后五四”时期纯文学刊物如《语丝》、《新月》等刊物亦未必有此等办刊层次。
在此顺便说明一下,从文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实际上是中国文学体制现代化进程的体现,而这个进程同时有三种形式存在。第一种是以俄苏、日本为师的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其作品讲求政治功利性,充满了小林多喜二、契诃夫与果戈理的讽刺精神,在现代中国则以鲁迅及其杂文为代表。第二种则是以欧美为师的自由主义以及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文学,其风格雅驯清丽,主张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作家直接从美国南部文艺复兴作家与毛姆、罗瑟蒂的英国随笔家那里吸取文体营养,在现代中国则以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美文为代表。第三种则是从“左翼文学”发端,在延安得到丰富,以赵树理、周立波为主的“延安派”文学,其创作实践则是左翼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叙事,其理论则是来自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鲁迅及其杂文风格在“左翼文学”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在鲁迅之后,萧军、聂绀弩、巴人与王实味等人高扬“鲁氏杂文”大旗——虽然他们在之后并未因为自己接过了鲁迅的大旗而受到新政权的青睐。[6]在鲁迅之后,杂文已然构成了左翼文学的“投枪匕首”,因为从论战、笔谈等方面来看,杂文语言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力量,在左翼刊物如《北斗》、《朝花》中,杂文占了相当多的篇幅,但是在《呐喊》中,杂文(包括短论与杂感)却只有区区46篇,占到总共187篇文章的24.6%,大约与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其他体裁的发稿量相持平。从这点来看,《呐喊》并不是一个斗争味十足、“空洞”的左翼期刊。
为进一步地说明问题,同时笔者亦分析了左翼文学期刊的代表《前哨》,这份被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杂志”的刊物创刊于1931年4月25日,其出刊也是一件“应景之作”——悼念“左联五烈士”的“纪念战死者专号”,但是在其后第二期,便改名为《文学导报》。这份自命“文学”的“导报”一共出刊8期,8期杂志竟然没有一篇小说、散文与报告文学,除了文告、理论批评、口号诗歌,就是鲁迅风格的杂文,而这也是“左翼文学杂志”最为鲜明的代表。但在《呐喊》中,却丝毫没有这种倾向。
由是可知,《呐喊》虽然诞生于炮声隆隆的战争年代,作为一份旨在“呐喊助威”的期刊,其并不失文学家办刊的激情,亦有着一份文学刊物应该具备的文学精神。它不依靠任何党派,不做任何政治势力的传声筒,这是《呐喊》杂志所传递的精神所在。但是,它对于抗战的呐喊,对于人类和平的呼吁,这恰恰不是其“空洞”的表现,而是战争叙事的必然。
四、结语:“时代的要求”究竟是什么?
作为新文学的重要史料,重新审理《呐喊(烽火)》杂志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呐喊(烽火)》只是一个支点,研究者的力度不应该仅仅只是作用在具体的文本、史料之上,而是应该全面、客观地把握“极左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左翼文学,而是被极左思潮所控制,以党派利益、“山头主义”为核心的文学规制)与“抵抗文学”(或曰抗战文学)的关系。
首先,“抵抗文学”与“极左文学”并无本质联系。
“抵抗文学”是一个特定时间下的词语,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以鼓舞全体国人士气为主要目的的文学体系,而“极左文学”则是片面地以极左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种文学运动。“极左文学”到最后发展为“党派文学”,即成为党内少数人意志的践行者。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却因“抵抗文学”而断裂,在初期的“抵抗文学”中,就有作家开始抛弃左翼文学的党派教条,而将目光投向了泛人类意识下的战争叙事。[7]
《呐喊》杂志虽为“抵抗文学”杂志之翘楚,却未曾陷入“极左文学”之窠臼。“极左文学”与“抵抗文学”相比,最大的特点便是“极左文学”不但反日,而且还反国民党政府,譬如在《前哨》杂志里,就有这样的诗作:
还要问一问国民党竟是什么人/原来是资本家地主的假名称/他们都是奴才性/卖国卖民都要卖的干干净。
只怕碰着工农兵/外国的中国的大人都惊心/国民党就赌咒发誓去打红军/哪知道打了半年打不胜/帝国主义说我对你不相信/要想亲手来打中国的工农兵/这也是东洋军阀出兵的大原因。[8]
这首诗歌写得简单粗糙、斯文全无,其立论令人匪夷所思,日本人侵略中国,竟然是帮国民党打红军?其作者政治素养堪比中学愤青。但是诗的作者“史铁儿”不是别人,正是中共领袖、著名作家瞿秋白。论瞿秋白的文采与政治素养,写这样的诗歌,实在是有些失文格,但是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瞿秋白被极左思潮干扰到了何种境界——毕竟在“极左文学”的视野中,任何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连日军侵华这样的世界战争,竟然也变成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洋枪队”。[9]
但是,在《呐喊》杂志中,全无这种狭隘的文学政治观,甚至还有相当多的篇幅,歌颂中国军队,即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功绩。在《呐喊》第一期中,就刊载了黄源的《空军的处女战》一文,在第二期里,又有郑振铎的《为士兵们做的文艺工作》以及黎烈文的《略谈慰劳工作》,充分反映了编者、作者捐弃党派纷争,以全人类、全民族利益为重的文学民族主义视野,丝毫不见之前“极左文学”中的偏激与狭隘。
其次,“抵抗文学”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而这恰恰是“极左文学”并不具备的。
在抗战期间,左翼文学内部曾就此分化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大阵营。周扬认为,“(国防文学)将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式各样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英勇事实……使它(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10]。但是,在另一位作家周立波心目中,崭新的“国防文学”是“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11]。
在这场论争中,所暴露出来的就是左翼阵营对于“大众文学”的推崇,甚至还意图让“大众文学”作为一个总口号,来统领包括国防文学、救亡文学甚至抗日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历史地看,这两大口号的论争,实际上是左翼文学内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矛盾的总爆发。由巴金、包天笑、林语堂、周瘦鹃、陈望道、郭沫若与鲁迅共21位各派作家代表在1936年10月1日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之后,左翼文学的内部纷争才在表面上尘埃落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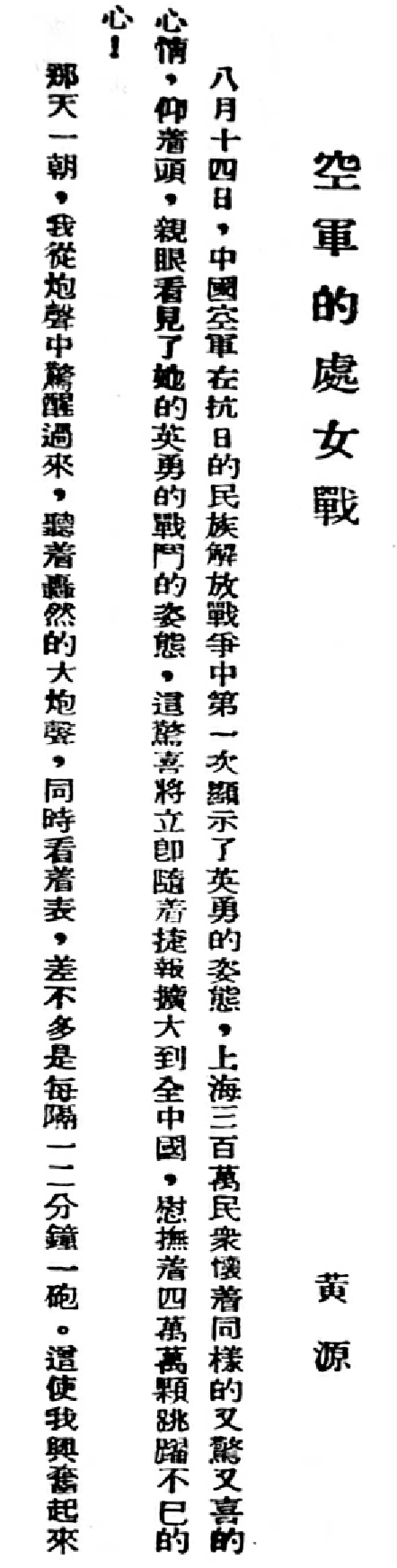
《呐喊》第一期报道空军初战
“左翼文学”被迫让位给“抵抗文学”,使其成为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的主潮,此为不争的史实。这也是《呐喊(烽火)》杂志缘何会“低开高走”的原因,尤其在移师广州的《烽火》杂志中,办刊者更增加了纯文学作品的分量,譬如小说、散文的篇幅,甚至还推出了“烽火小丛书”(主要是以小说散文为主,其作者群为茅盾、巴金、靳以、王统照与茅盾等文学大家)。“烽火”大有燎原之势,这足以见得胡风贬低《烽火》“不符合时代要求”,纯粹是个人恩怨作祟。
当然,《烽火》后期的畅销与巴金经营的“文化艺术出版社”不无关系。在抗战艰难环境下,一份刊物可以从发不出稿费、仅仅数页的“同人刊物”发展为插有广告、厚达数十页并有较大销量的市场类刊物,这也见得了《烽火》的生命力。同时,带有党派利益、“山头主义”的“极左文学”在这最为艰苦的时刻却销声匿迹了。“时代”毕竟“要求”顺应时代者。站在全民族利益之上的《呐喊(烽火)》杂志,便奏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而这声音,不但可以消弭炮火之声,还能洞穿历史,颠覆一切来自于暗处的非议。
【注释】
[1]为行文方便,若是两刊合论,下文概统称为《呐喊(烽火)》,若是单论其中之一,则只称为《呐喊》或《烽火》。
[2]胡风:《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关于此问题请参阅“补记”,此文发表于《书屋》杂志2010年第10期。
[4]从广义上说,《呐喊(烽火)》是一份与左翼文学有着一定渊源的刊物,但是它的意义更在于对于中国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培育,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物与当时的中共组织也有着一定的直接联系。譬如在第十七期曾出现了署名“易河”的一篇报告文学《陇海东行》,而“易河”正是新四军文化干部杨仲康的笔名。
[5]长期以来,1949年之前的“民族主义”文学似乎一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正面评价,而在1949年之后,“民族文学”则是一种以全民族利益为核心利益、以民族救亡图存为核心命题的文学。
[6]王实味在延安整风时被处死,聂绀弩在“反右”时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巴人与萧军在“文革”中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从广义的文体上看,姚文元亦是鲁迅杂文的继承者,但是他的结果也不好。
[7]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女作家葛琴(1908—1995)的《总退却》,鲁迅曾为该书撰序,称该书中“人物并非英雄”(见于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而另一位女作家杨之华(笔名文君,1901—1973)的《豆腐阿姐》亦是另外一部出自左翼文学但主张泛人性论的“抵抗文学”。杨之华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第二任妻子,在瞿秋白的推荐下,《豆腐阿姐》亦受到鲁迅的关照,并在“当天下午便改妥,而且还改正了里面的错字,分别写出楷体和草书。然后用纸包好送回”。见于陈铁键:《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史铁儿:《东洋人出兵》,《文学导报》第5期,1931年9月28日。
[9]笔者曾与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探讨这一问题时,方教授认为,抛开内容不谈,这类诗歌在左翼文学中并不在少数,此并非是作者创作能力的退化,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让更多文化层次不高的民众可以通过这种诗歌来了解、接受左翼政治主张。笔者同意方长安教授的观点。但本文在此处援引这首诗歌的目的乃是在于从其内容入手,分析瞿秋白这篇诗作所传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荒谬之处。
[10]企(周扬):《“国防文学”》,《大晚报·火炬》,1934年10月27日。
[11]立波(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35年12月21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