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海上航线的探险者
严格地说,开通欧洲至亚洲的海上航线是一群探险者,甚至是几代航海探险者的功绩,其中迪尼斯·迪亚士(Dias.Dinis),他是受亨利国王派遣,前往非洲各国、中东和开展贸易的船长之一。但历史上总是把第一顶桂冠加在非洲最南端好望角的发现者、葡萄牙航海探险家巴托罗梅乌·迪亚士(Dias. Bartolomeu)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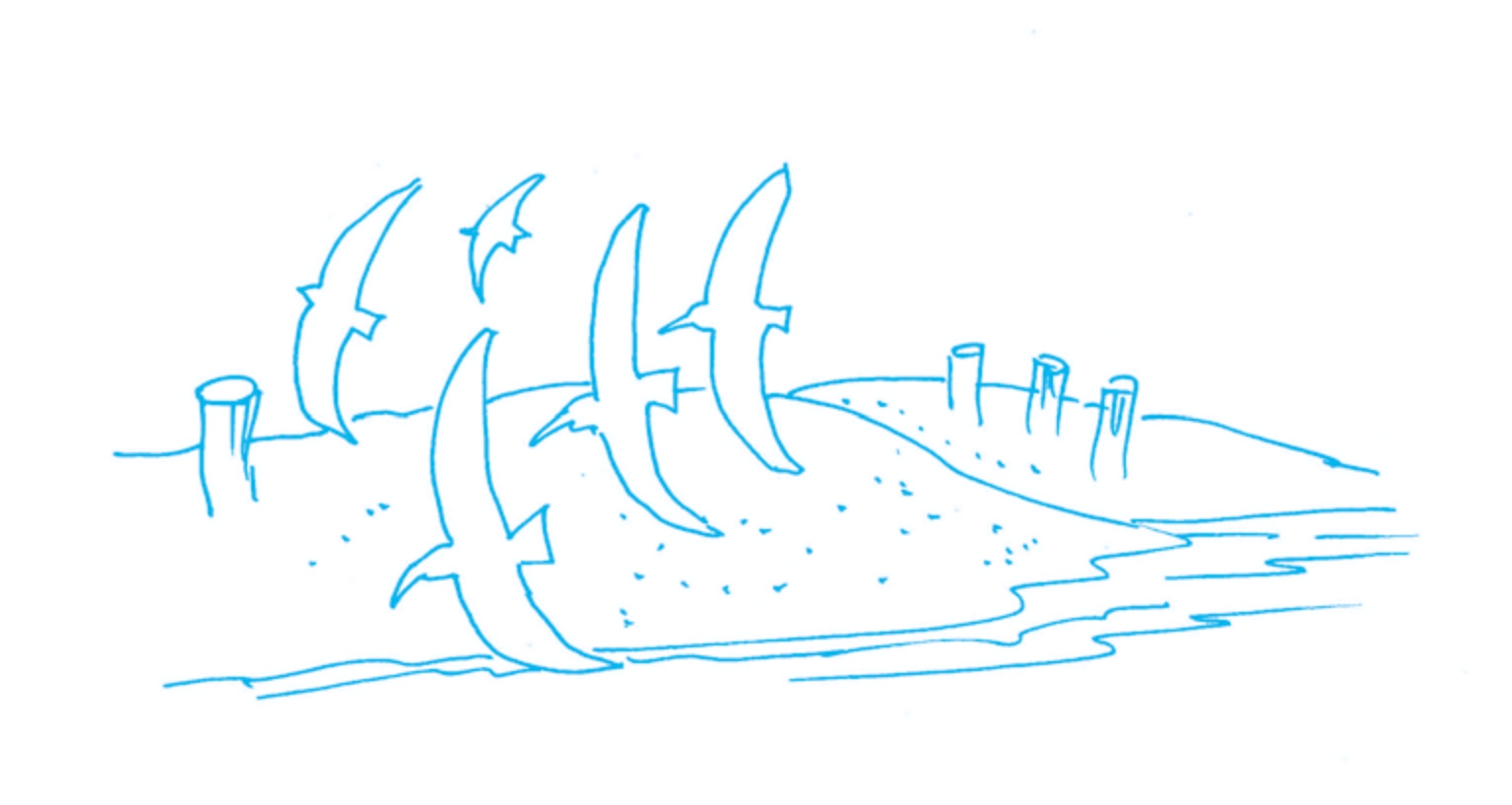
自从迪奥古·卡奥越过南纬20°的非洲西海岸后,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继续非洲南下探险的决心更大了。由于远航路程越来越长,条件越发艰苦,所以当若奥二世决定再次在非洲沿岸探险时,除派遣两艘各为50吨的军舰外,另外又配备了一艘专门装载粮食、淡水的宽体运输船,这艘运输船的确是相当破,破损程度简直可以随时扔掉。实际上出航时已有所考虑,那就是在船队返航时,如有必要,留下船上的铁器即可,至于破船,允许烧掉处理。
关于这次航行的船队组成,编年史学家若奥·德·巴罗斯有明确记载:“有两条船是武装船,性能稳定,配有重型武器,另一条装满了极多的补给品,因为过去许多船只都是因为没有补给而不得不返航的。船长的职务授给了巴托罗梅乌·迪亚士,他是若奥阁下家族里的一位绅士,是这条海岸的发现者之一。”与迪亚士在同一条轻便多桅帆船上的还有引水员佩罗·德·阿伦克尔,另一条的船长是若奥·英方特,他是一位年轻的骑士,他的引水员是阿尔瓦罗·马丁斯,那条摇摇晃晃的运输船船长是迪亚士的弟弟佩罗。三条船的人武装编制是五六十人。乘客中有六名非洲人;两男,四女。这是由著名的迪奥古·卡奥在发现刚果、安哥拉时从非洲带回的。这回,葡萄牙人聪明多了,不是把俘虏都当劳动力,或让他们皈依基督教,而是给他们以优待,让他们充当翻译,总之,让他们中的部分非洲人返回部落,去宣传,去做工作,为葡萄牙宣传,为葡萄牙人树立一个“和平、友善”的对外形象。这次放回来的四位非洲人,几乎成了葡萄牙人的使者,几位非洲妇女都衣着漂亮,并带上了黄金、白银和香料等货样。实际上,让她们如此包装返回非洲,葡萄牙人还另有目的,那就是,除为今后非洲贸易递上敲门砖,并取得非洲部落首领信任外,还想通过她们作内线,去打听寻找约翰长老国的消息。葡萄牙人以为,选非洲妇女充当这样的角色很合适,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女人通常都是弱者,不会卷入部落之间的战争。
迪亚士于1487年8月离开里斯本,在南下航行途中,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岸的一个要塞米纳进行了停留与补养,嗣后又航行到了安哥拉海岸安哥拉达·阿尔迪亚斯,所以在此停留,因为这里是迪奥古·卡奥抓非洲俘虏的地方,两个带来的非洲人让他们在此回家。为了便于探险,迪亚士的运输船在此抛锚,因为这里有大量的鱼和淡水可以补充。船上留下九个葡萄牙人看守。
以后的探险比较顺利,在经过南纬22°时,看到了由卡奥在克罗斯角最南端所立的标桩,之后沿遍布沙丘、十分贫瘠的土地绕行。在此后的航行中遇到南大西洋的大浪不得不在沃尔维斯湾抛锚避风。待滔天大浪肆虐之后,他们发现,这里原是一个五英里长的半岛,还是各种鸟类栖息的好地方,有敢于在汹涌波涛上飞翔的海燕,有敢于贴着海面低空巡游的海鸥,有在霞光中抖擞着翅膀,在头雁的率领下,排成人字形、彼此互唤着、豪迈地掠空飞行的群雁,在碧绿的水面上空展翅翱翔的水鸟,还有那鹈鹕、火烈鸟以及还有不少说不清名字的大群大群的海鸟。
迪亚士等正为观赏这些鸟类看得入迷时,突然发现有几只海鸟被长弓箭射下来。嘿,这真是好箭法,正当在欣赏箭法时,他们又看见不知从那里出来的几个土著人到这里来放牛牧羊。为了不伤害他们,迪亚士等只是追踪几个土著人的足迹去寻找其居住地。果然有所收获,他们发现这里是非洲南部霍屯族人的居住区,其居室很有意思,是一种用牛皮搭起来的圆锥形的小包蓬。
迪亚士在这里避风休息,停留了好几天,后来,他们又航行了两个星期,顶着猛烈的南风,逆风前进,终于很费劲地在卢得立次湾抛锚,在这里,他们把其中的一位非洲妇女放上了返回家乡的海岸。

迪亚士最后一次看到非洲西海岸的陆地,大概是现在的开普省塞达尔堡北边陡峭的红色马奇卡马高地,实际上,离葡萄牙很多航海者为之长期奋斗探寻的非洲之角只差不到200英里了,尽管迪亚士并没有意识到。
迪亚士看到马奇卡马高地确实也已很不容易了。原因是,自离开多里斯山之后,就一直在与强劲的南风搏斗着,为了不致在接近海岸时把船撞坏,迪亚士毅然决定把船转向开阔的大西洋,一直向西。尽管迪亚士是位有耐心的船长,然而,这回他也差点对船只在逆风中的航行丧失了耐心。须知,在这种情况下的航行已经大半个月了。根据他长期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经验,只要驶往看不见的大陆的海域一定会遇上顺风的,但这次可是意外了,真是老航行家遇到了新问题。请看编年史学家罗斯的记载:是猛烈的北风把船吹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奇怪的是,在南部非洲仲夏的一月份,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莫明其妙的北风。
在茫茫的大西洋上,迪亚士的船又向西南方向颠颠簸簸地行驶了13天,由于风力过猛,迪亚士不得不把风帆降下来。按照迪亚士的估算,船只离海岸已相当远了,于是下令掉头向东航行。令这些航海者不解的是,南半球的仲夏,涌浪之大像小山一般,这且不说,海水还这么冷。为了及早能见到非洲陆地,迪亚士在脑海里不断地估算着航海人心中的三角形,但却一直没有发现陆地,于是又再一次地改变航向。怎么老是见不到陆地呢?甚至东方地平线上连陆地的影子也见不到。迪亚士自问着,后来,迪亚斯决定向北航行。当然,那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非洲最南端是现在南非的厄加勒斯角,其纬度是南纬34°51′。而迪亚士的船还一直在咆哮的南纬40°的纬圈带上航行,怎能找到陆地呢?只能在风暴圈里遭罪受。不过,那时的迪亚士还自信着呢。
迪亚士决定向北航行是正确的决定,终于在1488年的二月初,船员们在极端疲惫、简直个个像散了架似的状态下,再一次见到了非洲陆地,总算惶惶不安之焦虑得到些平静。其实,许多船员在那咆哮的南纬40°上航行时,他们不停地在向上苍祈祷,请上帝保佑,双手不断地在胸前比划,口里念着,阿门、阿门。尽管发现了新的非洲陆地,使迪亚士又不断地向自己提出疑问,不对啊,历来发现的非洲海岸线都是向南的,而现在呈现在面前的海岸线怎么是向东了呢?殊不知,迪亚士已经绕过了非洲之角,但迪亚士那时不相信这一点。
可以后出现的事更古怪,迪亚士继续向东航行,而海岸线依然不断地向东延伸,且越来越远。迪亚士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搞错,用凉水冲了好几次脑袋,一而再、再而三地揉揉自己的眼睛。这样,他才相信不会错了,甚至用他们所使用的很简陋的航海仪器也可以计算出,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离博哈多尔角以东有两千英里之遥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正处在埃及的正南方。这才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里海岸线几乎很平直,也很少遇到岛屿。当见到陆地景色时,这些长期海上飘荡的船员们一下子兴奋起来,陆地啊,久违了。其实,航海人见了陆地就高兴,况且,这里海岸可真美,那里的花草,从船上就隐约可见,气候也舒服。眼看着这生机勃勃的景象,勾起了船员们对家乡的思念。怎能不想家呢,屈指算来离家远航已七个月了,这一路上风风雨雨的煎熬,特别是在风暴40°圈中航行时,真是要了命,不少老船员都在吐酸水、苦水,甚至是绿色的胆汁,年轻的船员则在不断呼唤着,哎哟,姆妈。船员们可真是想家了。
后来,迪亚士在航行中发现了一条河的河口。河口的出现又引起了船员们的惊喜,这难道是船员们神经出问题吗?其实,这都是真实的反映。须知,流入印度洋的河流就是很少,著名的也就是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河、伊瓦洛底江、赞比西河等几条。当然,那时的迪亚士心里很明白,由于一路上很少见到河口,难怪船员们又惊喜起来。这种心情,对长期居住在陆地上的人来说,是不会产生的,也想不到长期远航的人会这么激动。
迪亚士原想满足船员们的欢心,上岸登陆,可是天公不作美,冲岸浪太大,没能如愿。由于看到那里有人扬鞭放牧,迪亚士就把此河命名为“多斯瓦凯伊洛斯河”,即“牧人河”。
1488年2月3日,他们来到了旁边的一个海湾,那里有个小岛,离大陆很近,岛上栖息着很多海豹,由于海豹叫声像驴,后来有人称它们为驴企鹅。后来发现,流入该海湾的河流也是与众不同,说是河中“长满了芦苇、蒲草、薄荷、野橄榄树,还有与葡萄牙完全不一样的花草和树木。”
在引水员阿伦克尔的领航下,登岸上陆后,他们在山丘上看到一群乳牛和几个半赤身露体的人,于是,他们用欧洲不值钱的小玩意竟换来了牛和羊,使船员们几个月来第一次品尝到了新鲜的牛羊肉。
也许是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激怒了放牧人吧,当迪亚士派人去海滩附近找淡水时,迪亚士被扔过来的一块石头打中了,船员哪里肯依,进行还击,一个牧人中箭射死,其他牧人赶着牛羊仓皇逃走。这就是葡萄牙欧洲人对从未知晓的民族的初次见面礼。待走近看时,那个被射死的“黑人”的头发像“绒毛”,其肤色像“枯黄的树叶”,比非洲西岸的黑人的肤色要浅得多。
这个初次被欧洲人认识的南部非洲黑人,究竟是什么人种并不清楚,只是说,是南非的土著人吧。但迪亚士等发现,与这里黑人在作“货物”交换时,黑人的说话虽不解其意,但具有明显而独特的吸气音,发出的声音多为“hot”和“tot”,很怪。以后荷兰人来了,讨厌他们的结舌,干脆称这些土著黑人为“Hottentot”,译名取音译“霍屯督”人,实际是贬低南非黑人。但那里的黑人,自称是“科伊科伊人”,在南非黑人的心里,自己是“人中人”、“真正的人”。
迪亚士离开“牧人港湾”(现今的莫塞尔港)后,继续向东航行,看见一座巍峨的山顶,就称它为埃斯特雷拉山。其实,这是位于葡萄牙本土东部的一座山峰名称,也是葡萄牙的最高峰,海拔为1991米。迪亚士何以取此名,可能的用意是,船员们实在太想家了,让他们以后看到此峰就会想起葡萄牙。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让大家别忘了,这里也是葡萄牙领地,至于究竟为何选取此峰名?随着迪亚士的作古,没有人再去细问了。之后,他们抵达了一个面向海洋宽阔的海湾(即阿尔戈阿湾),从这里起,海岸又缓缓地转向了东北,向印度方向伸去,迪亚士心里明白,也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们的航船已绕过非洲全部的南海岸,这里应该是印度洋了。可船员们并不高兴,以为根本还没有绕过非洲最南端的海角。尽管迪亚士对继续探险的热情很高,但船员们则不肯再前往,一位名叫巴罗斯的人这样记载:“由于人们都已筋疲力竭,再加上被航行经过的大洋上铺天盖地的大浪吓破了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埋怨起来,要求再也不要走远了。船员们说,给养就要用完,应该回去寻找他们来时留下的运输船和补给品,他们说,留在运输船上的人大概都快要饿死了。船员们说,这一次航海发现的海岸很长了,也已经够多的了。最好的办法是,回过头去寻找已要落在他们后面的那个最伟大的非洲之角。他们表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继续前进了。”
尽管迪亚士多么想继续发现,但也无可奈何,于是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个文件,并让大家在文件上签字。最后仍然恳求大家,再沿着这条海岸多走两三天,他许诺,如果仍然看不到什么,就返航回国。
在航行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他们航行到凯斯卡玛河口的外边,迪亚士认为应在那里去树立标志,无奈汹涌的波涛又加上不停咆哮着的冲岸浪,船只无法靠岸,迪亚士正在大为失望。正当掉头往回走时,迪亚士抓住了一个机遇上了岸,把醒目的标志立在阿埃霍埃克的顶上。迪亚士真是不忍现在就离开,但前进不得,停留也不行,无可奈何。巴罗斯有记载:迪亚士“怀着极大的痛苦和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这里,“就像离开他永远被流放的可爱的儿子一样”。在返航途中,一路测量,包括绕道南大西洋期间错过的海岸。
6月6日,他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迪亚士渐渐地靠近了非洲的最南端,他们到达了一个“雄伟壮观的海角”,这是花岗岩的奇岩怪石,它远远地伸向海上,从侧面看是座山和一石锥,这就是非洲南部的最南端,也是一个最尖端,在周围沙滩的辉映下,更显得突兀与雄伟。在返航途中,在普林西比岛靠岸时,迪亚士又搭救了前来索尼尔河口探险者中的一些幸存者。终于在公元1488年的12月返回葡萄牙的塔古斯河。行程1600英里,历时15个月。
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听取了迪亚士的报告,迪亚士诉说在非洲南端的风暴实在太大,我把最南端的海角称为“托尔门托”,这确实是“风暴之角”。但国王另有想法,这一发现该有多好啊,梦想即将实现,葡萄牙人现在已经可以绕过威尼斯和伊斯兰帝国,勇敢地进入印度洋了,这是良好的希望,怎能叫风暴角呢,应改称为“好望角”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