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开迪涅莱班的时候,拿破仑在队伍前头领队,所有的迪涅人都走上大街,欢送声响彻城市上空。姜是老的辣,将是老的好,这帮常年征战的拿破仑家军,对皇帝的惯数心领神会。出城后,队伍自行换成行军状态,领队人变成波兰骑兵和掷弹兵,行军井井有条。队伍沿着布莱恩河的右岸前进,晚上6点多钟,暮色降临,走到布莱恩河和阿尔卑斯大河迪朗斯河(Durance)的交界处,出现了一座大大方方、颇有气派的城堡,这里便是小镇马利热的进口。马利热(Malijai)的名字来源于法国南部的方言奥克西当语(l'occitan),拆开来看为Mal i Jai,就是“睡不好”的意思。小镇在两条大河交界处,布莱恩河与迪朗斯河脾性都比较泼辣,常犯淹灾之事,当然让人“睡不好”了。无巧不成书,拿破仑在这里度过的一夜,几乎没有合眼,也没有睡好。
小镇落在上阿尔卑斯地区的山脉中,方圆二十几公里而已,最显眼的标志性建筑就是这座名叫“城堡”的城堡,建于18世纪70年代。城堡为当时路易王朝的一名地方财政官所有,城堡内部均为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钟情的吉普塞利(Gypseries)石膏雕刻装饰风格,墙花绘画繁复绚华,典型的宫廷风雅。因为这是小镇最体面和宽大的住所,当地市长便把拿破仑安顿于此。城堡主人诺季尔先生是亲路易王朝的,打猎回来见拿破仑一行已经入驻城堡,彼此相见出现一个“你不情我不愿”、令后人寻思逗趣的场面。诺季尔是路易王朝的铁杆派,面对拿破仑只以“先生”称呼而不是“皇帝”或“君主”等尊称,以此来表明他的立场,但苦于路易十八的军队追不上拿破仑,面对这大批军马,也只好由之任之。老皇帝见他这模样早就心生不快,又得知诺季尔第二个兄弟长驻马赛,更是让他心烦,要知道连夜追赶他们的马塞纳大将军,正是从马赛而来。无奈天色已晚,车马劳顿,此处宽敞暖宜,心里再不情愿,也得暂歇于此,他挥挥手道:“今晚打扰您了,我会留下饷酬的”,然后关上房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述者笑着跟我说,我笑着在那听,却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笑的是仿佛看到一位在外骁勇善战的斗士,回家后褪下战袍换上睡衣,伸个懒腰那般真实平凡的可爱。这位房主因为势力而忍让,老皇帝因为物资而屈就,不管是庸人还是皇帝,在生活里都会面临两个举重若轻的字:妥协。皇帝丢开权杖也是凡人,谁都有需要别人的时候,哪怕是一个敌人。在生活面前,吃喝拉撒永远是最大的需要,生活可能不认皇帝,但也许会认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明白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皇帝还没有心情伸懒腰。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去床上休息,而是坐在摇椅里忧心忡忡。这倒不是为了诺季尔,他所忧虑的是下面要攻克的重镇锡斯特龙(Sisteron),这是进入多菲内省区的门户之地,一个历史性的防守重镇,照他自己的话“一旦进入多菲内省(Dauphiné)的大门,法国就是我们的了”。因此,开路将军康布罗纳已先行去锡斯特龙,试图用外交说服的方式来开城,拿破仑正焦急地等待他的音讯,等待之时则不断书写“告士兵宣言”来消磨熬人的时间。到凌晨2点多,康布罗纳凯旋归来,老皇帝悬着的心总算稍有放松,吃了些简餐后,便于5点整装待发。下楼时,小镇的百姓们全都聚集在城堡楼下,静静地等他起身为他送行。更出乎他意料的是,昨天那个打猎回来胡子拉碴的诺季尔,这会也梳洗整齐,听说老皇帝为操虑行军而一夜无眠,可能感动于他的执着与坚定,正恭敬地向他行礼。生活带来的惊喜永远超出想象,拿破仑离去后,仆人在他房间里发现一页他亲手写的“告士兵宣言”,被扔在火炉里,却奇迹般的幸免于火苗而保留下来。这是历史上存留的唯一一张拿破仑亲笔书写的“告士兵宣言”,无意中成为他给诺季尔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

城堡原始大门上的牌匾记录:“1815年3月4日到5日的夜晚,拿破仑在此过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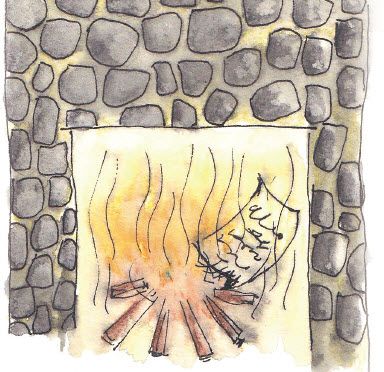

马利热镇长办公室
现在这座城堡的底楼是马利热市政府大厅,被列为历史保护遗产建筑,而楼上两层则都是私人住宅。拿破仑曾留宿一夜的房间,现今的主人并不希望被打扰,对外一律匿名。城堡门边的墙上有一块石牌匾标着“1815年3月4日到5日的夜晚,拿破仑在此过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以拿破仑为标榜的缀物。我问起为何这里不像有些地方一样修个博物馆或展览厅之类的,市政府人员坦白地说这是由于经济原因。生活,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英武皇帝的经过,一定给这个地方带来过传奇般的光辉与人文价值,然而当皇帝成为传说,法郎变成欧元,资金就是发言权,把这座历史建筑交给有能力的人各自承担,或许是保留它的可行方式,至少在这个经济危机四伏的时期。小镇市长得知我们一行将为中国读者介绍“拿破仑之路”,特地将她的办公室大门打开,让我们参观室内的装饰。精致的墙纸画与遍布天顶的石膏雕塑经常出现海船、美人鱼等与大海相关的形象,是典型的18世纪上普罗旺斯地区布尔乔亚上流阶层的风格。当我们细细参观完后,才发现女市长不知什么时候已悄悄离开,大门另一边的工作人员也都安安静静的,我们离去时他们对我们点头一笑而无多语。“这里的人都这么低调的吗?”我不禁好奇。“也许这算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吧。”陪伴我的女孩随即带我去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穿过宽阔的迪朗斯大河,来到其左岸的青山丛中,我们在绿赫山(la Montagne de Lure)前停下,沿一条山径小道往上走。天飘起濛濛细雨,烟雾缭绕,山色深浅不匀,埋步于此,仿如寻找不为人知的宝藏似的,让人隐隐地激动起来。半山腰不到的地方,一座古罗马式教堂赫然立于眼前,这是此片地区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保存相对完整。女孩指了指教堂对面的山崖,让我看一个草木掩映的山洞。“大约一千多年前,有一位隐士居住在这里,进行灵修,人们称他圣多纳(Saint Dona)。他本人深谙山间草木,曾帮助很多人治疗疾病,并以祈祷和传授教义的方式给予人们心灵安抚。之后,围绕他又产生出各种与龙蛇相斗的传说。他去世后,人们难忘他的帮助,年年来这里送花或祭奠品,一直持续了千年。直到近年来,由于山体有变,山洞变得危险,才不再对外开放。”


隐居,对我来说是一个带着莫名吸引力的词,而真正目睹隐居状态,这是第一次。和很多人一样,疲惫于城市的喧嚣,又放不下它繁华的精彩,我们时常在狂喜与低落中上上下下,“隐居”仿如那个在最伤感的时候听你述说的老朋友,带来让人踏实的归属感。一句“大隐隐于市”,是我们集体密藏的解药,迷乱时拿出来闻香,告诉自己原来我们都有专属自己的山洞,可以在里面唱自己的歌,不去理会外面的林林总总。真正的隐居,起源于天主教徒,是一种自愿与世隔绝、抵抗诱惑,在绝对的清净中,一个人与自我灵魂进行对弈,以求在灵魂升华中接近天神。历史上可追溯的第一个隐居者为250年间一埃及天主教徒安东尼奥乐高,他只身前往上埃及的大沙漠,灵修冥想直至生命结束,从此开启了隐士之路。说到隐居,很自然地联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是一部将隐居式生活带入人们臆想空间的泰斗之作。闲庭野鹤云湖间,人可思考又可不思考,这种生活方式使无数城市人心向往之。实际上,他的这段隐居生活也就持续了二年零几个月,说是隐居生活,不如说是隐居体验;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态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生短暂,当尽其荣,或许态度更重于方式。连拿破仑都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妥协与疲累,会关起门来留一个人静思,第二天还不照样启程,继续前进。
看着烟雨中的多纳隐士洞,可以想象他卧膝冥思的状态,伴着山里间或几声鸟鸣,清心寡欲,终其一生。灵性精神,不见形状,却充盈于这整片密林山间,无理由地令人动容。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无声片刻里,听见了自己的灵魂。这应该是隐士们用一生孤寂为人间换来的赏犒,提醒我们灵魂的存在,并在自我灵性的对话中修复自己。然生活皆在选择,在此他有他的至纯圆满,在外我有我的花花世界。在自我隐匿的一刻里,我们回归内心,学着在个人深处的精神世界中重新建立,之后依然一头扎进世事浮沉,不问孰好孰坏,但求无怨无悔。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