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帕米尔高原之后,荒凉的峡谷戈壁,美丽的高原湖泊,偶尔在路边出现的毡房、牧民和羊群,永远在视野中的连绵雪山与草甸,一路上的高原风光实在令人迷恋。尤其是几座大雪山,几乎一直伴随着我们,其中就有海拔7546米、被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在幕士塔格山脚,我们能清楚地看见陡峭山崖边的雪不断地崩塌。过喀湖时,有风,湖面上波涛回荡。“狼”说,如无风,湖面就像一面光洁的镜子,可以万分清晰地看见倒映在湖中的慕士塔格峰和蓝天白云,真的是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哪是真景哪是幻境,此时摄影出来的图像,如同仙境。喀湖位于素有“冰山之父”之称的慕士塔格和公格尔峰之间,公格尔共有九座山峰相连。传说公元前10世纪,西周第五代君主周穆王即位第十三年,即驾车西游到此地。唐高僧玄奘也曾游历于此,那时哪里有什么交通工具,玄奘是骑马,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险才看到如此的美景。而周穆王的车也不知是否马车,能否真的可以颠簸到此。
帕米尔高原曾经是古代新疆通中亚和南亚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由于地势高寒,行旅艰险,因而充满了神秘和浪漫的气氛。在阿克陶县布伦口,我们还看见有倾圮的石屋驿站遗址。那时的骆驼队、马队,是根本无法与现代车辆相比的,那需要多么坚韧的精神才能长途跋涉于高寒之山啊。由此可见,在古代,商人是人群中最想争取生活幸福的人,为此他们可以忍受一切困难承担一切风险。
这一路有意思的,还有公路边上的服务区。那就是立一块木牌子,上写“休息区”,除了路边上有一片还算平整的地面,没有小店,没有厕所,更没有加油站,啥也没有!据说只是作为开长途货车的司机在此地停车睡觉的地方。在高原开车,必须算好里程加足油,路上是没有加油站的。因为从喀什出来,我们还去看了冰川又沿原路返回,路上就没有加过油,终于,离塔县还有五六十公里时,我的车上指示灯告急,马上就没油了!

坐在路边的孩子
坐在我车上的几位女士立马慌神了,婉婉说,如果天黑到不了塔什库尔干,停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会冻死人的。其实,我一路上已经很小心地省油了,好在前方的路坡多,一个接着一个,而且都比较缓、比较长,于是我开始发挥多年来练就的过硬本领:所剩无几的油,仅用在第一个坡时挂五挡帮助车上去,后面基本上利用下坡的动力溜车,第二个坡也无需挂挡就可上去,下坡时又能积蓄能量上第三个坡……就这样将一辆几乎没油的车一直开到了塔什库尔干,比另两台车还到得早。


芦苇出生在这儿
在这里,天黑得晚,都九点多了,还像黄昏时光。街上走着黄头发或黑褐色头发、高鼻深目的塔吉克族人,这里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曾看过一个纪录片,介绍塔吉克族人训鹰的过程。街道两旁,我看见了人与鹰的石雕。而小时候看过的那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们住的宾馆大厅,就贴有电影中那位美丽的古兰丹姆扮演者的生平故事。看了介绍后我才知道,她当时被导演选上时,还是个中学生呢。不过,后来随着电影受到批判,她似乎度过了很艰难的一段日子,如今看上去非常苍老,美丽早已不复存在。
第二天,我们一行三辆车向中国最西端的红其拉甫开去。在媒体上老看到中巴公路以及巴基斯坦的动荡之类,大家也都想看看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高原雪峰异国风情倒底是个啥样。车行100多公里到了红其拉甫边检站,却被告之要回到塔县买门票,80元一张,否则不让上去,好话说了半天,无果,只好掉头下山又向出发地开回去。又走了100多公里,回到县城买了票,接着马不停蹄又向红其拉甫奔去,这次再去就只有我这一辆车了,车上只有我和云云、芦苇夫妇和婉婉,其他人都懒得再跑一回刚跑过的路,留在塔什库尔干逛街了。
红其拉甫国门倒是挺雄伟,而巴基斯坦那边却无任何建筑物以及边防哨所之类,一眼望去,只有无边的山和一条土路。天空飘着雪花,寒冷而空旷,整个大山上只有我们一行五人,芦苇说这里反正没人管,把车开到巴方远处看看,我说那可不敢,万一咱们这边的边防部队发现会有麻烦的,要是开个枪啥的就更惨了。
雪越下越大,几个人傻乎乎地在两国交界处来回窜,照了些照片,再没啥可看的,只好上车返回。
刚下到山半腰,一个穿着大毛皮靴羊毛大衣的武警战士把我们拦下了。我们上山时已见过他,他拦车说带他上去,由于我们车已满员没法带,我们玩完下山才又碰到了他,他还在往山上走。我也不是不想带他上去,知道他走上去也挺累的,实在是我那众泰车太小,后座坐三个瘦人但都已穿着冬装,觉得挤得慌,他五大三粗的,还穿着大衣,别说坐了,挤都挤不进来。
他拦下车问:“你们到巴基斯坦那边玩了吗?”我们说不敢过去。他说:“刚才叫你们带我上去你们不带,我要是上去可以带你们到那边玩。”我忙说,那咱们想办法挤挤再上去吧。谁知道那小战士幸灾乐祸、带着嘲弄的口气和表情一挥手说:“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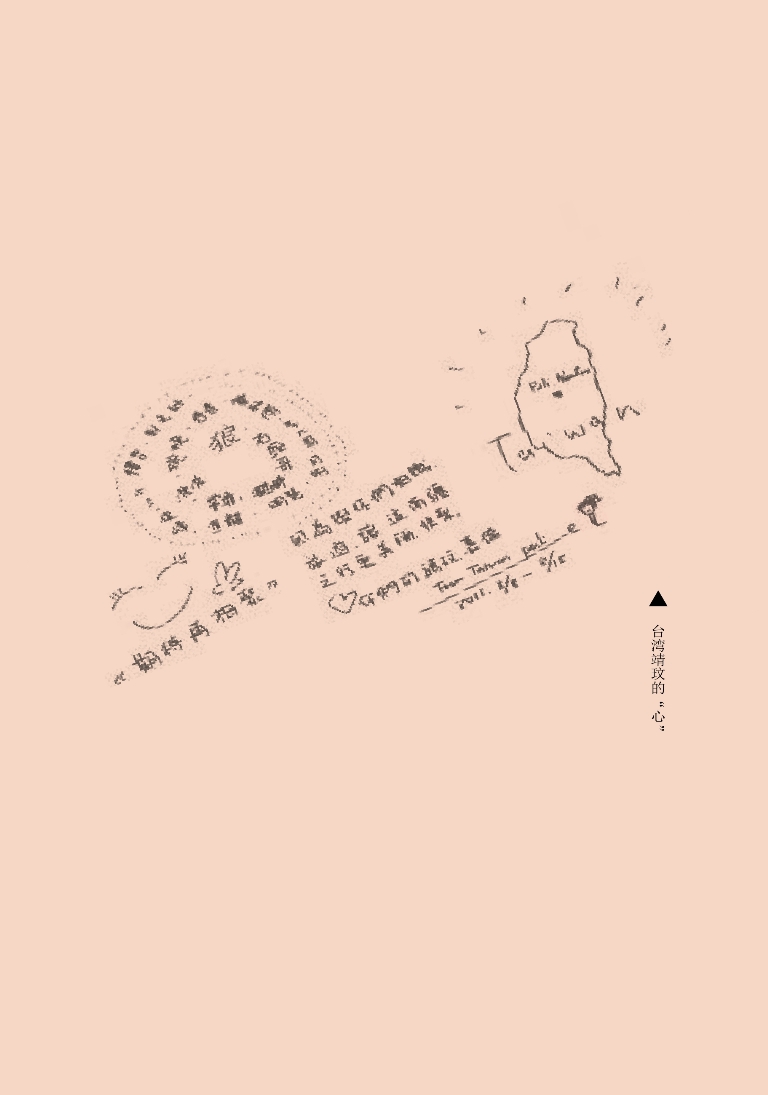
听他说了声“晚了”,反而把我们乐得够呛,真像个调皮赌气的孩子说话。再细看看那小战士,个子很大,脸却是张名副其实的娃娃脸。云云说,他怎不先说可以带我们去那边呢?悔不该当时把石头换下去让他坐!石头一脸无辜地说,为什么总是欺负我?
望着那小战士得意扬扬地朝山上走远,大家叹气说,也是我们活该,不做好事所受的惩罚,再怎么说也是晚了。

去塔什库尔干

第二天,我们从中巴口岸红其拉甫回来后,“狼”就开始指挥大家工作了。我们沿途停车,采集着各种植物小果:小红果,小黄果,还有带小翅的灰翅果。有一种红果很难摘,枝条上刺很多,学名叫大果蔷薇;另有一种小红果,小小的圆圆的,学名居然叫白刺。有一个细节让我对“狼”这个年轻人充满好感,哪怕是在无人区,他也会将我们产生的所有垃圾随身装走,一路上,大家喝空的矿泉水瓶子,都被他塞在车顶行李架的缝隙中,一个接一个,最后成了很美的装饰。
各国都在研究从植物中提炼能源,中国也不例外。“狼”所进行的工作,也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环节。
“狼”说,虽然有时也会抱怨工作条件艰苦,但还是很喜欢这种工作。有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不用和人勾心斗角,不用成天揣测别人的用心,不用设计人也不会被人设计,不用和行人接踵摩肩,不用闻汽车尾气。而且,还能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野生植物之美。离疆前,“狼”送了一本精美的新疆植物图志给云云,里面一幅幅让人心动的植物照片,都出自他的拍摄。今年春节,“狼”打电话时说,过完年,他会再寄一本新的植物图谱送给我们。从帕米尔回到喀什再进入阿克苏地区后,黄土随着大风,刮得看不清几米远,但我们还是找到了那个标明“三团”的路标。在这里,芦苇要举行一个小小的个人仪式。没来之前就知道,她出生在这儿,父母是当年支边的上海知青。下了车,黄沙刮得人睁不开眼,我举一束路上摘来的无名草花献给芦苇并喊道:“怪不得你小小个子还能吃苦啊,原来从小就生在这么苦的地方!”
芦苇在这里长到六岁,又随父母到了甘肃。十二岁才随父母调动到了江西。也许出生在西北荒漠,天生就带着不羁的个性,她曾一人跑东北漠河,跑云南雨崩。就是从雨崩开始,迷上了户外。偏偏芦苇嫁了个上海人石头哥。大家都知道上海人大多是中规中矩,从不乱来,顾家而且会持家,特爱老婆的。幸亏有了这最后一条,才让芦苇最后得逞吧。她的先生虽叫石头其实并不硬,本名中有三个石头而已,长相极其忠厚,圆脸大耳,善良细心,做饭炒菜那是一流,我想不是老婆爱上户外,他可能永远是个居家的好好男人。因为是一个单位的,我认识他们较早,看着爱玩爱折腾的芦苇如何将她的石头哥一步步改造过来,成了她忠实的驴友伴侣,这过程当然十分有趣,也历尽艰辛,故事无数。我所知她获得成功改造的第一次,便是带先生徒步进了雨崩。那可是一条真正的驴友路线,没有相当的体力和毅力,很难坚持。岂料,石头悟性极高,一下子便爱上了户外,让芦苇觉得胜利来得太容易。从此,他俩开始一次次走西藏,走新疆,乐此不疲。此次进疆,石头便成了大伙最细心的管家,灌茶水,买食品,别人不用操一点儿心。在乌市“捡”来的驴友中,有一位台湾姑娘叫靖玟的,十分喜欢石头,一路上有事没事都叫着“石头哥”,我调侃说,靖玟喊“石头哥”软软的声音像港台片中的女生,太好听了,大家干脆逗这可爱的姑娘让她一遍遍地叫“石头哥”,芦苇根本不在乎,还把靖玟甜美嗲嗲的声音录成了手机铃声,说是永远让石头哥记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