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不幸
婚后十一年,我从来不看书。我不看书不是因为我不识字。想当年在大队读耕读中学时我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不看书是因为我没有空,我每天得上责任田责任山劳动,回家还得照顾孩子,服侍丈夫,孝敬公婆。因此,我翻开书的时候许多字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拿不准该读什么。就像走在大街上看到许许多多似熟非熟的面孔一般。
那天我看书纯属偶然。我帮丈夫捡拾书桌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书本。他总是喜欢把什么东西丢得乱糟糟的,你在前面捡他在后面丢。
我帮丈夫整理头天晚上他摊在桌上的一大堆书,偶然看见一本摊开的词典上有“妻子”这一条目。我心里一动,接着往下看:“男女结婚后,女人是男人的妻子。”哦,原来如此!书上的解释也这样干巴巴地没带一点感情色彩。难怪我和国宝结婚后这日子这么难熬这么令人苦恼。原来我心里的种种烦恼都是自作多情都是对国宝的过分苛求。
女人成为男人的妻子是幸福还是不幸?书上没写。要不是书上出了毛病就是我脑瓜子出了毛病,我总觉得为人之妻是人生的最大不幸。
我不大爱动脑子。我丈夫也常常这样说我。我不动脑子是因为我根本没空坐下来想事情。白天在山上一颗汗珠摔八瓣。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包谷地里,我蹲在半人高的包谷棵中,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包谷叶子钢锯片似地撕割着我的脖颈,汗水浸过,又咸又辣。正午,望着眼前无边无际的包谷地,我眼睛阵阵发黑。这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尽快地将包谷地的杂草扯完。晚上回到家,我喂猪奶孩子,弯腰拱背地匍匐在灶门口吹火。吃完饭,手软脚软,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孩子吮奶,像是吮血管里的血似的让人难受。我哪有心思去动脑筋!孩子还没吃够,我先睡着了。
偏偏国宝说我不爱动脑子。
国宝是我丈夫的小名。我俩一块长大,一块捉蚂蚱来逗蚂蚁,看千百只蚂蚁浩浩荡荡地将蚂蚱抬进墙洞中去。后来,又一块往书包里塞一瓶酸辣椒上耕读中学寄宿。耕中毕业后一块回乡干革命,一块上台演出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他扮演党代表我扮演吴清华。吴清华雨夜获救,一头扑进党代表怀里。“党代表”就用指头轻轻抠我的背沟儿。1977年初我们结婚了,婚后一块给他复习功课。1978年他考取了师范学院。从那时起,村里老辈同辈以至下辈的人都羡慕我。我昂首挺胸从村上那条牛屎街上走过,脚步轻飘飘有如腾云驾雾。一种甜腻腻的东西塞得胸中满满的像要从喉腔溢出。
我虽不爱动脑子,可如今几年过去也算而今识尽愁滋味了。当年那点得意劲早已荡然无存。每天孤独地荷锄下地,看见别人成双成对上山砍柴下田插秧,我肩上的锄头好重好重,压得我直不起腰来。
国宝是我丈夫的小名。可自他从学校毕业后就不喜欢我这样叫他。我们的第二胎是在他毕业后的第三年生的。小家伙虎头虎脑,一副不替古人担忧的福相。他二舅为他取名龙生。舅舅为外甥取名是我们这里的老习惯。可国宝不喜欢这名字。“俗气!”他说。然后就着灯光翻了半天字典,末了将右拳狠狠击在左掌上,“潞潞!就叫潞潞!”于是从那后小家伙就改名叫潞潞。
国宝从学校下班回来。搬张小凳坐在门口的南瓜篷下看书。一支烟在他指间悠悠地燃着。他看一本足有一块砖头厚的硬壳书。时而紧锁双眉,时而低声哂笑。忽然她用力将书本一拍,咕咕哝哝地说了句什么,站起来在南瓜篷下来回踱步。“胡扯!纯粹是胡扯!”他忿忿然有如谁当面骂了他的娘。又像当场识破了什么弥天大谎。
我知道他又该喊我了。果然。“春花!”春花是我的学名,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正儿八经给起的名字。“春花!”丈夫又喊了,“那猪叫得烦人,你干什么不把它喂了,也真是!”后面这句话说得很低。我赶紧往鼎锅里兑一瓢水,盖上锅盖,然后拌好猪食,朝猪圈奔去。丈夫经常埋怨我要喂猪呀鸡呀什么的,搞得满院吵吵闹闹邋里邋遢。可这猪我不喂行吗?孩子的奶奶68岁了,近年来又喘得厉害。古话讲男怕三六九女怕二四八,万一她挨不过这一年,没头猪……
我把猪食倒进猪槽里,这个呆子连忙直起脑壳往槽里拱,再不叫唤了。忽然腰上有一股热流慢慢往裤头下扩散。潞潞在背上撒尿了。
回头看国宝,他又心平气和静地坐下看书了。只要他不发脾气,我苦点累点也心甘情愿。
我今年虚岁35。35岁的女人大半还不甘寂寞,白天苦点累点咬咬牙也就过去了,晚上的孤独却让人无法忍受。
潞潞的痱子近来越来越红越来越密了。睡觉前总要我抓痒痒。我来不及洗净拌猪食时留在指甲缝里的糠屑,便替他抓痒哄他入睡。
牛么牛,犁大丘,
买匹马,下扬州。
扬州姑娘会打茶,
什么茶?黄豆茶……
“俗气!”国宝突然撂下书本,一声断喝。我回过头去,见他坐在桌前,满脸恼怒。我惶惶然,不知他究竟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气。
“你就这样给孩子灌输知识!”他声音放轻了些。我也恼了。我虽不敢像他那样大声吼人,可心里气的不行。我每天披星戴月,累死累活,就为了换这份气受?
“我就会这些,要不,你来陪潞潞睡。”我心平气和地对国宝说。
“我?”他吃惊得瞪大了眼睛,“笑话,我陪孩子睡!”
屋里出现了长久的沉默。一只甲虫从黑暗中飞来,卟地撞在窗纸上,掉下窗台。潞潞带着不尽意的情绪入睡了。我倒出奇地清醒,睡意全无。
“唉!”国宝突然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知道他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看他脸上,悲哀得如同刚死了亲娘一样。
睡意渐渐袭了上来。眼皮沉重地合上了。我觉得一个人只有睡着了以后才省心,什么烦恼什么忧愁通通忘得干干净净。我真想睡它个一年半载。可是不行。田里的禾苗刚打胎,可有大半生了虫。要买一瓶杀虫醚。30多块钱。丈夫说还没有发工资,手头没有钱。他除去每月交给我90块伙食钱外,就没再多给过一块半块。潞潞吵着要吃冰棍,还是我一个钢镚一个钢镚打发的。明天起早一些,回娘家打个转,跟孩子二舅借30块钱,先把农药买回来,然后跟岩生借台喷雾器……
国宝又伏在写字台前埋头写起他的小说来了。他曾不止一次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他要写一部小说,一部让全国人目瞪口呆的小说。可划划拉拉几年了,却不见他写出点什么来。
撕啦!撕啦!国宝总是写了又撕撕了又写。那撕啦撕啦的声音伴着我沉入了梦乡。
国宝什么时候上床我不知道。潞潞常拉梦尿,我又没空每天换洗,国宝嫌尿骚味重,总是另睡一头。要说女人就是命贱,我嘴上不说可心里却有一种耿耿的企望。刚结婚那阵多好啊!我每夜枕着他的手臂,听他低低的鼾声,心融化在一种妙不可言的境界里。这种令人销魂的夜晚此生此世怕再也享受不到了!
“春花春花。”国宝用脚轻轻踢了踢我。我醒了,其实是半醒半睡。我把脚跟伸过去,在他脊梁上一上一下地厮磨起来。我脚后跟一年四季裂口子,粗得像是一把锉刀。国宝发现我的脚跟替他搔背痒很合适,每每背上发痒,便要我用脚跟磨。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磨着磨着,丈夫入睡了。可以听见他低沉的鼻息声。月亮快落山了,斜斜地从窗格子里斟进来,撒在床前的衣橱上、地板上。窗外,纺车娘一声接一声叫得烦人,睡不着。躺在床上闷闷想心事,一直挨到天亮……
潞潞满五岁进六岁了。本想越大越好带,可这小家伙却越大越调皮。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了个坏习惯,晚上不到是一点钟绝不上床睡觉。不仅不睡,还喜欢在床上翻来滚去叫闹不已。国宝对此十分头痛,却又毫无办法。只是捧着头坐在书桌前长吁短叹。
“我要有个书房就好了!”他常常这样说。他是个读书人,要个书房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理解他的苦衷,可又没法满足他的要求。家里两间木房,除了一间做堂屋和厨房,余下的一间隔成三个小房间。东面是两老的卧房,我们睡西面,中间一个黑不溜秋的夹房用来做谷仓。一家大小六口人的田,我虽侍弄不好,但每年也收个三四十担谷子,加上包谷红薯,里面堆得满满的。
国宝不愧是个读书人。做事从来说一不二,雷厉风行。一个星期天,他从学校带来三个高中男生,将谷子红薯包谷统统从谷仓中挑出,堆在堂屋角落里,然后用木板圈起来,于是搬进书桌书橱。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搬就搬吧。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不再唉声叹气。或许,搬了书房,有那么一天你真能写出点什么来!
这一来,我们家可热闹了。天擦黑,堂屋便成为老鼠的世界,百十只老鼠嚼谷子,剥玉米、啃红薯,窸窸窣窣响成一片。吃饱了,它们便在谷堆上嬉闹,调情,拉尿拉屎。我有心上街上抱一只猫回来对付这些孽障,可一问价格,20元一只,只得作罢。
潞潞的奶奶首先是对国宝唠唠叨叨,然后便将铺盖从房里搬出,在谷堆旁摊了个地铺。每夜不停地赶走老鼠。“嘘!嘘!”我半夜醒来,听见这声音,心里又怜又痛。嫁过来十多年了,婆婆从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人心换人心,这事放到谁身上谁也不会好受。于是我狠狠心,卖了一百斤毛谷,买了只斑猫。这样,家里总算安静了。
国宝这人手脚并不笨,这我清楚。想当年他还没上大学的时候,是家里响当当的主要劳力。每天忙完队里忙家里,手脚不停。他会木工,会捕鱼,还会套田猪挖穿山甲。只是这些年他除了那些书外把什么都丢荒了。要说他身上还有点什么与当年没什么两样的话,那就是吃饭。这几年物价高,家中拮据,加上我没时间对付,一日三餐总是匆匆忙忙随随便便。他从没叫过苦,吃得比我还香。初一十五家里打牙祭,他总把好的瘦的挑给两个老人和两个小把爷。自己却专拣肥肉或那些筋筋吊吊的落脚货。常常一边吃一边摇头晃脑地读一首什么诗:“莫道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看他吃得开心的样子,我从心底感到高兴。
这天,省里两个写书的和一个编书的下乡到我们村。国宝说他们来体验生活。我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可却知道他们全是有学问的人。国宝似乎老早就和他们认识,他把三人恭恭敬敬请到家里,待为上宾。我从地里杀虫回家,一桌丰盛的饭菜已摆到了堂屋正中。白斩鸡、红烧鸭、清蒸鱼,花花绿绿,香气扑鼻。这样的饭菜,不用说平常日子,山里人连过年也没见过。没想到国宝竟能做出这么洋气的饭菜来。别看他平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那是大人不做小人事。
白米饭、重阳酒满屋喷香。三个贵客一边吃一边赞叹不已。我却香在嘴里痛在心头。年初买了十六只鸡崽,可一个月后拉白屎死了十一只。剩下五只总算喂大了。下个月潞潞的奶奶满六十八,虽不办酒,但叔姑侄儿外甥们聚拢来就是两桌人。没两只鸡上桌会显得寒酸,也会在我身上落下话把。月初潞潞拉十多天稀,病好后坐马桶坐着坐着就抽筋,我都舍不得杀只鸡给他补身子。倒好,如今过早地成了国宝待客的菜!两个孩子一人一个鸡腿在廊檐下三下五除二便吃尽了,老拿眼睛朝桌上瞟。国宝就像没有看见似的只顾往客人碗里夹菜。看孩子这副馋相,此时就是龙肝凤胆也吃不下了。我放下碗,和客人打了声招呼,左手牵着老大,右手抱着老二,想也没想便朝村中的供销社走去。塞给他们每人一块钱,让他们俩想吃什么买什么。两个孩子欢呼雀跃,欢叫着向副食品柜台奔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顺着两腮温温热热地滚落下来。
这夜国宝喝了九分醉。要说他这人还是有个优点,从不贪杯。他是太高兴了才醉的。他没像往常那样吃过饭就把自己关进书房里。而是满面红光地坐在床边。
“春花,明年我的中篇小说就能发表了。真的,绝不骗你!”我迷迷糊糊地直想睡,只是嗯嗯地答应着。我知道他不需要我发表任何意见,他太高兴了,心里盛不下,需要倒出来。“我那三位朋友答应帮我推荐,叫我脱稿后马上寄去。”他脸上溢出光流彩,嘴上滔滔不绝。我却再也无法睁开沉重的眼皮。
“春花春花!”国宝不让我睡觉,使劲摇着我,“不瞒你说。明年我就再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啦!到那时……”我一激灵,醒了。“不是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我故意淡淡地问,“要当官了?”“当官?去它的吧!我还瞧不起当官的呢!我要当作家!”他手舞足蹈,完全陶醉在一种美妙的境界中。
作家!读耕中的时候就知道作家是一种非常神秘而又伟大的人。难道国宝就要成为作家而我也将成为作家的妻子?这一夜我一反常情久久不能入睡,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满足?期待?憧憬?我说不清楚。反正一下便觉得今后的日子很有盼头。
潞潞拉梦尿了,我起身给他换裤子。天已蒙蒙发亮,朦胧的亮色裹着丝丝凉风从窗格子挤进来。再也不能睡了!我穿上衣服,起身去门外抱柴火。赶紧弄熟早饭!丈夫要上课,我要上山给黄麻剥黄脚叶。
拉开大门,一丝微微的晨风扑面而来。好凉快!村寨万籁俱寂,人们正流连于黎明前的最后一曲好梦里。我突然有点可怜自己。心想:千万不要成为作家夫人!作为一个大学生的妻子我就够不幸的了,一旦成为作家夫人,我坚信我的不幸将更会加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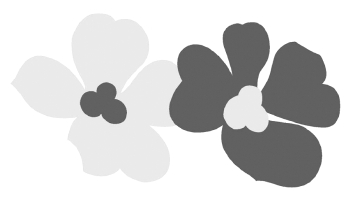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