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蝉和蚂蚁的寓言
名声大多是靠传说故事传开来的;无论是在有关动物还是人类的故事中,都能找到无稽之谈的踪迹。尤其是昆虫,如果说它以某种方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是靠了民间传说才走运的,而民间传说却最不关心故事的真实性。
比如说,谁不知道蝉,没听过它的名字呢?在昆虫世界里,到哪里还能找到像它那么出名的昆虫呢?它那爱唱歌不顾将来的故事,早在我们开始训练记忆时起,就被作为素材了。琅琅上口的短小诗句告诉我们,严冬到来的时候,蝉跑到邻居蚂蚁家去乞讨。这乞丐不受欢迎,得到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回答;而这正是这个昆虫出名的主要原因。那两行短短的答话粗俗而粗鲁:
你过去唱歌的呀!我很高兴。
那么,你现在就跳舞去吧!
这两句话给昆虫带来的名声,远远超过了蝉高超的演奏技巧。它钻进儿童的心灵角落,再也不会出来了。
蝉生长在有橄榄树的地区,大多数人都没听过蝉的歌声;可它在蚂蚁面前那副沮丧样却老少皆知。名声就是这么来的!一个严重违背道德和自然史的传说,一个大可非议的传说,一个只适合奶妈讲述的小故事,居然就这样造出了名声。而这名声,就像小拇指的靴子和小红帽的饼一样[1],顽固地支配着岁月留下的破碎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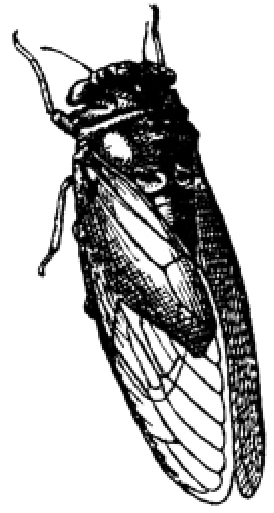
南欧熊蝉
儿童是恋旧的人,习惯和传统一旦保存到他们记忆的档案中,就会变得难以摧毁。蝉这么出名,应归功于儿童。他们刚开始试着背书时,就结结巴巴地背诵蝉的不幸。有了儿童,寓言中那些粗浅无聊的奇谈怪论就会保存下来。说什么蝉会在寒冷的冬天挨饿,尽管冬天没有蝉;蝉会求人施舍几粒麦粒,尽管这食物根本不适合它娇弱的吸管;蝉还会乞讨苍蝇和小蚯蚓,尽管它从来不吃苍蝇和小蚯蚓。
这种荒唐的错误,究竟责任在谁?拉·封登。虽然他的大多数寓言观察细致入微,令我们着迷,但在蝉这件事上他却考虑欠周。他寓言里的前几个主角,如狐狸、狼、猫、山羊、乌鸦、老鼠、黄鼠狼,还有很多别的动物,他都非常了解,因此描述起来准确细腻,饶有趣味。这些都是他熟悉的动物,是他的邻居和常客。它们的集体生活和私生活都发生在他的眼前;但是,在兔子雅诺[2]蹦跳的地方,蝉是个外乡人;拉·封登从来没听到过它的歌声,也从来没见过它的身影。他心目中这个著名的歌手肯定是蝈蝈儿。
格兰维尔[3]绘制的插图,狡黠刁钻的铅笔线条与著名的寓言可谓相得益彰,但他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他的插图里,蚂蚁穿得像个勤劳的主妇,站在门槛上,身旁是大袋大袋的麦粒;乞食者伸着脚,哦,对不起,伸着手,蚂蚁不屑地扭转身去。头戴十八世纪宽边女帽,胳膊下夹着吉他,裙摆被北风吹得贴在腿肚子上。这就是这个角色的模样,而这完全是蝈蝈儿的形象。和拉·封登一样,格兰维尔也不知道蝉的真正模样,倒是出色地再现了那个普遍的错误。
拉·封登这个浅薄的小故事,不过是拾另一个寓言家的牙慧。描写蝉遭受蚂蚁的冷遇的传说,如同利己主义,也就是如同我们的世界一样历史悠久。古代雅典的孩子们,背着装满无花果和橄榄的草编筐去上学,就已经把它当作背诵的课文在口里嘟囔了:“冬天,蚂蚁们把受潮的粮食放到太阳下晒干。突然一只饥饿的蝉来乞讨,它请求给几粒粮食。吝啬的收藏家回答说:‘夏天你在唱歌,那冬天你就跳舞吧。’”这情节枯燥了些,而且有悖常理;可这正是拉·封登寓言的主题。
但是,这个寓言是出自希腊,一个盛产橄榄和蝉的国家呀。那么,伊索[4]真的如传说那样是这寓言的作者吗?我很怀疑。不过,没什么关系。作者是希腊人,是蝉的老乡,他应该对蝉有充分的了解。即使在我们村里也没有那么见识贫乏的农民,会不知道冬天是绝对没有蝉的。临近寒冬,需要给橄榄树培土。这时节,那些经常翻弄土地的人,都会认得铲子挖掘出来的蝉的若虫;他在路边无数次看到过这种若虫,知道到了夏天,它是怎样从自己挖的圆井洞里钻出地面,又怎样挂在细树枝上,从背中间裂开,把比硬羊皮纸还要干的外壳蜕去,变成由浅草绿色旋即转成褐色的蝉。
那么,阿提喀[5]的农夫也不会是傻瓜,连最缺乏观察力的人都不可能错过的,他当然也会注意到;他也知道翻耕土地的乡亲们很清楚的事。创作这个寓言的文人,不管他是谁,都有最好的条件了解那些事情。那么他故事里的谬误是从何而来呢?
古希腊的寓言家比拉·封登更不可原谅,他只讲述书本上的蝉,而不去询问就在他身边像锣钹般喧嚣的蝉;他不关心现实,只因循传统。他只是一个陈年旧事的应声虫,复述从可敬的文明源头印度传来的故事。印度人用笔描述的主题,是展示没有远见的生活会导致怎样的苦难;可是古希腊寓言家似乎没有真正搞懂故事的主旨,还以为自己运用的这个小小的场景,比昆虫的谈话更接近真实。印度人是动物们伟大的朋友,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这一切似乎都表明:最初寓言的主角并不是蝉,而很可能是另一种动物,正如人们想象的是一只昆虫,它的习性恰好与寓言中的昆虫非常符合。
这个古老的故事,曾在很多个世纪里引起印度河两岸哲人的深思,也让那里的孩子们得到了乐趣。它也许和历史上某个家长第一次提出厉行节约一样年代久远。这个故事从上一代的记忆中传到下一代的心里,有的还保持原貌,有的就传得走了样;而传到希腊时,故事已失去原味了。就像所有的传说一样,为了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细节已被岁月的流水磨损。
希腊人在乡间见不到印度人说的那种昆虫,就随随便便地把蝉给放了进去,就像在“现代雅典”巴黎一样,蝈蝈儿代替了蝉。坏名声就这样形成了,错误刻进了孩子们的记忆中,再也抹不去。从此,谬误压倒了真实。
我将设法给这个被寓言诋毁的歌唱家平反。确实,它是个讨厌的邻居,我毫不迟疑地承认。每年夏天,它们被我家门前两棵高大葱郁的法国梧桐吸引,数以百计地前来安家;它们从早到晚地不停地鼓噪,敲打着我的耳膜。在震耳欲聋的奏鸣曲中,我根本不可能思考;思路在晕乎乎地飘忽旋转,怎么也定不下来。如果不利用早晨的几小时,整个白天就会白白浪费。
嗨,着了魔的虫子,你是我家的祸害,我多么想住宅安静呀。可有人说,雅典人把你养在笼子里,好随时欣赏你们的歌唱呢。饭后消化打盹时,有一只蝉在鸣叫也就罢了;可我聚精会神想问题时,几百只蝉一齐奏乐,震得我鼓膜发胀,简直如同酷刑啊!可你却振振有词,理由充足,是你先占领这里,鸣叫是你的权利。在我来之前,这两棵大树是完全属于你的;而我却反倒成了树荫下的入侵者。好吧,就算你说得有理;不过,为了替你写故事的人,还是调弱你的响钹,压低一点振音吧。
事实的真相否定了寓言家的肆意杜撰。尽管蝉和蚂蚁有时是有一些关系,但关系并不那么确定;惟一确定的是,这关系恰恰与寓言家告诉我们的相反。这关系并不是蝉主动去建立的,为了活下去,它从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反倒是蚂蚁,这个贪婪的剥削者,把一切可吃的东西都囤积在自己的粮仓里。不管什么时候,蝉都不会跑到蚂蚁门口去乞讨,也不会老实地承诺连本带息一起归还;恰恰相反,是蚂蚁,饿得饥肠辘辘去求歌唱家。我说的是“求”!“借”和“还”从来不会出现在强盗的习性里。它在剥削蝉,而且还厚颜无耻地把蝉抢劫一空。这种抢劫,是个奇特的历史问题,至今还不为人所知。
七月的下午热得令人窒息,一般的昆虫干渴乏力,徒劳地在干枯萎谢的花朵上转悠,想找水解渴。但蝉对普遍的水荒一笑置之,它用小钻头一样的喙,刺进取之不尽的酒窖中。它在小灌木的一根细枝上站定,一边不停地唱着歌,一边钻透坚硬平滑、给太阳晒得汁液饱满的树皮。然后,它把吸管插到钻孔中,一动不动,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畅饮,沉浸在糖汁和歌唱的甜美中。
我再观察一会儿,说不定就能看到意想不到的灾难呢。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东张西望地转悠,它们发现这口井,井边渗出来的汁液把它暴露了。这群家伙蜂拥而上,开始还有些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我看到匆忙赶到甜蜜的井口边的,有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花金龟,最多的是蚂蚁。
那些小个子为了走近清泉,便钻到蝉的肚子下,蝉宽厚地抬起足,让不速之客自由通过;那些大一点的昆虫,不耐烦地跺着脚,快速地吸了一口就退开,到旁边的树枝上去兜一圈,然后更加大胆地回来。它们越发贪婪起来,刚才还有所收敛,现在已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开源引水的凿井人从泉水边赶走。
在这群强盗中,最不罢休的是蚂蚁。我曾看见它们一点一点地咬蝉的足尖;逮着正被它们拉扯的蝉的翅尖,爬到蝉背上,挠着蝉的触角。一只大胆的蚂蚁就在我的眼前,竟然抓住蝉的吸管,拼命想把它拔出来。
巨人给小矮子烦得没了耐心,最终放弃了水井,朝这群拦路抢劫的家伙撒一泡尿逃走了。可是对蚂蚁来说,这种极端的蔑视算得了什么呢?它的目的达到了,它现在是这口井的主人。但是,没有转动的水泵从井里汲水,井很快就会干涸。井水虽少,却甘美无比。等以后有机会,再以同样的方式去喝上一大口。
大家看到了,事实的真相把寓言里虚构的角色彻底颠倒过来。肆无忌惮、在抢劫的时候毫不退缩的求食者,是蚂蚁;而甘愿和受苦者分享成果的能工巧匠,是蝉。还有一个细节,更加能说明角色的颠倒。歌唱家在五六个星期里长时间地欢腾之后,生命衰竭,从树上掉下来,尸体被太阳烤干,给来往行人践踏,又被这个总在寻找战利品的强盗碰上了。蚂蚁把这丰盛的食物撕开,肢解,剪碎,分成碎屑,运回去充实它的储藏仓。更有甚者,垂死的蝉,蝉翼还在尘埃中微微颤动,就有一队蚂蚁在拖曳,把它肢解开来。那时的蝉真是满心忧伤啊。这种残酷行经,才真正体现了这两类昆虫之间的关系。
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对蝉的评价很高,被称为“希腊贝朗瑞”的阿那克里翁[6],为蝉做了一首颂歌,夸张地大肆赞扬蝉。他说:“你几乎就像诸神一样。”诗人给予蝉神一样的尊荣,但理由却不恰当。他认为蝉有三个特性:生于泥土,不知疼痛,有肉无血。不要去指责诗人的错误,这不过是那时的普遍说法而已;而且这个错误在观察的眼睛睁开之前,已经流传很久了。再说,在强调措辞与和谐的小诗句里,人们不会那么细致地注意到这一点。
即使在今天,和阿那克里翁一样对蝉很熟悉的普罗旺斯诗人,在歌颂蝉的时候,也并不怎么关心真实的蝉。不过,这个批评不适合我的一位朋友。他是热情的观察家,也是一丝不苟的务实派。他准许我从他的文件夹里抽出一首普罗旺斯语作品。在诗中,他以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着重描写蝉和蚂蚁的关系。诗意形象和道德评判由他负责,这些精致美丽的花朵,和我的博物学园地无关。不过,我得承认,他的叙述非常真实,符合我每年夏天在荒石园里的丁香树上看到的情况。我把这首诗的法语译文附在后面,许多地方只是意思大致相近,因为普罗旺斯语在法语里并不总是能找到对等的词。
蝉和蚂蚁
一
上帝啊,真热!可这是蝉的好时光。
它快乐得发狂,尽情享受
那似火的阳光;真是收获的好季节啊!
在那黄金般的麦浪里,收割者
弯着腰,弓着背,辛苦劳动,不再歌唱:
干渴啊,把歌声掐死了在喉咙里。
这是你的好时光啊。可爱的蝉,勇敢些,
让你的音钹响起来吧,
扭起你的肚子,鼓起你的两面镜子[7]。
收割的人挥舞着镰刀,
刀头啊不停地翻动,刀刃
在金黄的麦穗中闪光。
割麦人腰间挂着小水罐,
罐口塞着草,罐里装满水。
磨刀石待在木盒里,凉快得很啊,
还能不停地饮水;
可人在火样的日头下喘着气,
骨髓仿佛都快给煮沸。
蝉儿,自有解渴的妙法:你用尖尖的嘴戳进
细树枝鲜嫩多汁的树皮里,
钻一口井,
糖汁从细细的管道涌出。
甜蜜的泉水汩汩流淌,你凑近去
美美地吸吮玉液琼浆。
日子不总这么太平,哦,绝对不!那些强盗,
附近的,流浪的,
看着你挖井。它们干渴难耐啊,跑上来,
想要与你分一滴蜜浆。
当心,我的小可爱,这些囊中空空的家伙
先是卑谦,很快就会成为无赖。
开始只求饮一口,然后就要残羹剩饭;
进而不再满足,抬起头,
想要全部霸占。利爪似耙
搔弄你的翅尖。
爬上你宽宽的背脊;
还抓你的嘴、扯你的角,踩你的脚。
强盗将你四处乱拽,让你心烦意乱。
嘘嘘!撒一泡尿
向这些家伙喷过去,然后离开,
远远地离开这群
抢夺水井的败类。
它们浪笑着,寻欢作乐,
舔着唇上的蜜浆。
在这些不劳而获吸人血汗的流浪汉里,
最不甘罢休的是蚂蚁。
苍蝇、黄边胡蜂、胡蜂、害鳃金龟
这各式各样的骗子、懒鬼,
全都是给那大太阳赶到你的井边,
却不像蚂蚁,一心要赶你走。
踩你的脚趾,抓你的脸,
戳你的鼻子,
就为了赶走你呀,这无赖真没人能比。
恶棍把你的爪子当梯子,
胆大包天地爬上去。爬上你的翅膀,
蛮横无礼地散步,惹恼你生气。
二
以前那些老人们说的都不可靠。
他们告诉我们说,
冬日的一天,你饥肠辘辘。低头弯腰,
偷偷地前往
蚂蚁巨大的地下粮仓。
大堆的麦粒还没往地窖里藏,
已经沾湿夜晚的露霜,
此时正摊在太阳下翻晒,
等到晒干装进粮袋。
这时你突然来了,眼泪汪汪。
你对它说:“这天多冷,北风
呼呼直响,我
快饿死了。你积粮堆成小山
让我装一布袋吧。
我会归还的,在甜瓜成熟的时光。”
“借我一点儿麦粒吧。”还是快走吧,
别以为这家伙会听你讲,
别再骗自己了。那大包大袋的食粮,你休想得到一粒。
“滚远些,去刮桶底吧;
夏天只管唱歌,冬天饿死活该!”
那古老的寓言就是这么说的,
它教我们学那吝啬鬼
幸灾乐祸地系紧钱袋
……让这些笨蛋
也尝尝饿痛肚子的苦头吧!
这些寓言家让我愤懑不平,
说什么你大冬天去寻找
苍蝇、小虫和麦粒,这些你可是从不吃的啊。
麦粒!你要来做什么?
你有自己的甘泉,再也不要别的。
冬天又有什么意义?你的子孙
在地下酣睡香甜,
而你也长眠将不再醒来。
你的尸体掉下来,化为碎片。
一天,四处猎食的蚂蚁,看见了你的尸骸。
就在你干瘦的皮囊上,
这些恶棍拼命争抢;
挖空你的胸脯,把你切成碎片,
当作腌肉储藏。
这可是下雪的冬天最好的食粮。
三
这就是真实的故事,
与寓言说的完全不一样。
你们这些该死的作何感想?
哦,你们这些专捡小便宜的,
手上带钩,大腹便便,
想用保险箱来统治世界。
你们这些恶棍还放出流言,
说什么艺术家从不干活,
愚蠢的家伙活该遭殃。
闭上嘴吧,
蝉钻透树皮出酒,
你夺它的饮料;它死了,
不糟蹋它你还心不甘。
我的朋友就用他那富有表现力的普罗旺斯俗语,为被寓言家诋毁的蝉平了反。
【注释】
[1]小拇指和小红帽:法国童话故事作家佩罗的童话中的人物,收在《鹅妈妈的故事》中。——译注
[2]兔子雅诺:拉·封登寓言中的主人公。——译注
[3]格兰维尔(1803~1847年):法国画家,画风怪诞,富于想象。为拉·封登的《寓言集》配过插图。——译注
[4]伊索: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希腊寓言家。——译注
[5]阿提喀:希腊半岛,雅典位于此半岛上。——译注
[6]贝朗瑞(1780~1857年):法国歌唱家。 阿那克里翁(公元前6世纪):希腊抒情诗人,诗歌多以醇酒和爱情为主题。——译注
[7]音钹、镜子:均为普罗旺斯语中对蝉的身体部位的称呼,与发声有关。——译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