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可能性的滞后:再谈庶民历史
作为可能性的滞后:再谈庶民历史[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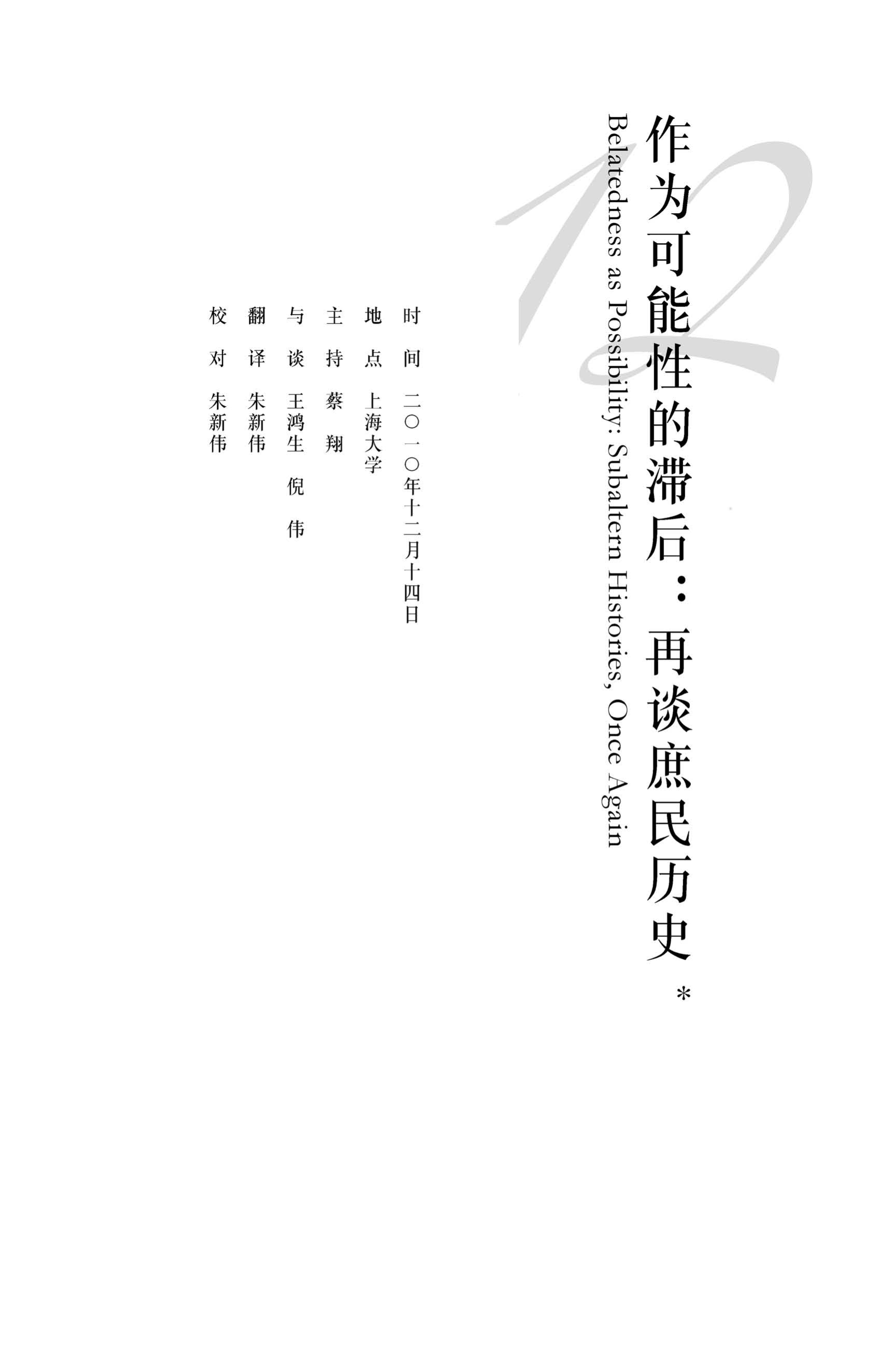
我要谈的是一系列被称作“庶民研究”的历史书写。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便经常参与其中。这套书写已获得全球性声誉,为历史研究引进了一些有趣的方法和概念。之所以想在这里谈《庶民研究》这本杂志的历史,是因为我想借此与大家分享全球左翼的某种历史观,或者说,概述性的历史观。庶民研究曾经被泛指为“左翼”的历史书写。我说“曾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继续出版该刊。“庶民”这个词源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著作。葛兰西被墨索里尼关押了起来,于20世纪30年代末去世。[2]他把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称为“庶民阶级”。我们的书写系列还受到印度当时的毛泽东主义思想的影响。讨论《庶民研究》,免不了要讨论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以外地区的接受史和理解史。我知道在中国关于毛泽东的贡献有许多讨论,我称之为“中国的毛泽东”,或者说,民族主义的毛泽东,这个“毛泽东”是贵国的政治和思想先驱。但是,还有一个“全球的毛泽东”。这就如同有一个印度的甘地,还有一个全球的甘地。这两个“甘地”并不完全一致。有时,从民族国家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观察同一个人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我觉得可以在此谈一下那个“全球的毛泽东”,这个毛泽东如何进入远在印度的我们的视野,如何形塑了我们的思维。这也许不是你们在中国讨论的那个毛泽东,但我觉得,全球的毛泽东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毛泽东同样重要。
我所讨论的这个全球的毛泽东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全球动荡年代。大家知道,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大量的学生运动,不单是在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印度的情形也是如此。当然,中国那时候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中国、欧洲和印度的学生造反运动互有联系。欧洲人理解“文革”的方式说起来很有趣。而我们当时在印度深受欧洲文革书写的影响。但是,20世纪60年代还属于一个更大的世界历史进程,即去殖民化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0年间,欧洲老牌列强式微,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独立,美国和苏联崛起为两大超级大国。因此,冷战的年代也即去殖民化的年代。
许多非西方历史学家都在讨论如何将“历史”本身去殖民化。我想往后退一步,先讨论盎格鲁——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Anglo-Marxisthistoriography),或者说,社会主义历史书写在英国和美国的状况。虽然英美的所谓社会主义历史书写也反对帝国主义,但实际上,它无法凸显问题的症结。以印度为例:
英国人生产了大量的有关印度历史、印度考古学和古钱学的著作,但所有这些著作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帝国主义历史书写。这种历史书写方式最终都是要为帝国主义或政治精英的思想正名。帝国主义历史书写反复宣称,英国人维持大不列颠帝国并统治其他民族的原因是,后者还不够成熟,还没准备好自治。然而,由于英国对外是帝国主义、对内是自由主义,他们不得不解释,为什么一方面自治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一方面亚洲和非洲人民却仍旧不能够自治,必须要让英国人像老师上课一样教导当地人如何自治。
因此,在全球民主历史进程当中,这是一种我称之为“时机未到”结构(not yet structure)的民主观或自治观,其中包含着帝国主义的时间结构。甲对乙说:“当然,我希望你自治,希望你有能力投票,希望你参与政治体制,但时机未到。”我把这种结构称之为“时机未到”结构。这种结构深深地印刻在欧洲历史书写当中,甚至当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写作所谓的第三世界历史、当他们用表面上反帝国主义的形式书写时,“时机未到”结构仍然和帝国主义历史一样印刻在那里。所以,尽管有着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区别,盎格鲁——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殖民地状况时依旧分享着“时机未到”结构。英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书写一直持续至20世纪30年代末。其中最早的著作之一是科尔(G.D.H Cole)写的《平民史》。科尔决定下笔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发现平民不像女王、皇帝或政客,他们通常不会留下什么历史记录。所以,他为了让历史变得更加民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量化。他收集了工资和物价方面的历史数据。平民第一次进入历史的时候,是以数字、而非面孔的形象出现的。如何写作平民的历史,其中确实蕴藏着有意思的问题。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在战后获得了大幅进步,历史学家正面迎接挑战,以描绘面孔而非抽象数字的方式写作“普通人”的历史。其中最有名的是汤普森(Edward Th ompson)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这些历史学家创造性地从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借鉴方法,将平民引入历史,描绘出平民的斗争如何变革了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在写作英国民主历史时对此加以体现。
但甚至这些力图使历史变得更加民主的学者,这些将工人阶级和穷人当作历史变革动力的大历史学家,也会陷入“时机未到”思维的迷雾。当他们书写欧洲以外地区人民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明显,尽管他们都秉持着民主的精神。我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件事情触发了《庶民研究》的发端。汤普森1963年发表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前,霍布斯鲍姆写了《原始的叛乱》(1969)。在那本书中,霍布斯鲍姆将目光投向欧洲以外的世界,考察那些陷入殖民统治并最终奋起反抗的部落和农民。然后,他作出了颇有意味的判断。他说,20世纪是最具革命性的世纪,因为部落人民和农民阶级不得不每天处理与现代官僚体系的关系;而部落人民和农民阶级被迫反抗现代政府,这乃是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特点。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但是”——霍布斯鲍姆还正确地指出,农民和部落人民、没受过教育的人民,不得不怀着满腔怒火与现代官僚体系作斗争,而后者是由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和欧洲殖民官员组成的,前者却缺乏对现代政府和商业制度的全面理解。因此,前者通常会使用“魔法”或“超自然力量”来对抗现代制度。他们有时会相信超自然力量将保护他们抵挡枪炮,与现代军队作战。这在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都发生过。鉴于此,霍布斯鲍姆认为20世纪虽然是最具革命性的世纪,但欧洲以外的历史行动者的意识仍然是“前政治的”(pre-political),他们的政治意识“时机未到”。所以,甚至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的历史学家也会在思考欧洲以外地区的群众政治时陷入“时机未到”结构。可以说,亚洲和非洲的反殖民主义群众运动虽然有大量的农民和部落人民加入,他们的思维和意识却仍然是“前政治”的。
印度亦如是。反抗殖民者和当地统治者的农民和部落起义一直伴随着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甚至著名的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组成的。[3]但在霍布斯鲍姆的眼里,这些反抗都不能算作政治的,因为农民和部落在根本上是“前政治的”。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1968年,剑桥大学的学者希尔(Anil Seal)出版了一本关于印度民族主义的重要著作——《印度民族主义的诞生》(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该书的第一章便驳斥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100多次印度农民起义,称这些起义不过是拿着棍子和石头的愤怒农民的暴动,谈不上政治或意识形态。只有那些能够谈论英国制度的、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的行动才谈得上是“政治的”。甚至我们印度人自己或多或少也接受这一假定,这种“时机未到”的历史书写假设。虽然我们认可农民是民族运动或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
历史学家,不论是欧洲人还是印度人,全都陷入“时机未到”结构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试图以(西)欧的政治历史来解释全世界。在他们看来,欧洲政治是发展型的。欧洲历史上存在着农民,但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渐成为工厂和资本主义农庄里的工人阶级。同样,工人起初是工厂里的农民,一步步地学习现代工厂的纪律。但后来,工人开始反抗,为争取权利而斗争,最终组成获得权利保障的工会。通过这一过程,农民以产业工人的形象重生,而产业工人则以公民或革命者的形象重生。这是我所谓的“发展主义”模式。这种一步步递增的历史观即历史阶段论,其内在蕴含着“时机未到”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以外地区的农民和部落虽然能够以革命者的身份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但却仍被看作是前政治的。
要将历史学这门学科去殖民化,也就是要挑战这一“时机未到”结构,挑战政治主体的发展型理念。“时机未到”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政治理念,可追溯至现代政治思想之初。但想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去殖民化国家的境况:中国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农民革命,成为把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民族国家;印度通过甘地领导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群众民族主义也成了民族国家。越南人刚刚打败法国人,后来还战胜了美国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农民民族国家。在这些事件中,农民一夜之间翻身做了革命者或由革命者过渡为公民。印度决意实行群众民主制度,赋予农民投票权,不论他们是否受过教育。印度领导人没有对农民说,我们要先教导你们何谓民主,再把选票交给你们。印度领导人决定农民第二天就可以成为公民,不必等到大规模的工业化、普及教育和欧洲式的社会变革铺展开来。中国也没有抱着先发展产业工人阶级的想法而拖延革命的脚步。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通过印度、中国和越南的经验来书写民主、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历史,并且避免欧洲历史学给我们的视角,那么,工业以外的群众在我们的叙述中扮演什么角色?答案很明显。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没人能够撇开如此庞大的一群人而创造出反殖民主义的群众政治——你必须要为农民预留空间。农民必须是主要的行动者。所以,如果你读毛泽东的文字,你会看到他所理解的农民战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在理论上代表工人阶级。当然,只是在理论上,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人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在真正发生了城市工人阶级革命的苏联,也是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因为俄国的工业化程度还比较弱。20世纪反殖民主义政治的必然趋势是,农民不得不迅速被征用为革命力量或民族主义者。领导人来不及将他们送入学校。政治运动就是农民接受教育的学校。可以说,反殖民主义的历史和历史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同时挑战了欧洲深层的“从幼稚到成熟”(maturation)的政治观。
我们于1982年开始出版《庶民研究》,当时共有9个人,其中一位学者比我们其余人年长约20岁,担当领导角色。我们原来全都是毛派或对毛泽东思想有着同情的学者。我们都认为,不能把农民称为“前政治的”。那我们怎么着手呢?我们的精神导师古哈(Ranajit Guha)[4]引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著名口号:炮打司令部!他说,无论谁来解读那些遭遇现代官僚体制压迫的现代农民,都不能把农民当作前政治的。我们的第一个观点是,农民从一开始便是政治的。人民本质上就是政治的。我们都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2年,印度与中国发生了一场战争。文革开始于1966年,印度的许多年轻人由于国内的常年贫困和社会不公现象而感到幻灭,转而发展出对于毛泽东的一种非常浪漫化的想像。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这是受了欧洲关于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想像的影响。我们阅读欧洲人和中国人关于文革的描述。结果,1969——1971年间,印度发生了一场毛泽东式的运动,大约有4 000人因此丧生。其中有些年轻人在革命失败后成了历史学家,他们想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历史进程的另一种可能性。1969年,古哈在英格兰任教,准备写作一本关于甘地的书。但他于1970年来到了德里,结交了一些毛派朋友,然后对于印度农民阶级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潜能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其中的一些年轻朋友后来到了英格兰读博,古哈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这样,他召集了我们八九个人,就印度反殖民运动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印度反殖民群众运动的核心存在着一个矛盾:甘地本人反对暴力,但农民和部落常常为了民族大业而被动员起来,以甘地的名义行使暴力!因此,我们当中许多人对于农民眼中的甘地形象非常感兴趣。我们意识到,对农民来说,甘地有点儿像个神。不是超然的神,而是乡村的神。一个乡村的神既能让村民染上霍乱和天花,也能保护人们免受侵害。乡村地区关于甘地有着许许多多传说。我们认识到,如果你把这些都叫做“前政治的”,那你对于民族国家及其历史的理解就会变得过于精英化。所以,我们开始写作一部反精英的历史,反对欧洲历史学家的历史阶段论。我们在经历工业化之前就形成了民族国家。中国在形成真正的无产阶级之前便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要反思农民作为政治历史的主体,牢记那些通过魔法、迷信或被其他精英斥为幼稚的手段进入现代政治领域的农民主体。
回到庶民研究。《庶民研究》将农民当作可以绕过现代化进程的现代主体,这种做法有着久远的谱系。俄国社会主义者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曾经在马克思晚年写信给他。查苏利奇问马克思,俄国能否在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写了几段很长的草稿,但最终只寄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他说自己身体状况太差,无法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草稿最终以英文的形式于20世纪70年代公之于世,因为当时全世界都想知道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能否为现代政治带来希望,能否避免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后果。从19世纪晚期起,许多国家的人都想探究农民成为现代政治主体的潜能。20世纪初,许多印度知识分子乐观地认为,与城市阶级相比,农民的共同体生活形态为社群主义的政治模式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一些人觉得,只要充分动员农民,就能跳跃式地跨入现代化进程。
回到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从未寄出的回信草稿之所以被翻译出来,是因为全球当时正处于中国革命和越南的情境之中,人们对于农民和现代政治的关系问题有着广泛兴趣。某些理论家,例如沙宁(Theodore Shanin),提出农民对于斯大林来说是真正的“尴尬阶级”。这些理论家的意思是,农民是一个永远无法被革命化的社会阶级。其他理论家则引用毛泽东在1927年关于湖南地区农民运动的经典考察报告,毛在报告中辨别了革命中的盟友:贫农是否真的有革命性,中农是否会在贫农和地主之间摇摆,等等。你可以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辩论在欧洲的20世纪70年代重新点燃,因为全球的左派都在寻找亚非地区的农民,将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的新希望,这又引发了关于文革的浪漫想像,形成了某种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信件在那时被公布了出来,而人们又忽略了他最终拒绝回答的姿态。人们一拥而上,都去研究马克思的草稿,试图通过动员农民来铸造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抵抗。因此,从欧洲工业化心脏地区被逐出之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运动还延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想要在其他地方寻找革命主题。可以说,在越战和《庶民研究》的背景下,那场辩论是这段历史的高潮。
那场辩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那场辩论有何重要性?我的观点是,20世纪的新兴民族和民族国家是在那些不必先上学、接受教育、获得权利的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人凭借他们参与革命运动和民族运动而自动获得了公民权。这段历史,及其生产出的历史学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时机未到”结构。我把那种挑战的武器称作“现在即刻”的时间观(the temporal horizon of the now)。所以,如果欧洲人对被殖民者说:“你们还没到自治的阶段。”被殖民者就可以回答,他们一直都做好了准备。我们用“现在即刻”来对抗“时机未到”。反殖民运动仿佛一直在用“现在即刻”的主张来对抗那种基于“时机未到”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我要说的是,这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遗产,民主运动的重大转型,同时也是政治思想史的难解之题。如果你去看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被赋予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澳洲土著获得的权利,你会发现,两者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机未到”的历史。由于反殖民主义反抗欧洲主宰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已经无法再跟某人说,你必须再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权利。政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民主化变革。虽然这一思想存在于欧洲思想史本身——基于自然权利的政治思想总是能天然地赋予你某种政治权利——但欧洲思想内部有着某种矛盾。这个矛盾被反殖民运动凸显了出来,后者通过实践,凭借“现在即刻”挑战了前者的“时机未到”结构。这一变革不可逆转。现在已经很难让一个人等待自身成熟,然后再赋予他政治权利。我觉得这是历史赐予我们的礼物。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谜题,因为,一旦将农民视为政治的,将农民的魔法、宗教或其他各种不成熟的表现引入政治领域,并拒绝将政治等同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不再能够理解什么是政治了。所以,现在政治已经无边无际,不再是一个概念,因为一个概念或定义必须要有其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变得民主化,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除了承认“一切皆政治”——政治与生活共生,不再有清晰的定义。这既是20世纪民主运动和反殖民运动的礼物,也将是思想领域意味深长的谜题。
【注释】
[1]在征询了查卡拉巴提教授本人意见之后,我们决定在此使用这场演讲的现场文字整理稿,其中的诸多发挥和延伸较之原讲稿更为生动。原讲稿“作为机遇的滞后:庶民历史再研究”收录于《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迪佩什·查卡拉巴提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5页。——编者注
[2]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1928年被捕,1937年去世。——编者注
[3]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本已摇摇欲坠的莫卧儿帝国自此完结,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亦从此告终,印度开始被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称为“英属印度”。——编者注
[4]出生于印度,现居奥地利,庶民研究的开创性人物,其《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书已成为后殖民主义经典著作。——编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